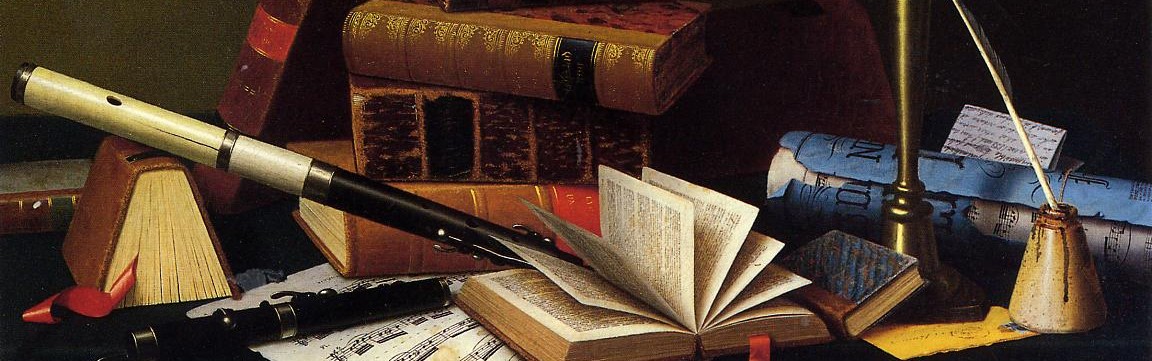冯象:为什么“法律与人文”
一
“法律与人文”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我起个头,简单讨论一下为什么法律教育和法学需要人文这个问题吧。文史哲作为一般的文化修养,是包括法律人在内的公民社会成长的条件。显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人文。
传统上,法律与人文的关系非常密切。法律依托文本,由人文知识集团操作,是所谓文明社会的一大特征。一切成文法社会,包括英美判例法,都是如此。换言之,人文对于法律人来说,不仅是一般的文化修养,还是法律技术的基础或行业基本功。起草文件、调解纠纷、法庭辩论,这些事都需要人文的阅历。但这种技术性的知识运用也不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希望探讨的,其实是这样一个学术问题:人文的思想立场,特别是人文的批判精神,能够对中国法学提出什么样的挑战?
我们来看看中国法学的现状。自七十年代末开始重建法制至今,总体而言,法律教育和法律人的人文成分(考试范围、学科出身)无大变化。但相对而言,可以明显感觉到,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影响越来越大了。实际上,官方和民间的学科分类都已将法学列为“社会科学”。这样划分是有些道理的,因为法学的方法的确在向社会科学靠拢,经常借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理论。形成这一趋势的原因很复杂,或许和大学的“表格化”管理、消费社会的膨胀有关。也跟现代/西方式法律的保守性格有关。此外,法律是“地方性知识”(吉尔兹语),不能提供分析自身的方法。教科书上的三段论司法推理,其实是一套循环解释的技术;就是从法条抽取原则和学说,再用这些原则学说来分析法条的含义,论证其正确或错误的适用。循环论证是做不了学问的。所以我说,法学若要把“地方性知识”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就得“融入”社会科学(见拙文《法学方法与法治的困境》)。当然国内外都有论者指出,即便如此,法学也不属于社会科学,行业性质不同。但无论如何,大家都承认,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正在成为法学的主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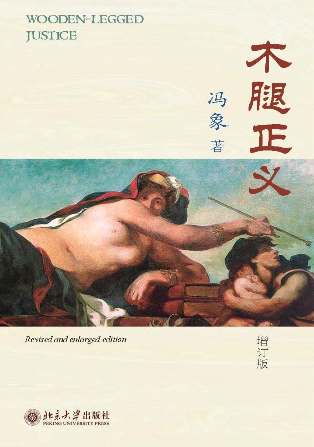 那么,我们今天怎样看待、进而主张人文呢?能不能“零敲碎打”地主张,比方说,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故而追溯传统必须重视史料的收集和梳理?不可否认,这是人文的用处了。再如,法律的基本原则、各派学说都可以做抽象的理论辨析,上升到哲学层面讨论,结果诞生了法哲学一门专业。那也是人文。更不用说遍地开花的“法律与文学”运动了。但这只是知识领域的划分,仍旧比不上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广泛地介入并引导法学研究。
那么,我们今天怎样看待、进而主张人文呢?能不能“零敲碎打”地主张,比方说,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故而追溯传统必须重视史料的收集和梳理?不可否认,这是人文的用处了。再如,法律的基本原则、各派学说都可以做抽象的理论辨析,上升到哲学层面讨论,结果诞生了法哲学一门专业。那也是人文。更不用说遍地开花的“法律与文学”运动了。但这只是知识领域的划分,仍旧比不上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广泛地介入并引导法学研究。
我有个想法,来杭州前和笑侠提过。我们主张人文,归根结蒂,只有两条理由:一是迄今为止,社科主流对新法治的剖析批判还不很成功。可能因为社会科学在中国尚且不够成熟(相对人文而言),无力突破法治意识形态的羁绊。它很少触及政法体制的深层结构;老百姓每天面临的困境,从上访村到拆迁户,反腐败到基层民主,医疗改革到社保崩溃,它也是清谈多于探究。从体制上看,比起“不实用”的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的市场资源多,更愿意“跑点”竞贿,收编为“基地”“工程”。因此,提倡人文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是我们坚持教育伦理、抗拒学术腐败、争取学术自由的当务之急。
第二,随着腐败日益合法化制度化,法律必然充斥具文,蜕变为“潜规则”的母法。具文化了的法律,仿佛一部冗长的“哈利波特”或续不完的迪斯尼动画片,是社会现实剪碎拼贴再颠倒了的虚构。而且惟有不停地虚构,那颠倒了的现实即“人人平等”的神话才不会化为乌有。这样,当法治的故事与虚幻的正义消除界限,当权利和腐败彼此不分,理论的进步就一定首先是人文精神与思想立场的进步了;反之亦然。注意,我这是就学者的职责,即社会批判和理论建构而言,不是说法律人的日常实务;理论和实务不可偏废,都是同学们在法学院学习、训练的内容。以上两点,便是我们在法学领域寄希望于人文的理论挑战。能不能做出贡献,乃至影响主流,则有待我们的努力了。
二
我总觉得,作者谈论自己的作品是件尴尬事。尤其今天这么严肃的场合,还存在一个悖论,让我难以直接回应大家的精彩评论。刚才几位发言提到罗兰·巴特的命题“作者已死”,就是说,作者写完作品便退出语义生成的舞台,作品的“原意”得靠读者和批评家来敷演了。按照这一理论,我该换个身份,“复活”作为读者发言。可是一旦“轮回”做了读者,就违反了法律或“大写的理性”对作者的定义(《著作权法》第十一条),没办法依常理解释,例如当初我这句话是那个意思;更不能诉诸普通读者的同情的理解和想象,以作者身份保持与读者的距离——那段让读者信赖作者、与之对话而跨越“生”“死”的心理距离。
所以我想就谈两点:一是如何看待西方尤其美国的学说和实务的“入侵”。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始于清末民初,大框架取自欧陆,学说则兼采欧美。这是解放前旧法治的情形。解放后受苏联影响,机构设置和教材学理照搬,但组织制度和政法实践延续了中国革命的传统。文革结束,法制重开,西方学说又回来了。九十年代起,美国的理论和律师实务占了上风,从商界和学界成两头夹击之势。官方政法话语随之掉头,词汇提法更新换代。进入新世纪,反而是有些美国专家信息不灵,不太适应了。例如德沃金教授,他来中国讲学,便经历了一场“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原本兜里揣着“异见人士”名单,准备掀开“竹幕”传播人权思想西方价值的;哪想到,从官府到学府,满眼西装革履,满耳“人权自由民主宪政”。气得他回到纽约登报批中国人虚伪,传为美国汉学界的笑话。
于是就有了新法治下,中国法学如何借鉴西方学说,并挑战主流立场和原理的问题。这问题一般说是不会有西方专家来为我们解答的,因为西方法学处理的,首先也是本土的传统与实践。毋宁说,许多时候,由于西方学术的强势和法治话语的“正确”,一些西方流行的理论教条和实务做法,极易成为我们思考的障碍和改革的歧路。因此我有这么个希望:认真研究西方的理论与制度、调查分析中国的现状之外,我们的法律教育还应强调一条:要鼓励不“正确”的想法,敢于怀疑、反思、批判。法律之为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理由在此。
其次,间接回答各位同仁的提问,谈谈自己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看法。我们称它为“运动”,是因为其中进路繁多、方法各异,像苏力讲的,看不出它会整合成一个理论流派(《法律与文学·导论》)。作为运动,“法律与文学”七八十年代在美国兴起,原是对法律经济学的保守立场的反动。多数论者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后现代、女权及族裔理论的运用,都是以法律经济学为靶子的。但是那样学究气的争论,对于我关心的中国的问题(社会控制、文化生产、政法策略的转型等等)并无太大意义。所以念法学院的时候,我读了很多案例文献,可是如何分析,提出有意义的理论问题呢?考虑了很久,试着写了两篇讨论兵家传统和著作权的论文,也没想明白。后来到香港教书,常回内地,同新法治的实践接触多了,才慢慢把一些基本问题厘清了。就是那些法律绝对保持沉默,千方百计遮掩的事情,例如私有产权的重建。这些年来大力鼓吹私权神圣,无非是要给产权复辟一个说法,争取一个平稳的过渡。但过渡期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腐败和掠夺,各种特权与强权的合法性,或它们作为受保护权益的地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产权复辟本来是毫无道德理想可言的,“私有”二字开头还是禁忌,故而媒体宣传只能从功利或工具主义的角度为它辩护。那么,是什么样的社会与文化屏蔽机制,使得人们,那些最容易被伤害的多数,低头认命而无力抗争呢?
我以为,这便是新法治的任务了。正是通过人们产权意识中最薄弱的环节,即抽象物上的私有产权——知识产权——开始了复辟的“平稳过渡”;在知识产权改写历史、重塑文学的同时,悄悄启动了新的社会与文化屏蔽机制。
我很欣赏李琛老师先前的发言。她说法律文本和文学文本一样,也是一种叙说,有着相似的温情的释读。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新法治的“温情”运作,一刻也离不开广义的文学,包括大众文艺与媒体的宣传配合(参见葛兰西,页389以下)。这一点我在《木腿正义》和别处讲过。但我今天要指出的是,由此出发,有可能为中国法学开辟一条进路,促其加入社会批判和理论挑战的前沿。这,就远不止“法律与人文”的题目了。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注:本文为作者在浙江大学“法律与人文”研讨会的两次发言。会上蒙胡建淼、葛洪义、许章润、郑成良、何勤华、刘星、钱弘道、苏力、沈明、刘忠、胡水君、孙笑侠诸先生析疑指正,获益良多,谨此一并鸣谢。
参考书目(以著/编者姓名拼音为序):
- 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北京认真对待权利》,载《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2.9.26。
- 方流芳:《如何认真地看待学术游戏——读德沃金访华报告有感》,载《视角》3:1,2003。
- 冯象:《木腿正义》(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冯象:《法学方法与法治的困境》,载《北大研究生学志》1/2006。
- 葛兰西:《文化论集》(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Cultural Writings), David Forgacs/Nowell-Smith编,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
- 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法律的文化解释》,梁治平编,北京三联,1994。
- 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北京三联,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