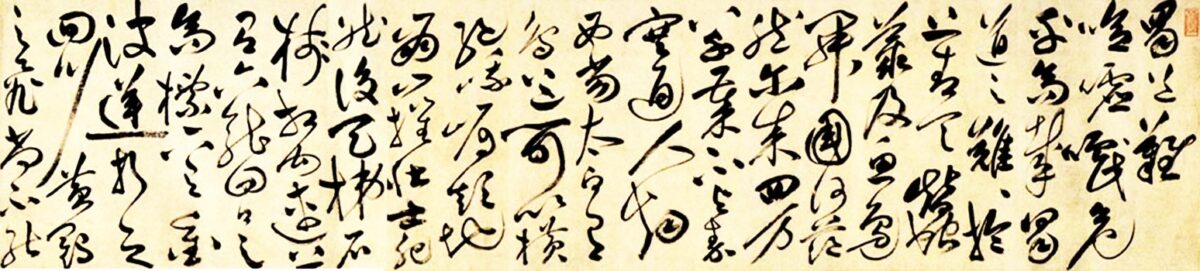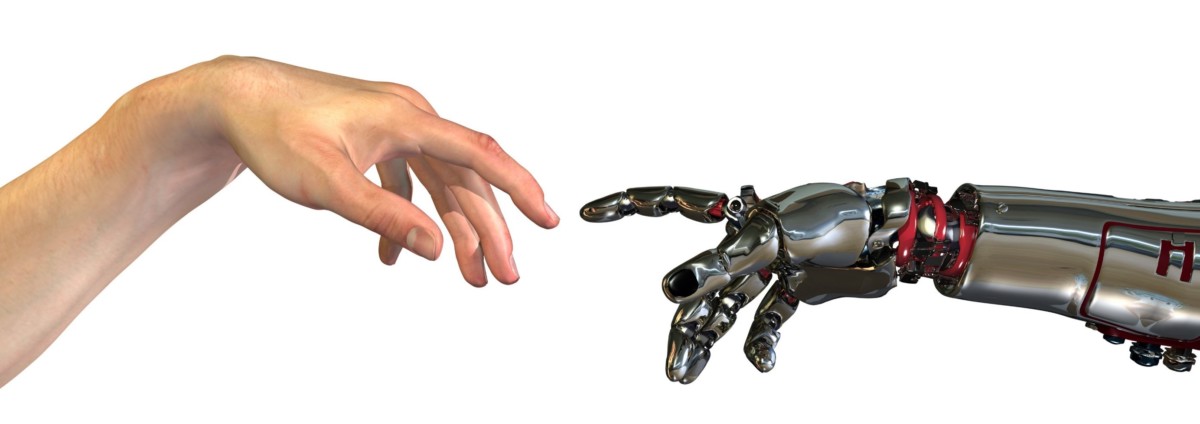为什么中文这么TM难?
《为什么中文这么TM难?》(Why Chinese Is So Damn Hard)是汉学家 David Moser 的一篇著名的文章(至少汉学圈以及真正下过功夫学汉语的外国人中间有很多人读过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1991年。作者行文诙谐幽默,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为什么对于绝大部分西方人来说,汉语是一门非常难学的语言(并且公道地指出,汉语之难,甚至显示在以之为母语的中国人也并不总能精湛地掌握它)。作者从西方人的视角出发,归纳出了九个原因。在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今天所知的互联网还不存在,更不要说智能手机或其他设配上的电子词典等各种辅助外语学习的“应用”了。话说回来,学习手段的便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汉语难学的事实。作者文中提到了文化隔阂是造成语言学习困难的深层原因。在可以遇见的未来,也许恰恰只有文化隔阂才是相对容易化解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的障碍。其他的困难一时还看不到什么解决的希望。
大部分第一代海外华人移民都会让自己的孩子学习汉语。然而,这些孩子中的大部分对汉语学习都意兴阑珊,仅因父母的压力才不得不学。当然,这种状况客观上也跟汉语在海外华人孩子生活中实际用处很小有关。不过,鉴于学习外语的黄金年龄持续很短,大概仅在十来岁之前,待他们意识到汉语的重要性时,通常早已过了语言黄金期。就这一点来说,华人家长推孩子学汉语,就像推孩子学乐器一样,尽管属于“家长作风”,但也未必不是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