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西洋人养cow吃beef?
《万象》去年十二期林行止先生《道在屎溺》一文谈委婉语,极佳,可惜有一处疵瑕。林先生提及“英语世界”吃牛肉不说“牛肉”而另用一词代替,羊肉、猪肉亦同,且引申作西洋人的饮食“文明”:“因为不忍食有感觉的动物,另起一名,便大快朵颐”等等。是谓“西洋人养cow吃beef”(页129)。虽是戏言,却出于误会。
英语里牛肉、羊肉、猪肉等另有一套名称,不是想说话委婉或注意饮食“文明”。这些名称来自中世纪统治英国的法国诺曼贵族和他们的侍从、士兵、僧侣。诺曼人占了当时英国大约二百万人口的四分之一,说的是法语(准确地说,是古法语的诺曼方言),听不懂伺候他们的英国人的“土话”。所以一头牛(cow < 中古英语cou < 古英语cu)宰了烤熟,端到“肉食者”主子的桌上,自然就变成beef,即古法语的“牛”字(boef < 中古拉丁语bos的宾格bovem),不能叫cow了。老百姓放弃自己的叫法,学说主子和上层阶级的语言,首先是为了沟通、谋生。猪肉改称 pork(中古英语 porc),羊肉改称 mutton(中古英语motoun),都是顺着诺曼人的说法,即源于古法语的词汇。这段法语入主英语的历史,从前许国璋先生等编的那套大学英语教程里专有一课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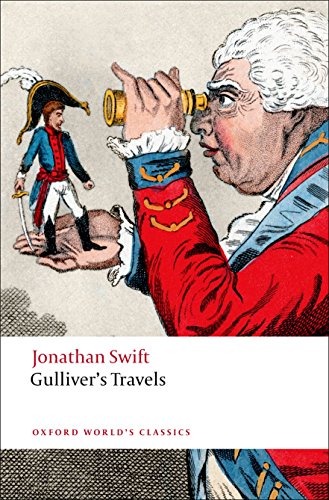 现代英语的词汇,将近百分之四十借自法语,有点像杭州话了。杭州话里有许多北方语汇和儿化音,与四周越方言区的各种方言明显不同。这是宋室南渡,小朝廷带来了北方官话,老百姓受了影响的结果。英语也是如此。其词汇语源之混杂,在主要西方语言里首屈一指。欧洲的“其他世界”,例如德、法、意、西诸语,在日常生活用语的层面,都没有给食用的家畜肉另起一“洋”名的(比如德语“牛肉”Rindfleisch:牛Rind + 肉Fleisch)。所以,不能说“西洋人养cow吃beef”。
现代英语的词汇,将近百分之四十借自法语,有点像杭州话了。杭州话里有许多北方语汇和儿化音,与四周越方言区的各种方言明显不同。这是宋室南渡,小朝廷带来了北方官话,老百姓受了影响的结果。英语也是如此。其词汇语源之混杂,在主要西方语言里首屈一指。欧洲的“其他世界”,例如德、法、意、西诸语,在日常生活用语的层面,都没有给食用的家畜肉另起一“洋”名的(比如德语“牛肉”Rindfleisch:牛Rind + 肉Fleisch)。所以,不能说“西洋人养cow吃beef”。
说到屎溺,在英语世界,大约从十八世纪末开始,进入维多利亚朝,才渐渐有条件“文明”起来,培育“文明人”亦即城里的中产阶级信守的卫生习惯和语言禁忌。换言之,现代英美人关于屎溺的种种语言禁忌,大多属于维多利亚朝的遗产,并非英国老底子的风气。前两天刚翻过一遍《格列佛游记》(1726),里面就有不少屎溺的描述,坦然得很。那本书当时是妇女和儿童都可以读的,作者斯威夫特是修辞的名家。常说英国人拘谨。《傅雷家书》载,傅聪先生听英国人唱亨德尔《救世主》(1742)“哈利路亚”一段,十分感动。在给父亲的英文信里说,英国人这时候突然inhibition(傅雷先生译作“抑制”)全消,达到了ecstasy(傅译“狂喜与忘我的境界”;两个英语词都来自法语)。这里所谓“抑制”,其实只是对现代英国人和一部分“英语世界”而言。因为以英语为母语的还有庞大的非“盎格鲁”裔人口,那些民族的艺术性格,多半是较少“抑制”而容易“狂喜”的。那么,回到《格列佛游记》和《救世主》领风骚的那个时代的英国,是不是说话就少一些禁忌了呢?也不是。有教养的男人之间,谈到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另有一种他们通晓的语言,那就是拉丁语。
二〇〇三年二月八日,原载香港《信报》2003.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