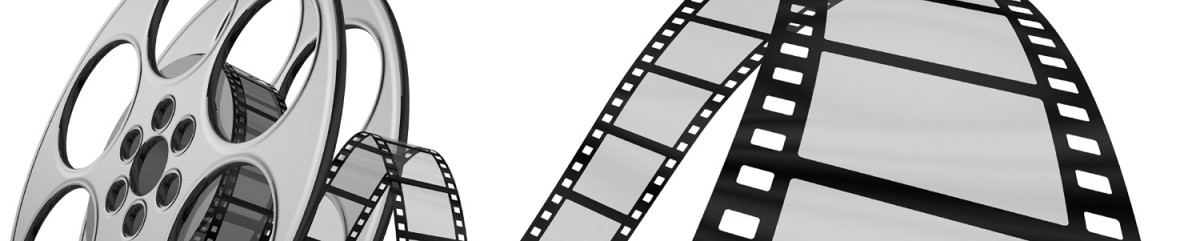
谌洪果:向死而生——评电影《死囚168小时》
这部电影的英文原名叫“Dead Man Walking”,意即“死囚上路”,它是美国监狱中死囚前往行刑室时狱警通常会喊出的话。中文世界一般将这部电影译为“死囚168小时”,我认为是比较少有的传神佳译:168小时即一周。然而,该片名以具体的168小时这个数字来定格一个生命即将消失的每一个时刻,它们一下一下地敲打在人们的灵魂深处,让观众对生命有刻骨铭心的审视:不远的死亡的确是被决定的,从而也是被等待的,但对于一个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死囚来说,他是耗尽生命、还是重新获得对生命之价值的认可和理解?
 电影的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名为海伦的修女,成了为死囚马修·庞斯莱提供帮助的义工。她尽各种努力帮他寻找律师、申请聆讯、上诉和测谎,并充当他的精神顾问,最终以言行感化了他,使他承认自己罪行,向被害者家属道歉,从而平静而有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电影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作为法律题材的影片,它没有关于案件的复杂叙事,也没有法庭上控辩双方激烈繁杂的辩论。它将视角直接切入一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死囚在这死前168小时之内发生的心灵纪事,一种内心如何顽抗、斗争与挣扎,最后如何获得安宁的历程,而引导这一切的就是那个名叫海伦的修女。但说“引导”似乎有些居高临下的味道,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同样的精神撞击和洗礼也发生在海伦修女身上,发生在故事的每一个参与者、以及观众身上。
电影的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名为海伦的修女,成了为死囚马修·庞斯莱提供帮助的义工。她尽各种努力帮他寻找律师、申请聆讯、上诉和测谎,并充当他的精神顾问,最终以言行感化了他,使他承认自己罪行,向被害者家属道歉,从而平静而有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电影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作为法律题材的影片,它没有关于案件的复杂叙事,也没有法庭上控辩双方激烈繁杂的辩论。它将视角直接切入一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死囚在这死前168小时之内发生的心灵纪事,一种内心如何顽抗、斗争与挣扎,最后如何获得安宁的历程,而引导这一切的就是那个名叫海伦的修女。但说“引导”似乎有些居高临下的味道,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同样的精神撞击和洗礼也发生在海伦修女身上,发生在故事的每一个参与者、以及观众身上。
我从这部影片中提炼出四个问题,它们关涉人的肉身与精神、生命与死亡的基本意义。也许我们没有答案,但一旦我们开始正视这些问题,我们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接近意义本身。
马修一直拒不认罪。为什么?
他之所以不认罪,最直接的理由是他认为自己没有受到公正对待。案发当时,他和另一主犯维特洛共同实施了强奸杀人行为,虽然事实上他参与强奸了那个女孩,并将女孩的男朋友杀了,但这一切都是在维特洛的指使甚至威逼之下完成的,最后残忍杀害女孩的也是维特洛。可是在审判中,同伙因为有钱聘请了好的律师,最终使陪审团相信指控其的证据有“合理怀疑”,被判终身监禁,而他自己却要被处死。他认为在这个国家的司法制度中,死囚都是穷人。
但是,在这个直接理由背后,有一个更根本的拒不认罪的理由。那就是他不能以平等、而只能以偏见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他是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当海伦和他一见面时,他就挑衅地问她:“你从没有如此接近一个杀人犯?但你所住的地方住了不少黑人,他们老是在互相厮杀。”他为自己将要躺在那些黑人躺过的行刑台上而大声抱怨。是什么原因让他怀有如此深的种族偏见,将黑人排除在社会之外呢?在海伦修女的追问下,他说自己看不惯大多数黑人的懒散,浪费纳税人的钱。可是他又不得不承认自己佩服黑人斗士马丁·路德·金,并且同样厌恶懒散的白人。他的歧视理由看来并不充分。
庞斯莱的偏见如此根深蒂固,看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他本人一直也都是一个被歧视者。他从小不幸,十四岁丧父,在穷人区工作;他和妻子离异,而正是前妻告发的他;他被人们视为杀人狂,禽兽、天生恶魔,得而诛之。一个不断被这个社会所排斥的人,怎么可能以平等心来看待社会呢?所以他在绝望里充满仇视地说“我对这个政府毫无感情”,接受记者采访时大放厥词,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对的,声称会参加恐怖组织,会炸毁政府大楼,让修女都震惊:“我怎么会帮这样一个人?我一定是疯了。”
这些理由似乎都可以很好解释马修对自身罪行否认。但问题是,这样的理由能成为理由吗?一个人的不幸是否就可以让他有权对别人施加不幸?当你碰到一个所谓的“懒人”、“恶人”时,你是否就能够将之归属于一类懒人或恶人?被社会排斥就一定意味着要排斥社会吗?更何况,当马修有了不幸、恶、冷漠等一类的观念时,其实他也无形中有了关于幸福、善及爱的标准。这些东西并没有从他的经历中消失,比如修女对他的帮助、比如他的母亲和兄弟们对他的关爱,只不过这一切都因为他执着于自己的不幸而被遗忘了。
他越拒不认罪,越证明他并不甘愿自己就此被社会排斥,越证明他对人性尊严中某些东西的渴望,这恰好是让他认罪、获得做人尊严的契机。
影片的将近尾声时,也就是死囚即将处死的那一天,一幕最为感人的对话出现了,马修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我杀了他……”
海伦修女:“他们的死你肯负责吗?”
死囚:“我肯……昨晚我跪在床前,为他们祈祷,以前从未试过……”
“有些伤痛只有上帝才能抚平。你制造了惨剧,但你现在重拾尊严,谁也不能剥夺。你是上帝的孩子。”
“从没人说过我是上帝的孩子,他们都是说我是混蛋。我希望我的死能让对方家长好过。”
“你能为他们做的,就是祈求他们的心得到平静。”
死囚:“我从未得到过真爱,从未爱过女人或任何人,现在快死了,却获得了爱……感谢你爱我……”
从一个极端仇视社会的人转变到这一步,的确让人深感人性的辉煌。但这种转变并不是靠一种纯粹的宗教或道德说教完成的,它经历了激烈的斗争和角逐。当看到马修对社会的极端仇视时,连修女也愤怒了:“你这个笨蛋,让他们更乐于下手。你想过被害人的父母没有?他们的儿女被枪击、中刀、强奸。弃尸荒野。若你家人有此遭遇,你会如何?”可是,从前面马修拒不认罪的态度来看,要想让马修同情死者亲属,实在极为艰难,因为在他看来,死者家属唯一愿望就是让他快点死,所以光靠所谓的责骂是无济于事的。纯粹的仇恨和怜悯都不能让马修认罪和恢复人性,看来只有爱才能让人具有良知。海伦正是靠这种“爱”的信念让马修终于认罪。但这里一定要记住,爱的基础是平等,爱的意义是作为人的尊严。她告诉马修,耶稣的死是一种真爱,是通过自己的爱让那些被忽略的人,妓女、乞丐、穷人等,明白了了生存的价值,使他们终于找到尊重和爱他们的人。“耶稣以爱改变世界,而你却眼看两个青年被杀。”
不仅如此,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爱的力量、精神的冲击不能停留在上面的说服层面,还得靠具体的、外在的表现与行动。要让心灰意冷的死囚知道,这个世上就有这样的人,在他们身上就有着实实在在的人性的尊严。而马修所碰到的修女海伦恰好就是这样的人。导演对海伦的处理是很成功的,没有让她成为一个空洞说教士的形象。她到监狱时没有穿修道服,以至狱长都说“这些人很少见到女性,也许你穿修道服,他们会对你尊重一些。你轻视权威,他们只会依葫芦画瓢。”面对马修的轻佻挑衅,她严正地说:“我来这不是给你娱乐,请你尊重我。”“为何?因为你是修女,戴十字架项链?”“因为我是一个人,所有人都该得到尊重。”实际上,海伦正是靠这种姿态逐渐赢得马修的尊重的,以至他甚至直言告诉她:“我不相信这里的人,但你没有惺惺作态,或对我传道。所以我尊重你。你有胆量,你住在人人带枪的黑人社区。”问题的关键是,一旦充满偏见的死囚终于学会以尊重别人的心态看待人世,那么离他真心忏悔、获得尊严也就不远了,所以我们才终于看到了前面那幕感人的对话。
无论如何,我们的尊严和理性都必须在普通生活中发挥作用。一如科恩所说,尊严的普遍性说明任何人都不是完成某种较高目的的工具。所以重要的是要让他内心真正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而不是别人和社会把罪强加给他的。正因为这种内在精神与外在行动之统一的可能性,才使得海伦对马修的“劝说”管用,而在那段感人对话之前海伦对马修说的另一番话也才能作为促使他认罪的最好诠释:“马修,赎罪不是免费上天堂的方法,只由耶稣负责付出代价。你得对自己得救赎有所承担,你得努力赎罪。约翰福音第八章,你们必知道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若你要死,得让你死的有尊严,若要如此,你就得为沃尔特和霍普的死负责。”
为了不使“认罪”的过程沦为空泛说教的结果,我们还必须追问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我拿什么来拯救你?当然,这里“我-你”的主宾句式容易让人感到一种本文开头所谓的“居高临下”,似乎和我所论述的平等、尊严相矛盾。其实,“我拿什么来拯救你”,更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是自己对自己的拯救,只不过这种对生命意义的困惑和追问最终以这样一个自我反省式的方式表现出来了。同时,拯救者与被拯救者分属不同主体,也不意味被救者精神上的匍匐,关键是如何拯救、为了什么而拯救。
世事维艰,并且容易让人身陷其中不能自拔。我们和这个社会不可分割。生在世上,有些东西是无法选择,从而也无法抱怨的,比如我们的出生,但另外一些东西,我们可以作出抉择,所以我们可以堕落,也可能重生,比如我们的精神。电影中,死囚最后得到拯救的,也就是这精神,只有在精神的意义上,“活着,还是死亡”,才成为一个问题。
作为修女,海伦当然是一个拯救别人的角色。但她的拯救毋宁也是在寻找迷失的自己。母亲告诉她,小时候她曾在发烧时大喊大叫把母亲打得淤青,但母亲的怀抱最终安抚了她。如今,面对死囚庞斯莱,她好像也成了一个母亲。可是,拯救的过程何其艰难,因为她首先面对的就是马修的质问:“你为何当修女?”这话的意思,确切说就是,你凭什么拯救我?海伦的回答表面无奈,实际有力:“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就像你为何当罪犯一样。”这个回答的意思其实是:对于被决定的东西,比如当修女,就像那些无法选择的事物一样,我们恰好是无权质疑的,但正因如此,我们真正能够思考的正是那些可以使我们的精神获得救赎的东西,而且,只有你开始了这个思考,你才能开启拯救的大门。
海伦对马修的拯救当然也必须从代表精神和灵魂可能深度的宗教理解和道德言说开始。电影中已经不止一次展现了她和马修关于圣经理解以及道德良知的辩论,比如对于耶稣死亡的意义的解读、对于受害者家属可能的同情。但局限于此是不够的,一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海伦是宗教的事业者,但她的事业必须植根于这个充满矛盾厮杀的世界中,她对神的认知和对别人的拯救只能是在世的行动。所以,拯救必须在一方面听从自己意识不到的召唤,另一方面要化为“沉重的肉身”,正如母亲对她告诫:“你在寻找真正的博爱,要面对种种风险。天使传报是常事,但道成肉身却罕见。海伦,你不是圣人。”对于海伦来说,这也就意味着她必须接受各种误解与甚至屈辱。被害人家属直到最后也无法理解她为何要与那个杀人恶魔为伍;她在社区“希望之屋”的同事不明白她为何要舍近求远,因为社区希望她帮助的人就有很多,等等。
我们必须强调,正是在沉重肉身的束缚下,海伦所做的并不是为了成就什么高尚,她不过是听从召唤而已。她所有努力的方向,也不过是让死囚马修在死前能听到这种召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都是需要指引的人,即使我们并不知道到底能否获得拯救。海伦的内心在热切地诉说:“主啊,帮助我。这地方多阴森恐怖。这样杀人多处心积虑。别让他崩溃,帮助他与我坚强。帮助我们坚强。”
她是在拯救别人,还是拯救自己?
正是这种精神化为现世行动的拯救过程,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片中好像被忽略的法律拯救的作用。影片里,法律对马修的宣判似乎并没有让他有机会反省自己的灵魂,反而让他的仇视找到发泄的理由;整部电影似乎是想要为死刑的正当与否,或者为超越司法制度进行人的拯救提供宗教的论辩。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如果离开一种法律制度的“宣判”,我们的一切拯救可能发生吗?我们的精神介入了肉体,但它应该进一步深入,介入到决定我们肉体存在的社会制度当中,即,我们一定要寻找如何在现实政治法律制度的条件下拯救人。如果脱离了制度条件,那也就是在用一种割裂社会的方式来试图实现拯救,这和马修与社会之间的互相排斥与仇视实际上是一个逻辑。因此,法律的拯救作用虽然在片中没有用显明的方式加以强调,但恰好说明了其独特的重要性。法律的作用是要使社会团结起来。如果法律没有实现这一点,那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制度机器出现了问题,或者有它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它在死刑问题上的尴尬。但说到底,我们在设计法律这种制度时,其出发点一定是为了使社会团结起来的。至于这种作用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那又关系到我们在具体条件下对法律这种可选择事物之运作方向的理性选择:死刑的存废与否,就是其中值得思考的重要方面。
法律制度对死刑的规定,将私人间弥散的杀人方式收归系统的政治制度,这无论如何是对滥杀的一种约束;死刑执行方式从残忍到人道化的发展方向,也说明法律在不断改进和维护人的尊严;死刑适用领域的不断缩减,也在见证着人类对生命价值的进一步体认。
但是,这部电影并没有抽象地思考死刑应不应该废除的问题,它只是展现出死刑问题的复杂性。正如片中一位狱警所说:“要对行刑程序妄加评论,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表面看起来不合理或不必要的做法,其实有着深厚的理据和长久的经验。”也许这就是电影着意要揭示的东西:一个法律制度之下总会存在不同人在认知层次上的差异,制度不可能期望所有人对生命的理解同一。
海伦修女对死刑的态度其实并不清楚,虽然她的努力就是在捍卫和拯救生命,但她更关注的其实是一个人应该如何去死才能实现生命的尊严;至于死囚马修,在他没有认罪之前,可以说死刑对他是没有起到惩罚作用的,直到他的精神恢复了人的尊严,他才坦然面对死刑,希望自己的死能给被害者家属一些安慰,但这当然不能说是死刑的作用;片中明确表示支持死刑的就是以受害者家属为代表的普通民众。这里且记录片中有关他们态度的三个片断:
片断一: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受害人父母的悲痛照片,一个充满欢笑的家庭消失了,新闻标题是:“父母的伤心永无止境”;片断二:一个人讲述,在某被害人的牙医叔叔将手伸进被害人腐烂的嘴里以确认死者牙齿记录前,他一直反对死刑,但那天之后,他全力支持死刑。片断三:在死囚道歉、执行死刑、举行葬礼后,被害者家属戴先生来到墓地,和海伦修女的对话:戴先生:“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我满怀仇恨。我没有你的信念。”海伦修女:“我有的,不是信念那般简单。也许我们互相帮助,消除仇恨。”戴先生:“我不知道。大概不可能。我该走了。”
法律当然是需要理性和人道的,但作为制度,法律也不得不关注具体个体的感受,关注他们的爱恨。法律统治之下的大部分人,都是凡夫俗子,他们不能超越一定时空条件决定下的感受去理性批判一种制度的得失,去评判他们的行为是否具备足够的理性和尊严。法律终究是实现正义的工具,所以法律的核心命题就是正义有没有得到伸张;正义如何得到伸张。而这两个命题都无法脱离个体的存在和个体的感受,这种存在和感受往往决定着人的思考限度。不过,电影毕竟为死刑本身的不正义性提供了超越歧视、偏见和仇恨而进行理性思考的方向,那就是马修临刑前说的话:希望自己不要带着仇恨离开人世,也希望自己的死能给他们带来些许安慰,“我只想说……杀人是错的,无论杀人者是我、你们、你们的政府……”
是的,不要杀人。也许谁也没有权利杀人,特别是处心积虑的杀人。
以上四个问题或许可以归结为一个最终的问题:如何向死而生。影片最后的镜头不断交错切换,那是不同的死亡瞬间:死囚的脸、墙上的钟、自动注射机的启动、犯罪现场杀人场面、两具被害人的尸体,等等。无论什么方式的死亡,天灾、人祸、自杀、他杀,可选择的、或不可选择的,都在逼迫着人的心灵,我们对待死亡的态度也许才是照耀我们心灵的镜子。海伦修女用爱与坚毅对“向死而生”做了最好的阐释。在一场让死囚和自己都同样经历的精神洗礼之后,海伦回到了工作的地方,她看到孩子们在墙上写的话:“we love you sister Helen.”(我们爱你,海伦嬷嬷),这句话足以让她欣慰一生。真的,这正是电影要告诉我们的答案:人性可能得到提升,我们可以获得拯救。
“向死而生”,这是一个问题,一个真正严肃而有意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