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象:修宪与戏仿——答记者问
又到了修宪的季节?你们记者是候鸟,一飞回来,风景跟着就变……
谢谢,过奖了。怎么说呢?我没什么“专家意见”,不够格。不过修订《宪法》这事其实跟法律也没多大关系;修不修,怎么修都行——不如修大坝拆民房后果重大,需要公开的不受拘束的包括尖锐批评的辩论——比方说许多人关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句是否入宪。这是老问题了,上一次(一九九九年)修宪就议论过。“私有”了,还要“神圣”,无非是不满意《宪法》只讲“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二条)。这些人认为,现在到了为私有财产争平等待遇的时候了。实际上,入不入宪,对公民合法财产的法律地位和司法保护不会有丝毫影响。为什么?因为《宪法》条款没长“牙齿”:法院不能援引《宪法》对任何政府行为包括立法做违宪审查,当事人也不能依据《宪法》提出诉讼抗辩的主张。《宪法》缺一个进入司法操作的程序安排,跟真实世界的宪政生活是脱节的。所以我说过,《宪法》只有在统编教材里才是法律规章的“母法”(见《它没宪法》)。所以你看,入不入宪,纯粹是一个政治决定。或者说,是私有财产这句口号,这面大纛,这一整套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在转型社会中的政治合法性,需要找恰当时机以恰当方式宣示一下。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有朝一日,这句口号真入宪了,也不要以为你买下的房子、兜里的手机、接发的短信、每个月的奖金、你的饭碗身价之类,会突然“神圣”起来,别人不敢碰了。
对,一切照旧。包括老板的脸色、局长的旨意,一切不用《宪法》规定就已经不可冒犯的东西。一切虽然《宪法》禁止,却仍然畅行无阻的东西。
但是,入宪没有法律后果,不等于公民权利的界定和保护不产生宪法问题,不需要好好研究、慎重处理。道理很简单:《宪法》缺席,必然有其他纲领性规范文件到场指导。这些年来,农村的各项改革,从家庭承包制到费改税试点,不都是中央出台政策,发红头文件指导的?国有企业破产、工人下岗、城乡土地转让划拨,也从来不用考虑《宪法》。然而这些举措关乎民生大计,包含宪法问题——那些《宪法》没法管的问题:你想,要是当真把第十二条“公共财产神圣”严格执行了,中国社会还不倒退四分之一个世纪!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宪政的实践跟《宪法》的文本不是一回事,反而像“两股道上跑的车”,不碰头。《宪法》本本那几页纸,能保护什么禁止什么?哪怕年年修订!宪法原则的实现,归根结蒂,靠的是公民的广泛参与和公正独立的司法。所以没有成文宪法,照样可以有发达的宪政传统和违宪审查制度,例如英国。问题不在一句口号、一种观点是否入宪,做成条款;而在这些响亮的语词背后的价值理念,能否进入社会生活,为执法和司法者所尊重,成为政法实践的惯例,即成为一个个具体的诉求抗辩、法律解释,乃至公共政策与公共辩论的依据。
这方面的案例?有一些。你敲门进来之前,我正在读一个案例,是清华一位教授编的,叫作“青岛三考生诉教育部(高考分数线)违宪案”(王振民编《中国宪法案例教程》,页45以下)。你们报道过?那是典型的公民宪政意识的表现,虽然三名考生(原告)向最高人民法院投诉之后,没有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被告教育部所在地法院)正式起诉。
是的,原告认为,山东省高考录取分数线定得高,北京等地定得低,教育部这一规定侵犯了原告(山东考生)受教育的权利(《宪法》第四十六条)。
为什么终止起诉?说是引起各方关注的目的达到了。很现实,对不对?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撤诉率一向高。很难。有时候,让你赢你也赢不起,赢了反而“困惑”,像秋菊那样,后悔莫及。
宪法权利,和毛主席说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一样的,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在实践中认识,一点一点争取。然而到了法治时代,天天宣传立法,许多人被它搞糊涂了。以为抄几句话在纸上,开几次会吃几桌酒席,发发言举举手,就大功告成了。
明天下午我有一讲,讲版权和文学创作,题目叫“《围城》与《飘》”。你也听说了?……
是很有意思,但我不能把讲座内容事先披露给传媒了,对不对?
没错,向你披露,不违法也不违约。但这样做不好,违背惯例和学生的期待……谁说的,只要不违法什么都可以干?随地吐痰违法,性贿赂不违法。伤天害理的事情,百分之九十法律不管。实际生活中,除了办案子的律师,谁说话办事是对照法律本本的?你找不出来。你到楼下看看,熙熙攘攘,遍地法盲。我们每天做出的大大小小的决定,多半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或宗教信仰熏陶约束的结果。不然,陌生人之间就无法信任也不可能合作了(参见艾里克森《秩序不用法律》)。所以国家立法,不能随便破坏民间的传统和惯例。这个题目,我准备有空也写一写(见《取名用生僻字该不该管》)。
传统惯例是重要的公共利益。如何理解?让我想想。有了,杭州《江南》杂志今年第一期那个“风流版”《沙家浜》,你们怎么报道的?
这件案子涉及我刚才讲的宪法的价值理念,可以谈谈。
那个“风流版”,用杂志主编的话说,是一部中篇“试验文本”,借用革命样板戏的剧名,旨在探索“米兰.昆德拉说的”人性的多种“可能的存在”(东方网2003.3.23转载《新闻晨报》采访记)。结果,闹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批评者认为,如此“戏说”《沙家浜》太离谱了:居然把机智勇敢的阿庆嫂写成一个“潘金莲”;她丈夫“在上海跑单帮”的地下党交通员阿庆,做了“武大郎”;新四军指导员,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的郭建光,倒在阿庆嫂裙下演“哈巴狗”;而反面人物“忠义救国军”胡司令却摇身一变,俨然一名抗日“英雄”兼阿庆嫂的“老相好”。也有网友指出,“风流版”打的主意,是制造争议“拉动杂志的发行量”。二月底,(江苏常熟)沙家浜镇举办一个“小说《沙家浜》评论会”。与会者一致表示,小说不仅“严重侵犯”原作(沪剧《芦荡火种》)的知识产权,伤害了全国人民的感情,“还侵犯了沙家浜全体民众的名誉权”。镇长宣布,要拿起法律武器,状告《江南》杂志及小说作者……
名誉权我等会儿讲。我先问你,你怎么看,《沙家浜》(原名《芦荡火种》)仍在著作权保护期内,能不能“戏说”?要杂志和小说作者认错,错在哪里?
说得好。“戏说”样板戏作为政治问题,可以追究的责任确实有限。即便上纲上线,把小说定性为“歪曲革命历史、亵渎民族精神、丑化党的领导”那么一株“大毒草”,小说作者和杂志主编也不用担心,像从前那样,一夜之间变成“专政对象”抓去劳改。那是老昆德拉承受不起的“生命之轻”。时代变了。现在的小昆德拉作完检查,照旧写他的小说、编他的杂志。不是吗,人民网就有不少帖子,反对乱扣帽子和“语言霸权”,希望批评者多一点宽容。你看,人们没有忘记过去,政治统帅文艺那个惨痛教训。其实,沙家浜镇长说,考虑采取法律手段,就很说明问题:新时代的正义,是要在法律上找着一个说法,获得一种结果,才让人感到名正言顺、心里舒坦的。
注:据报道,四月九日,《江南》杂志社的主管部门浙江省作家协会受“省委宣传部的责成”,召开“专门会议”,让主编向沙家浜人民和新四军老战士赔礼道歉,并答应在杂志上刊登“认错书”,虚心接受读者的“批评与帮助”(新浪网2003.5.9转载《羊城晚报》)。但批评者之一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拒绝接受道歉。七月十五日,《江南》刊出给“所有读者、新四军老干部和‘沙家浜’的父老乡亲”的道歉信。信中承认:“不应该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以完全错误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所谓‘试验文本’来取代严肃的革命文学……丧失了应有的政治敏感性,导致政治把关不严……小说《沙家浜》的发表,引起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并且表示,杂志主编已向省作协党组递交了辞呈。主编解释,自己“仍然是新四军的儿子”,但因为杂志经费短缺,苦于拉赞助,今年不想再干了;再说“我不提出辞职,这个事情就不会有结束的时候”(《南方周末》2003.7.17,页C21)。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如何看待“戏说”《沙家浜》这类纠纷呢?
首先,作为一项宪政原则,政府部门应当尽量少管(但有义务资助)文艺。这一点我想决策者不难接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文艺的管制与利用,借助商业竞争、利润引诱和民事手段,要比直接干预来得温和也有效得多(见《诽谤与创作》)。其次,按照诉讼程序,请求司法救济的个人或团体,必须是能够行使诉权、跟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合格诉讼主体”(见《鲁迅肖像权问题》)。并非只要遭到经济损失或精神伤害,就可以告状索赔。比如,以“百万沙家浜人民”的名义起诉《江南》杂志侵害名誉权,法院恐怕难以受理。因为“戏说”阿庆嫂、胡司令等虚构历史人物,不论有无原型,跟今天江南某镇全体或部分居民的名誉或人格尊严是否受到贬损,实在隔了几层。说白了,法院不是神仙,它不能伸手太长,什么都管一切都判。否则北京的老舍茶馆为骆驼祥子的名誉尊严也可以跟人打官司了;更不必说,不久前传媒报道,某统编历史教学大纲不称岳武穆为“民族英雄”,亿万同胞所感到的震惊、愤怒和精神痛苦,该引发怎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美式”集团诉讼,叫那些四处征集“尼古丁受害者”签名,叮着烟草公司吸血的老美“牛虻律师”都自叹弗如!
不好理解?你是觉得不够公平吧;可惜,“民愤”不产生诉权。其实最有资格行使诉权的,反而不在杂志社开会道歉的对象之列,你猜是谁?《沙家浜》著作权人。不管怎么说,“风流版”的标题、故事角色、部分情节和对话,都“借”自《沙家浜》,未经授权,并且有可能损害原作作者(已故)与著作权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所以,如果合格权利人以侵犯著作权及相关权利(如不正当竞争)为由起诉,法院不能不管……
行,就说著作权(版权)。你觉得“戏说”免不了改动原作的人物故事,会影响原作的“形象和销路”,完全正确。销路涉及市场竞争,等一下谈。先说形象。作品形象在商业社会当然有商业价值(销路),但它首先是作者的一种人格或精神利益。法律规定,作者有发表、署名、修改作品和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等四项“精神权利”(《著作权法》第十条)。所以“戏说”对原作的改动,除了可能需要授权,还可能触及原作作者的精神权利。后者是独立的不可转让的权利,跟“戏说”是否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无关。例如改编剧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原作是否受到歪曲篡改,取决于“主要思想、主要情节和主要人物关系”有无“实质性改变”(“陈立洲、王雁诉珠江电影制片公司……著作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1990)。该案认为,电影《寡妇村》的导演(被告)为“实现剧本意图、提高影片质量”,改写分镜头剧本,增删原作作者(原告)认为关键的一些故事情节、对白、场景及人物动作,不算歪曲篡改。因为这些改动对剧本的“主要思想、主要情节和主要人物关系”未作“实质性改变”,属于“必要的改动”,在“电影导演艺术再创作的权限许可范围内”(参见《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条)。同理,如果我们把“戏说”《沙家浜》看作一种改编,则无论授权与否,只要“风流版”不尊重原作的主要思想、主要情节和主要人物关系,另搞一套,即是侵权……
“戏说”古人会不会侵权?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古人的作品,如《红楼梦》,当然属于公有领域。但是,作者的精神权利(发表权除外)与一般版权(财产权)不同,是一种享有永久保护的特权(《著作权法》第二十条):作者去世后,由他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行使;无继承人和无人受遗赠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这条规定,使得作者的部分人格利益(署名、修改、作品完整性)的保护力度和期限,大大超过了名誉权、肖像权等民法上的人格权(详见《孔夫子享有名誉权否》)。因此按照著作权的回溯保护原则,至少在理论上,今人是可以替古人主张这些精神权利的。有点不可思议吧?举个例子你就明白。鲁迅先生逝世超过五十年了,作品落入公有领域,复制出版翻译改编,都不用授权许可。但假如有人将《阿Q正传》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或随意“戏说”,人物故事完全颠倒,就侵犯了鲁迅的精神权利。他的继承人有权起诉追究侵权责任。那么这一原则能不能上溯到《红楼梦》,到《史记》呢?假如我们改写《红楼梦》,或者拍电影“戏说”《荆轲刺秦王》,会不会侵犯曹雪芹或太史公的精神权利?这两位伟人如果没有继承人在世,版权局能不能干涉我们的改写和“戏说”,例如下令禁止呢?
要是古今作者的精神权利真的享有永久保护,让子子孙孙或政府部门替他们维权,我们就干脆别想改编这事了。创作自由即言论自由,是重大的公共利益,不能被精神权利无限期地阻碍。这是一条宪政原则。我换一个角度讲。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风流版”说是“戏说”,其实并非单纯的改编再现,往剧本里添些细节,对话变叙述,写成小说;也不是演绎清宫野史,拖着辫子演肥皂剧。它属于一种传统文艺创作方式,小说绘画音乐舞蹈都有:就是拿原作里最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情节对白场景等等,加以摹仿、夸张、戏谑、讽刺,新编一个跟它唱对台戏的故事,通称“戏仿”(parody)。戏仿通过刻意安排的对比,让读者一下就看出了原作的影子,从而刺激他的想象,达到取笑、批评、颠覆原作的思想情调和立场的目的。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戏仿和改编的这一点不同,能否抗拒著作权,包括原作作者的精神权利,做戏仿作品的作者或出版者(被告)的抗辩事由?
 著作权官司有一种常用的抗辩,叫作“合理使用”。“合理”,意谓兼顾了各方利益,是著作权(通常解作刺激作者创作的产权收益)和自由使用作品的公共利益之间,多方“谈判”妥协的结果。公共利益可以转化为公民权利,反之亦然;言论自由、创作惯例、公平竞争等都是。《著作权法》允许,“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第二十二条)。这一条规定既维护了言论自由,也是对传统的作品使用方式(引文)的尊重。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nam et ipsa scientia potestas est)。力量何在呢?在传播和使用。人类寄予知识的理想,是自由传播自由使用,知识为天下公器。这在现代宪政,便是要知识不受禁锢,成为政治民主和个人选择的基础。还有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文艺创作:文艺家不可能脱离前人的思想表达而“自由”创作。“诗只能从诗中制造,小说也只能来自小说。这一点在文学同化于私有产业之前,本是无须多说的”(傅莱《批评之解剖》,页96)。换言之,著作权制度强调作品原创、作者天才,把作者视为一个个孤立的产权主体,实际是颠倒现实,构筑一种抽象物上的产权神话(意识形态),遮掩了文学艺术的基本性格:摹仿。
著作权官司有一种常用的抗辩,叫作“合理使用”。“合理”,意谓兼顾了各方利益,是著作权(通常解作刺激作者创作的产权收益)和自由使用作品的公共利益之间,多方“谈判”妥协的结果。公共利益可以转化为公民权利,反之亦然;言论自由、创作惯例、公平竞争等都是。《著作权法》允许,“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第二十二条)。这一条规定既维护了言论自由,也是对传统的作品使用方式(引文)的尊重。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nam et ipsa scientia potestas est)。力量何在呢?在传播和使用。人类寄予知识的理想,是自由传播自由使用,知识为天下公器。这在现代宪政,便是要知识不受禁锢,成为政治民主和个人选择的基础。还有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文艺创作:文艺家不可能脱离前人的思想表达而“自由”创作。“诗只能从诗中制造,小说也只能来自小说。这一点在文学同化于私有产业之前,本是无须多说的”(傅莱《批评之解剖》,页96)。换言之,著作权制度强调作品原创、作者天才,把作者视为一个个孤立的产权主体,实际是颠倒现实,构筑一种抽象物上的产权神话(意识形态),遮掩了文学艺术的基本性格:摹仿。
有了这样一套意识形态,知识的社会生产、流通和使用,知识的力量的控制与操作,才能采取产权的形态。所以“合理使用”也可以这么理解:为防止抽象物(作品)上设立的产权过度膨胀,压抑或损害公共利益和公民基本自由,任何产权不得未经谈判即划定疆界而拒绝公有。
戏仿算不算“合理使用”呢?戏仿同各种改编或野史式的“戏说”的差异,主要不在形式和技法,而在它对原作的摹仿、戏谑和批评的社会意义,亦即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艺传统、言论自由等公共利益及宪法价值。尽管戏仿要借用原作的文字和风格,“戏说”其中的人物故事,在司法审查中,就其社会意义而言,它反而比其他种类的改写和“戏说”更值得保护。在美国,版权纠纷中戏仿作品的“合理使用”抗辩,就往往跟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相提并论,成为非常有力而灵活的抗辩。而“法院应该避免生硬地适用版权法,以免压抑了那本该由法律扶植的创造力”(联邦最高法院苏特大法官语,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 510 U.S. 569 [1994])。这句话说得十分得体,拿来做人民法院的司法原则,我看也错不了。所谓“本该由法律扶植的创造力”,指的正是文艺创作中那些与产权神话相冲突的做法,包括戏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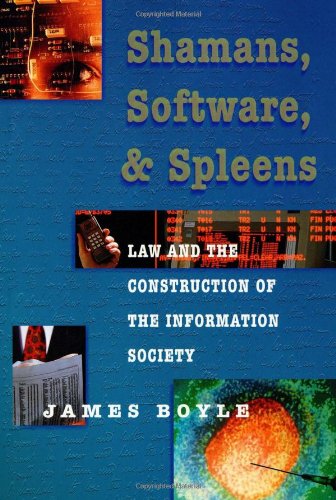 真的,研究知识产权的乐趣就在这里:人类那么多创造发明、思想表达和名称标识,进入资本的“新纪元”,用资本的语言来解说,就一下都成了“神圣”的私有财产的故事。然而知识产权纠纷有这么一种趋势,它经常迫使学者、法律家和决策者回到法治的前提,重新面对抽象物上产权的性质和矛盾,重新解释诸如产权可以鼓励创造发明、丰富社会思想之类的神话(参见博伊尔《巫师软件脾脏之属》,页19)。
真的,研究知识产权的乐趣就在这里:人类那么多创造发明、思想表达和名称标识,进入资本的“新纪元”,用资本的语言来解说,就一下都成了“神圣”的私有财产的故事。然而知识产权纠纷有这么一种趋势,它经常迫使学者、法律家和决策者回到法治的前提,重新面对抽象物上产权的性质和矛盾,重新解释诸如产权可以鼓励创造发明、丰富社会思想之类的神话(参见博伊尔《巫师软件脾脏之属》,页19)。
在中国,还要加一句:重新关注社会生活中一些宪政原则的缺席。
乍一看,这缺席似乎得归咎于《宪法》,因为它不能进入诉讼。但根本上,恐怕还是把产权看得太“神圣”了,忘记它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和公民基本自由,没有把与之冲突的文艺传统、言论自由等看作应受法律保护的重要价值。没有意识到,一方面,公民权利的产生、发育和保障并不依赖《宪法》本本;另一方面,这些权利作为宪法价值,是可以积极争取,转化为执法和司法的政策依据的。结果,不仅《宪法》本本在宪政实践中缺席,宪法权利所代表的价值理念,及其向民事权利和诉讼抗辩程序转化的探索,也跟着缺席了。于是,法制改革陷入立法主导的法条主义泥淖,便不奇怪了。
当然,“合理使用”抗辩的“宪法化”(强调宪法价值并以宪法解说),并不等于被告(戏仿者)自动得胜,产权和精神权利不受尊重。这些权利只是受了限制,对言论自由、创作惯例等公共利益适当让步,视纠纷的具体情节划分权界。实际上,原告(原作作者和著作权人)也可以主张公共利益即公平竞争。因为,在资本自由准入的商品市场上,依存产权而“自由”了的言论也是商品,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反对搭他人作品的便车,剽窃他人文字,“戏说”他人故事。在“合理使用”与公平竞争之间,也有平衡利益而“宪法化”的问题。所以这方面常有“难办”的案子,不但中国,美国也在探索之中(见《案子为什么难办》);例如视原作(戏仿对象)的版权保护年限、版税收入、社会影响等因素,综合衡量戏仿的合理性,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等等。明天下午要讲的《飘》的戏仿案便是一例……
中国的第一例?“风流版”算不算你理解的那个“第一”,我不知道。我关注的是知识产权和其他类型纠纷中,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及争议的“宪法化”趋势。近年来为私有财产修宪正名的呼吁,可看作这一趋势的背景。实际上,日常生活中,在我们周围,产权早已是吸纳、部署、分配公民权益的政法策略的中心环节了,例如版权对作者、作品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意义的排斥。其实现的前提,我在别处讨论过,乃是要我们、要整个社会忘却并重写历史(见《法盲与版权》)。既然如此,为利益平衡计,似乎就应当允许戏仿者以“合理使用”和言论自由抗辩,尽管有人借戏仿赚钱,搭便车牟利。比如“戏说”《沙家浜》,是不是“拉动杂志发行量”的商业伎俩?这大概不难查明,但商业目的不是过错。“风流版”有没有社会意义呢?不能说一点没有;关键是它妨碍了什么人的什么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读者对戏仿作品的理解,跟戏仿对象(原作)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象征意义是分不开的。《沙家浜》演过什么角色?样板戏象征什么?据说,巴金老人曾有这么一句回忆:“我一听到样板戏,就感觉自己的脖子被一双手死死卡住”。的确时代变了,如今那令人窒息的“高大全”也归化了产权,要求重新定义、法律保护,以便拒绝戏仿。戏仿又意味着什么?
面对“神圣”如此的产权,我们怎么办?我想,我们第一不能忘记历史,真实的一点不神圣的历史。
第二,我们有责任把以“神圣”为名颠倒了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
二〇〇三年四月
本文收于《政法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