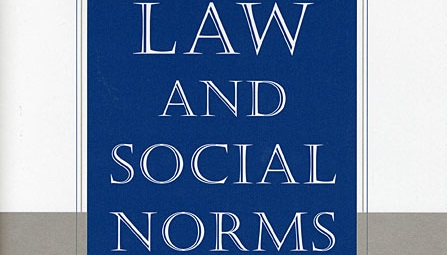
沈明:“世道在变”——法律、社会规范与法学方法论
[本文系埃里克·波斯纳《法律与社会规范》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译者前言。]
在今天的中国法学界,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的名字已经堪称家喻户晓了。不过,知道波斯纳的儿子、本书作者埃里克·波斯纳(Eric A. Posner)的人恐怕还不会很多。我先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埃里克·波斯纳生于1965年,本科和研究生就读于耶鲁大学,1988年以最优等成绩(summa cum laude)获得哲学专业硕士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1991年以优等成绩(magna cum laude)获得法律博士(J.D.)学位,同年获得马里兰州律师资格。毕业后的第一年,他担任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斯蒂芬·F. 威廉姆斯法官的法律助手(Law Clerk),然后又在美国司法部工作一年。1993至1998年,波斯纳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98至2002年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2003年起任该学院柯蓝和埃里斯(Kirkland & Ellis)(讲席)法学教授。波斯纳教授还是美国法律经济学协会(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Association)会员,著名学术期刊《法律研究杂志》(Journal of Legal Studies)的编辑。——在美国,这几乎是法律学术精英的标准履历,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平淡无奇”的。
埃里克·波斯纳生于1965年,本科和研究生就读于耶鲁大学,1988年以最优等成绩(summa cum laude)获得哲学专业硕士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1991年以优等成绩(magna cum laude)获得法律博士(J.D.)学位,同年获得马里兰州律师资格。毕业后的第一年,他担任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斯蒂芬·F. 威廉姆斯法官的法律助手(Law Clerk),然后又在美国司法部工作一年。1993至1998年,波斯纳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98至2002年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2003年起任该学院柯蓝和埃里斯(Kirkland & Ellis)(讲席)法学教授。波斯纳教授还是美国法律经济学协会(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Association)会员,著名学术期刊《法律研究杂志》(Journal of Legal Studies)的编辑。——在美国,这几乎是法律学术精英的标准履历,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平淡无奇”的。
《法律与社会规范》是波斯纳教授的第一本学术专著,200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美国法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1] 法律与社会规范研究是一个相对新兴的学术领域,通常,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法律经济学的一个延伸或者支脉。不过,在美国法学界,人们对于规范理论(norm theory)的方法论地位还存在一定争议:耶鲁法学院的罗伯特·埃里克森教授——他的《无需法律的秩序》[2]一书是当代“法律与社会规范”研究的奠基性著作——认为,依社会科学进路来研究法律的规范理论是一种取代了法律经济学的(托马斯·库恩意义上的)研究范式的转换;[3] 而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只有当一种理论不能为当下的研究者提供可接受的答案时,才会发生研究范式的转换,而法律经济学的情况并非如此,相反,它在不断地调整、丰富自己,以应对新的问题或者以前无力解决的问题。法律经济学几十年来的发展一直沿用着同一种基本的研究范式,即理性选择理论;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等都可以看作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拓展和延伸。[4] 事实上,在“法律与社会规范”领域,除了埃里克森教授1991年的那本被誉为开山之作的《无需法律的秩序》之外,真正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理论专著迄今为止恐怕也只有这本2000年的《法律与社会规范》了,[5] 即使从这个角度来说,像埃里克森那样现在就断言研究范式的转换,恐怕也为时尚早。退一步说,不论规范理论到底具有怎样的方法论地位,人们都公认它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斯坦福法学院的劳伦斯·莱西格教授(曾经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甚至提出,在以对法律与(以社会规范为代表的)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综合研究为特色的芝加哥学派内部,已经有了新旧两派之分,换句话说,出现了一个“新芝加哥学派”[6],而埃里克·波斯纳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法律与社会规范的研究牵涉到一些源流久远的法学理论问题,最典型的,例如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不过,法律与社会规范研究与传统法理学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它采取的是理查德·波斯纳所谓的“科学”而非“哲学”的进路。[7] 关于方法论的转换和创新问题,下文还要展开来谈,这里我想先提请读者注意一个虽然琐屑但却未必不重要的细节:作者在这本书中采用的注释体例是正文圆括号夹注(parenthetical references)加书末文献列表的方式,即[社会]科学文献的通行注释体例,而没有采用传统法学和人文学科文献常用的那种脚注或尾注的注释体例。[8] 在学术规范较为完善的西方学术界,这一“细枝末节”或许并不真的就是无关紧要的,我们至少可以从中透视出作者自己对本书的学术进路和方法论所作的定位,有了这种把握,我们才能够看清这本书在学术的“世界地图”中所处的位置,进而才可能更好地理解它甚至批评它。而且,如果可以“小题大做”的话,我甚至想说本书是一个信号,它标志着大约一个世纪以来的法学学术转向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也许有读者会问:“法学的什么学术转向?”这里所说的法学学术转向是指“法律作为一个自主学科的式微”和法律交叉学科研究的兴起。
“对于法律的理性研究在今天可能属于和白纸黑字打交道的人,但是未来它却会属于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9]——O. W. 霍姆斯法官在19世纪末做出的这一预言虽然难免让法律人略觉尴尬,可如今也已经是法律人耳熟能详的名言了。20世纪下半叶法律经济学运动在美国的兴盛发展为霍姆斯的伟大预言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证明。[10] 1960年代以来,除了法律经济学之外,法律与社会学、文学、政治学、女权主义、种族理论、社会生物学等法律交叉学科研究的兴起标示着法学研究开始了全面的、革命性的转型。1987年,理查德·波斯纳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文章,正式宣布了《法律作为一个自主学科的式微》[11]。
虽然法学的这种学术转向是大势所趋,但却并非一帆风顺。在《法律作为一个自主学科的式微》一文发表十年之后,即1997年,在纪念霍姆斯的名文《法律之路》发表一百周年的哈佛霍姆斯讲座上,理查德·波斯纳重申了他所倡导的科学主义、交叉学科的法学研究进路,并对法学及其他所有规范研究中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进行了几乎是毫不留情的学术抨击。在此基础上,1999年,他出版了自己的法理学三部曲的“终曲”——《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正如波斯纳法官自己所说,就作为规范研究的法律学术而言,多年来他反复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其实,波斯纳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正反映了传统法学范式的惯性与惰性,反映了学术变革的艰难。
可是不管怎么说,“世道在变”,“旧”终究要“让位于新”,因为即使“一部好惯例用久了”,也难免会“坏了人间”。[12]
作为美国法律经济学运动的第三代传人,埃里克·波斯纳教授不但继承了这一使“旧让位于新”的事业,而且在这条路上做出了自己的前沿性的贡献。在本书中,波斯纳开创性地构造出了信号传递-合作模型,依贴现率的差异把理性行动者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博弈参与人,将博弈论的理论资源应用于社会规范的分析,从而大大地拓展了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并对大量的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提出了富有创见和启发意义的分析,其中包括:礼物赠与、慈善捐赠,利他主义,社会地位,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功能,恋爱、婚姻、家庭(包括离婚、婚内纠纷、私生耻辱、同性婚姻),刑罚的耻辱效应及其利弊,犯罪学中的威慑模型与规范模型的统一,麦卡锡主义,尊敬/亵渎国旗,来自政府与社会的审查制度,投票,符号行为,行为的社会意义,罚金刑与自由刑的不同信号效应,种族歧视,社群与民族的建构/虚构特征,商业合同的形式,损害赔偿,交易惯例,社会规范与效率、分配正义问题,人们的不可通约性断言的姿态,商品化的社会现实,个体的自治权,法律对社群的影响,社群的衰落……即便我的列举带有一定的随意性而且是不完全的,这已经足够令人吃惊了:您能想象吗!?除了已经“帝国主义”的标准经济学模型之外,作者竟用一种模型解释了如此广泛的理论问题!
尽管本书处理的问题纷繁复杂,但作者的分析始终没有离开本书的核心问题:“……人们为什么会遵守社会规范?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无法理解法律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13] 本书的主题是法律与“合作的非法律机制”的关系,而激发这一研究的动因在于作者对于既有的法律经济学理论的一些不满。作者坦言,自己的研究属于一个可以追溯到法律现实主义的理论传统,该传统排斥“那种过分专注于国家,简化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分析简单问题、排斥重要及有趣问题的法律学术研究”。不过,“这一研究传统的影响却因一个重大的失败而受到限制,即这一派批评家没能针对他们所批评的方法论给出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作为替代。部分地因为这一失败,使该传统的影响尽管不是毫无声息,却也并不总是积极、明确的,”作者直截了当地指出,“学者们需要的是一种能够系统分析法律与非法律合作机制的关系的方法论。”(第5-6页)因此,作者为本书设定的首要理论任务就是贡献出这样一种方法论。
然而,多少有些吊诡的是,反对“简化”的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方法论同样受到了“简化论”(reductionism)的批评。[14] 应该说,这样的批评并不是毫无道理的,“简化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所有经济学理论进路的“通病”。(不然,它何以能“帝国主义”?)可这也正是学术事业的“本分”:社会科学的理论任务是解释,除了解释力之外,理论的价值还在于简约(归纳、演绎)。(比如,请想一想E=mc2。)[15] 笔者在一篇小文中曾经谈过,“现实的世界是无限复杂的,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事实证明,只有简单的理论模型才可能解释复杂的现实,以复杂的理论去应对复杂的现实,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也少有意义”。
如果我们接受卡尔·波普的“证伪理论”的话,那么“简化论”本身可能就算不上是什么缺陷。当然,正如理查德·麦克亚当斯教授在其书评文章中所指出的,“简化”应该有一个合适的限度。可关键的问题是,怎样的限度才算合适呢?——学者们的理论分歧常常发生在这里。波斯纳教授其实已经预见到了这样的批评,不过他或多或少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他强调,本书的贡献主要在于方法论的构建,并解释说:“理性选择理论可以通过聚焦于生成行为规律的声誉上的根源——而不是认知和情感上的根源——来阐明社会规范。我不主张理性选择理论能够为社会规范或者合作行为提供一种完满的解释。认知和情感并非无关的因素。只是它们尚未被心理学家充分理解,因此还不足以支撑起一种社会规范理论,一些人对认知和情感的重要性的一再重复但却令人迷惑的认同搅乱了对于论点的阐释,却没有带来任何补偿性的益处。”(第46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这段话正是波普的“证伪理论”科学哲学观的一个注脚,字里行间似乎蕴含着一种历史感:“过客”是所有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波斯纳教授的这本《法律与社会规范》是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它从属于由霍姆斯一百多年前的伟大预言所揭幕的那个法律学术传统,并且把法律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当然,您也可以说,“承前启后”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定语,因为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所有的著作(尤其是社会科学著作)都是“承前启后”的。这我同意;然而,我所谓“承前启后”的涵义还不仅限于此:我想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在上面这段话中,作者毫不含糊地认同了“认知”、“情感”这些心理学、生物学因素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也许“说者无意”,但我认为这至少暗示了法律学术的一个新方向:即从“法律与社会科学”到“法律与科学”的转向,尤其是法律与社会生物学的交叉研究。
其实,早在1976年(即爱德华·威尔逊的名著《社会生物学》[16]出版后的第二年),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霸业”立下汗马功劳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就曾指出,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定植根于“人性”,这实际是回避问题的托词,[社会]生物学的发展表明,“人性”只是解决问题的开端而非结束。[17] 毫无疑问,贝克尔本人正是一位跨学科研究的开路先锋。现在,大多数学者应该都会同意: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跨学科的,学科名称有时候只是一些标签而已。重要的问题是,跨学科研究到底应有以及能有怎样的“跨度”?科学家兼小说家C. P. 斯诺在1959年提出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此后,“两种文化”[18]的观念就深入人心了。然而,自1970年代以来,以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为首的一些知名学者提出了融合“两种文化”的主张,例如,威尔逊在其另一部名著《论人性》的《序言》中写道:“《社会生物学》一书的出版促使我更广泛地阅读论述人类行为的文献,参加了许多研讨会,并和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相互交流文献。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填补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的时代终于到来了。普通社会生物学——它只是群体生物学和进化论向社会组织的延伸——是完成这一努力的理想手段。”[19] 1998年,威尔逊出版了《协同:知识的统合》[20]一书,更为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关于知识整合的主张和展望。[21] 人,首先是物理性的、生物性的人,然后才是社会性的人。可以预见,而且我相信未来的学术史也会证明,所有的“以人为本”的学科的发展都将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生物学建立“联姻”关系。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其实正是“词”向“物”回归的过程,尽管“人不是而且也永远不会是自己命运的主宰”[22],然而人显然不应该也不会——如福柯所言——像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一样被抹去。[23]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一切听来过于玄虚,其实并不玄虚。
我们知道,20世纪后期以来,经济学已经发展为高度数学化的理论领域了,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中也大量运用了统计学等数学工具和方法,这些都是社会科学学科融合自然科学理论的典型范例。在本书中,作者所运用的主要理论工具就是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的博弈论,这实际上就是法学的数学化——在法律经济学已经成为常规科学之后,这样的学科发展趋势实际上是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事。由此可见,在由“法律与社会科学”到“法律与科学”的转向过程中,本书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余下的路,通往法律与[社会]生物学的路,作者则留给了未来。也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本书是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
当然,本书的贡献还不仅仅在方法论这一个方面。
作者为本书设定的目标一共有三个,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第一个目标是展示博弈论的概念对于理解法律问题的价值。……一个更具野心的目标是使读者相信,我所构建的旨在阐明一系列法律问题的博弈论模型是有用的。第三个目标是使读者接受关于法律与非法律形式的规范之间关系的几个实质性论断。”(第7页)除了前两个关涉方法论的目标之外,作者还在法律与社会规范方面贡献了实质性的智识增量。通读全书,我们会发现,作者的三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融合在一起的:一方面,虽然致力于方法论的建构,但作者的论述并没有流于纸上谈兵或者表演学术“屠龙术”,而是时时将自己的分析深入到上文列举过的那些具体的、“鲜活的”问题中去。另一方面,作者提出的信号传递-合作模型本身也不是凭空建造的“空中楼阁”,相反,该模型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基本生活经验,实际上是对人们熟视无睹的一些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律的分析、总结和提升,换句话说,本书所描述的绝大部分信号传递行为及其效应,读者都能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常识加以印证。一个人,只要他生活在社会之中,就会而且几乎总是要进行信号传递活动。用自然科学的术语作比喻,可以说信号传递就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力”或者“化学键”,是人们社会生活交往中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信号传递-合作模型同样是“帝国主义”的,其理论应用并不局限于狭义的法律与社会规范问题,而是可以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关于法律与社会规范的实体性问题的讨论中,作者充分地展现出了其理论思维的精细、深刻以及——老波斯纳所说的好的分析所必备的——“冷酷无情”。本书在很多问题的分析上都为读者奉献了发人深省的洞见,例如,在分析羞辱性刑罚时,作者指出,废除酷刑并非因为道德进步,相反,道德的某些进步是因为废除了酷刑(第六章);“在极权主义国家中,一个人通过赞同明显错误的宣传来表现其爱国心”——这是作者以符号行为为线索,通过推广对种族歧视信号的分析而捕获的“秘密”(第八章);从不可通约性的断言入手,作者“揭发”了人们的表里不一的“虚伪”,并由此提出了一个精辟的命题:意识形态(刚性)是的世界观(柔性)的夸张、简化版本(第十一章);等等。而当我读到作者提出的将信号传递理论和批判理论相结合的建议时,更不禁要感叹波斯纳教授在这本书中所寄托的理论雄心。
《法律与社会规范》一书可能会为中国法学和法律实践带来多个方面的助益。当然,如上面的介绍所表明的,本书在中国语境中的价值首先是法学方法论上的。罗伯特·埃里克森的《无需法律的秩序》一书把社会规范理论从先前的人文研究(解说)推进到了社会科学研究(论证)层次,[24] 而波斯纳则进一步拓展、精致、深化了由埃里克森所开创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我们可以看到,在本书中,社会科学进路的方法已经相当成熟了,而且如上文所述,从注释体例上透露出来的信息甚至表明,作者为本书的定位很可能并不仅仅是一部法学著作。在“中国法学界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对方法论的关注,乃至导致方法的单调和薄弱,除了大讲解释学(或阐释学)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替代或互补”[25]的情况下,本书的方法论以及论证结构很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些启发、借鉴甚至示范作用。
其次,本书对于法律与社会规范所做的细致而且富于启发的研究彰显出了这一学术领域或多或少被埋没了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以法律解释学为学术主流的中国法学中,这方面的研究注定是薄弱的。法律与社会规范(social norms),乍看起来这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范畴(因此容易被排挤到法学的边缘),但实际上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统一的,或者说是融合在一起的。在我国,法律通常指的是制定法(行为的应然),而制定法是法律的渊源,因此,从严格语义学的角度来说,制定法就不是法律。是的,这是一个悖论,产生这个悖论的原因在于人们定义法律的时候没有在实然与应然两个维度上做出必要的区分。[26] 社会规范,按照波斯纳教授在本书中的定义,是指存在于博弈均衡之中的行为常规(regularities)(行为的实然),即“活法”、“行动中的法”、“实际规则”。我国目前正处在迈向现代化的社会全面转型时期,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无法可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的情况,在这个时候,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社会规范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法律(制定法)可能存在着是否健全、适用等多方面的问题,而作为“活法”的社会规范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通过对社会规范的实证研究所获得的规范意蕴将是——而且必定是——法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做出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再次,尽管法律和法学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地方性的特征,[27] 社会规范更是具有天然的地方性,然而这些特征显然都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本书凭借着以博弈论为核心的科学方法论首先就突破了法学的地方性限制。勿庸置疑,方法论的普适性(或者说科学性)对于打破学科内和学科间的壁垒,深化研究以及推进学术同行的交流与评估具有关键性的作用。[28] 另一方面,本书还以其精湛、广博的分析展示了制度背后的深层的人性动因和逻辑动因,使我们有可能高屋建瓴地把不同国度的迥然相异的社会规范勾连起来,从而超越“法律”的地方性。所有这些对中国法学的“改革开放”、“同国际接轨”都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
而且,必将有一天,我们在流逝的时光中回望来路的时候会发现,所谓“改革开放”、“同国际接轨”之类的话语其实都是累赘的表述,因为学术乃至生活本身就是如此。
记得还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曾读过叶秀山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读那总是有读头的书》[29],谈的是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感受,当然,那时的我是读不懂这样的文章的,可是这篇文章的题目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年来一直没有忘记。现在,偶尔和同学聊起读书的体会,我还会故作深刻甚至好为人师地重复叶先生的这句话:应该读那总是有读头的书。法学和哲学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读书的经验上却是相通的。作为译者,我觉得波斯纳教授的这本《法律与社会规范》可算是法学领域中的一本“有读头的书”,到底是不是呢,当然,这就要请读者诸君自己来阅读、评判了。
在书成付梓之际,译者要向下列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首先感谢波斯纳教授仔细地为我解答了翻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感谢苏力老师介绍这本书给我翻译,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学习和锻炼机会;感谢他在日常学习中给予我的点点滴滴的教诲和启发。
感谢高鸿钧老师扶我在学术翻译之路上起步。
感谢冯象老师教我对学术翻译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
最后,我还要感谢妻子杨剑虹在翻译此书过程中对我的支持与帮助;她通读了译稿,并且提出了细致的修改意见。
希望他们几位能“不嫌微末地”接受译者的谢意。当然,译文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与错误盖由译者负责。
沈明,2004年7月3日。
——————————————————————————–
[1] 请看美国法律经济学领域中的三位知名学者对本书的评语:耶鲁大学法学院伊恩·埃里斯(Ian Ayres) 教授说:“埃里克·波斯纳的写作富于雄心而又引人深思,他的论题是法律学术中的最为重要、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他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结构,精致地阐释了论题,呼应了替代性论点,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广泛的法律领域,并收获了各种规范性法律意蕴。《法律与社会规范》一书应该成为关于规范理论的权威参考文献之一。”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罗伯特·考特(Robert D. Cooter)教授说:“埃里克·波斯纳讨论了法律与社会规范研究中的若干最重要的问题……《法律与社会规范》立足于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的理论,意在洞察广泛的道德行为;对于许多规范性的事实和制度来说,本书都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假说和洞见。”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理查德·麦克亚当斯(Richard H. McAdams)教授说:“通过对于信号传递模型的创新应用,《法律与社会规范》一书对经济学和法学理论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埃里克·波斯纳通过对于人类行为的一种简约的解释,扩展了经济学的领地,使其包括了一些直到晚近时候还仅仅属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所考虑的问题。正当经济学迷惘于如何能最好地解释群体连带、[行为的]一致性(conformity)和社会规范的时候,本书有望对经济学理论家的路径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见本书英文版封底。 [2] Robert C. Ellickson, 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中译本:《无需法律的秩序》,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3] 参见 Robert C. Ellickson, “Law and Economics Discovers Social Norms,” 27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537 (1998). [4] 参见 Richard A. Posner, “Social Norms, Social Meaning,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A Comment,” 27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553 (1998). [5] 尽管论文已经有了不少(包括法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具体可参见本书“参考文献”),例如专题文集就有:Symposium, “Law, Economics, and Norms,” 144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643 (1996); Symposium, “Law and Society & Law and Economics,” Wisconsin Law Review 375 (1997); Symposium, “The Nature and Sources, Formal and Informal, of Law,” 82 Cornell Law Review 947 (1997); Symposium, “Social Norms, Social Meaning, and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27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537 (1998); Symposium,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Norms,” 86 Virginia Law Review 1577 (2000). [6] Lawrence Lessig, “The New Chicago School,” 27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537 (1998). [7] Richard A. Posner, The Problematics of Moral and Legal The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中译本:《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8] 为了方便阅读,译者把中译本的注释体例改为脚注了。关于这一更改的更详尽的理由,可参见苏力:《走马挑刺》,载《批评与自恋:读书与写作》,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30页。 [9]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The Path of the Law,” 10 Harvard Law Review 457 (1897). [10] 劳伦斯·莱西格说:“[法律经济学]已经改变了法律的所有领域。现在,我们都是法律经济学家了。” Lawrence Lessig, “The Prolific Iconoclast,” The American Lawyer, December, 1999. [11] Richard A. Posner, “The Decline of Law as an Autonomous Discipline: 1962-1987,” 100 Harvard Law Review 761 (1987). 此文经修改后收入了Richard A. Posner, 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 14. 中译本:《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 借用丁尼生的名句。参见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国王歌谣集·亚瑟之死》,第408-410行,转引自冯象:《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70-171页。 [13] Eric A. Posner, Law and Social Nor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 以下引用此书不再加脚注,而是在正文中直接标出页码。 [14] 参见 Richard H. McAdams, “Signaling Discount Rates: Law, Norms, and Economic Methodology,” 110 Yale Law Journal 625 (2001). [15] 这一点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奥卡姆(Occam)剃刀原则;它在经济学中的体现可参见:Milton Friedma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16] Edward O. Wilson,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7] 参见 Gary S. Becker,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ch. 13. [18] 参见 C. P. 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a Second Loo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19] Edward O. Wilson, On Human N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reface,” p. xii. [20] Edward O. Wilson, 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8. [21] 其他一些著名学者也有类似的主张。例如,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对于宇宙统一理论的探索和展望,参见Stephen W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New York: Bantam Press, 1998, ch. 11. 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则不约而同地讨论了(广义)科学与美学的关联,参见杨振宁:《美与物理学》,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Richard A. Posner, Law and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01-302. 中译本:《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22] Friedrich A.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 176. [23] 参见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24] 参见苏力:《研究真实世界中的法律》,载《波斯纳及其他:译书之后》,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229页。 [25] 同上,第239页。 [26] 即罗斯科·庞德所谓“书本中的法”(law in book)和“行动中的法”(law in action)的区分或者卡尔·卢埃林所谓“书本规则”(paper rule)和“实际规则”(real rule)的区分。 [27] 参见 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ch. 8. 苏力:《面对中国的法学》,载《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 [28] 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就是经济学:经济学在今天就基本没有地方性了,“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如今几乎已经销声匿迹。 [29] 载《读书》,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