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弗里德曼:《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中文版序言
沈明 译
对于任何一位作者来说,得知自己的书被译成中文都会感到高兴的。世界上说汉语的人数超过了任何其他语言的使用者。在中国及其临国,汉语使用者的人数超过了十亿。此外,汉语还是一种绵延了数千年的古老文化和古老传统的载体。汉语读者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读者群。即使能把自己的文字传达给中文读者中的一小部分人,我就很高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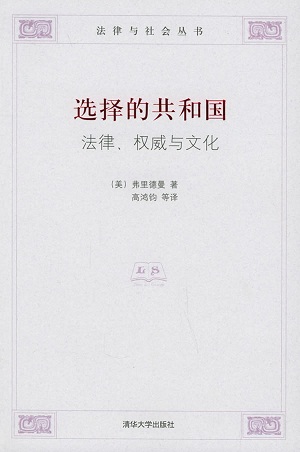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美国法律文化,它同时也牵连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法律文化。本书的主题是论述选择在某些国家的社会制度中以及法律制度中所占据的首要地位,这些国家是指欧洲、北美和其他地方的富裕发达国家。一些国家的文化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形象的说法是个人就是国王。他/她所需要或欲求的东西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的愿望总能得到满足。没有人能得到他/她所追求的一切;有很多人几乎从来没有得到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对许多贫困的人来说,选择是一种幻想;对监狱里的人来说是如此;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对所有身陷逆境的人来说都是如此。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就中产阶级而言,选择确实成为了或大体上成为了一种现实,这包括对商品的选择,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甚至对于宗教的选择。在上述这些社会中,为个人成就、个人满足所做的努力是人生的关键和基础。正是选择的这种首要地位使我将本书命名为“选择的共和国”。我努力尝试阐明“选择的共和国”在法律和生活的不同领域中所蕴含的种种意蕴。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美国法律文化,它同时也牵连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法律文化。本书的主题是论述选择在某些国家的社会制度中以及法律制度中所占据的首要地位,这些国家是指欧洲、北美和其他地方的富裕发达国家。一些国家的文化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形象的说法是个人就是国王。他/她所需要或欲求的东西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的愿望总能得到满足。没有人能得到他/她所追求的一切;有很多人几乎从来没有得到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对许多贫困的人来说,选择是一种幻想;对监狱里的人来说是如此;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对所有身陷逆境的人来说都是如此。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就中产阶级而言,选择确实成为了或大体上成为了一种现实,这包括对商品的选择,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甚至对于宗教的选择。在上述这些社会中,为个人成就、个人满足所做的努力是人生的关键和基础。正是选择的这种首要地位使我将本书命名为“选择的共和国”。我努力尝试阐明“选择的共和国”在法律和生活的不同领域中所蕴含的种种意蕴。
如我所说,本书涉及的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化与社会。它包含着我对这些国家的当代社会的思考和研究。然而我所做出的这些一般性的论断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吗?也适用于东方国家吗?它们对于中国而言有什么意义或者重要性吗?当然,即使不能把这些论断依字面含义照搬给中国,或者只有在做出大量解释性说明之后才能应用于中国,它们或许仍旧是有价值的。它们可以帮助中国人理解美国和美国之外的世界。不过,带着些许谨慎,我还是想做出断言:即使对中国、对西方世界之外的国家而言,我在本书中的论述也是相关的。
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勾勒一下不同类型的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首先,存在着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它们不属于西方世界,但是却富裕、高度发达,而且其结构和政府也(或多或少)和欧洲国家相类似。也有一些非常传统的国家,它们抵制现代化,首先映入脑海的例子是沙特阿拉伯。还有一些国家,例如索马里,似乎是在开倒车。剩下的就是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了:这些国家正在快速发展,但是它们的起点却远远低于日本或西方国家。
有些人认为,日本和中国(提出这两个最主要的例子)在文化和传统上同(比如说)法国或者美国是迥然相异的;不论它们在经济上如何发展,不论它们采用了多少先进的技术,都依然会保持其原有的方式。它们的文化和传统深深地植根于历史,而且已经融入了这些国家人民的灵魂。因此,不论中国和日本在经济上如何发展,不论它们采用了多么先进的技术,它们依然会是独特的,它们依然会忠实于自己特定的文化。
这种推论是否成立,我不无疑问。随着国家的发展,它们会变得越来越相似。这仅仅是因为现代技术会消解差异。不论在哪里,汽车就是汽车。然而这里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人们拥有什么,或者他们拥有什么现代工具和设施。现代社会的装备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人们的表面行为。汽车并不仅仅就是一件比马跑得更快的东西。技术改变着文化,改变着思维方式,正如它们以同样的程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一样。显而易见,人们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而且将永远存在。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两个欧洲国家完全相同。但是与两个世纪之前相比,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却在增加,而增加的程度令人感到吃惊。
这一过程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我认为,现代化创造着“选择的共和国”。除此没有别的选择。例如,请想一想广告的作用,就会明了。广告商不论是给什么产品做广告,其潜台词都不外乎是:该产品会使您更健康、更富有、更性感或者更快乐。它会使您的牙齿更洁白,或者使您的咖啡更芳香,它会在工作或者家庭中助您一臂之力。广告针对的对象是个人而非社区、家庭或者群体。现代经济赖以存在的支柱就是消费。而消费则意味着对个人需要、愿望和欲求的满足。现代经济以及现代社会,在这个意义上都是选择的共和国。
因此,我的预见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也会走上这条道路。它将会日益成为一个选择的共和国。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失去其固有的精神和传统,不过,其精神和传统会发生变化,也许不得不变化。这是否令人遗憾呢?无疑会有人做出肯定的回答,当然也必定会有人做出否定回答。
我坚信,本书会为汉语读者带来一些启示。汉语读者将不得不为他或她自己再做一次解译。他/她将不得不把本书中的信息,其中的观点与论辩解译为符合汉语读者思维习惯的社会、法律与文化术语。读者将不得不对下述问题做出评判:这第二次解译是否成功?或者,它是否遗漏太多、省略太多以至于变得支离破碎?我对这第二次解译和本书的翻译寄予同样殷切的希望。
劳伦斯·M. 弗里德曼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
200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