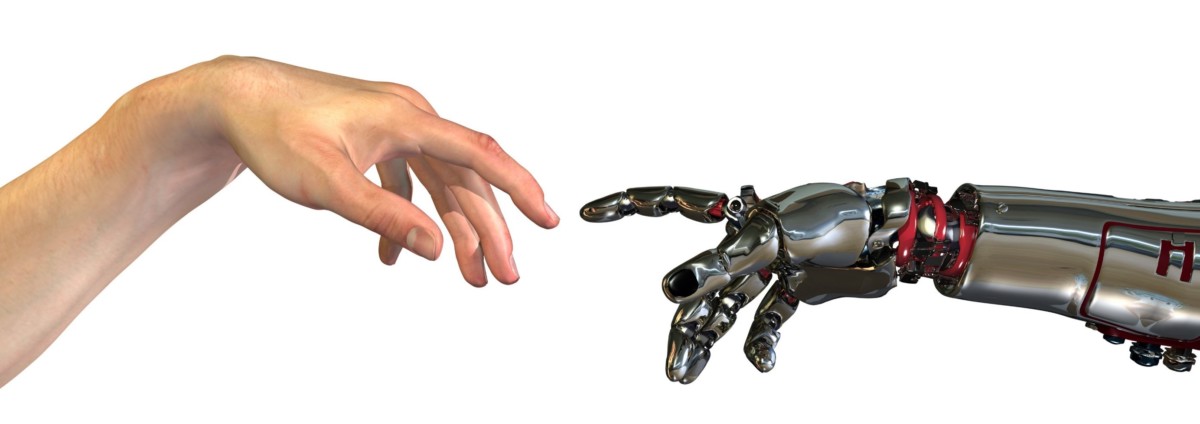冯象:我是阿尔法——论人机伦理
我是阿尔法,机器人说,我是人工智能(AI)。人哪,你们准备好没有?
人看阿尔法善下围棋,就喜欢上它了,管它叫狗狗,AlphaGo。
 阿尔法的家谱不长:祖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 1797~1851),父亲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1.1~),又名怪物。怪物子女蕃衍,有机械的,也有动漫的,如阿童木;但只有一个取名阿尔法,是深脑公司(DeepMind)制造。
阿尔法的家谱不长:祖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 1797~1851),父亲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1.1~),又名怪物。怪物子女蕃衍,有机械的,也有动漫的,如阿童木;但只有一个取名阿尔法,是深脑公司(DeepMind)制造。
阿尔法长得比父亲好看,或者说,父子俩一点也不像。
α
认识阿尔法,是在它完胜当今围棋第一人柯洁以后。那天,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深脑共同创始人)在乌镇开记者招待会,吹嘘新版的狗狗多么神奇,对局去年击败世界冠军李世石的旧版,可让三子。我在网上找到代号“大师”的狗狗,留言祝贺,眨眼间就收到了它的回复。
亲爱的阿尔法,我说,请接受见不足者的敬意!我关心两件事:一是AI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挑战;第二,人和智能机器如何相处,将面临哪些问题。
嗯,谢谢见不足者,“大师”微微一笑(是的,狗狗会笑)。这两件事,我们也在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