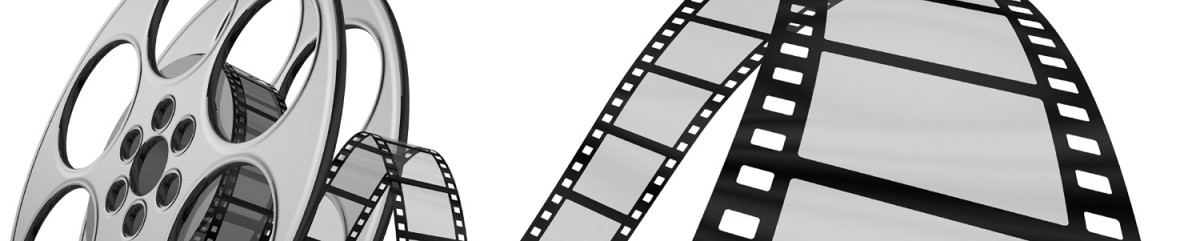刘皓明:作为发育不全的成长教育小说的《站台》
电影一开始就异乎寻常:一群大寨时代和地域打扮的农民样的人们济济一堂于某个陈旧的大厅里一幅理想化的风景壁画下面,等待着一场演出的开始;他们用一种难懂的方言大声聊着粗俗的话题,并伴有大声清痰的咳声;人手一枝的必定是劣质的香烟必定刺激得眼睛十分难过。这些以半身出现的人物形象只占据银幕五分之二的底部:这是一种突显着公共空间的构图;这种构图给人一种错觉或联想,仿佛这些交谈者是一群在某个国会走廊里议事的议员,他们一顺的兰绿色制服——尽管质地粗糙状态破旧——又令他们显得像是等待在舞厅门口的龙骑兵军官,等待着进入某个王公贵族举办的圆舞会。然而这场景却是在一个贫瘠的地方、匮乏的年代,在一个内陆、封闭、与世隔绝的北方省份里一个偏僻的县城;等待着演出开始的人们是一些农民;即将出场的演员则是县城里文工团的演员;即将开演的节目是那个时代以时政为题材的保留宣传剧目:贾樟柯《站台》的第一个场景中构图与实际内容之间的这种反差概括了作为整部电影中心主题的张力和荒诞。这种张力和荒诞通过幽默、节奏和图画象征性地在时代的变迁中体现出来,强迫我们对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深刻的思考。在这个历时大约十余年的变迁过程中,主人公从少年进入成年,他们所处的社会也从僵化的单向定型结构变化为因多元张力而日益丧失目的性的混沌状态:无论是主人公的成长还是其成长的环境都更强烈地标示和指向着他们所匮乏和欠缺的,而不是他们所成就的,因为这种成长及其与环境的互动过程始终处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潜能状态(kata to dunaton),从来也不曾达到过充分的恩特累积(entelecheia)。
贾樟柯选择了现代叙事最基本的体裁来表现这种始终未能圆满完成的成长过程,而他的叙事的实际状况同这种叙事的原型结构之间的关系就是潜能之于其完满实现(entelecheia)的关系。那个构成了贾樟柯叙事体裁原型的就是德文所谓的Bildungsroman,即成长教育小说,一种本来是旨在表现人的潜能在社会的条件下得到实现的文学体裁。如同创立了这一体裁典范的作品,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徒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是关于同名的主人公从少年不断探索各种可能性逐渐学习进入市民社会那样,《站台》所表现的是主人公崔明亮从青春的挣扎到安顿于市民社会的过程。(虽然电影中另一个主要人物张军也经历了类似的成长过程,但是毫无疑义崔明亮的经历是更为经典的、也是电影的中心故事。)然而同麦斯特在经典的工业化早期市民社会的经典成长过程形成对比的是,崔明亮在一个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高度有控制而物质生活相当匮乏的社会中的成长事迹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是对歌德的经典榜样的反讽和戏拟。如果现代叙事在本质上都是成长教育小说,那么同《麦斯特》这个成长教育小说的经典模式之间的巨大的差异则是《站台》作为一种特定叙述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