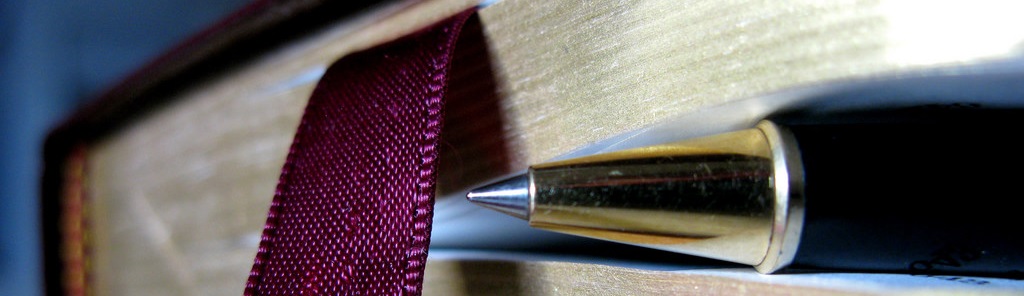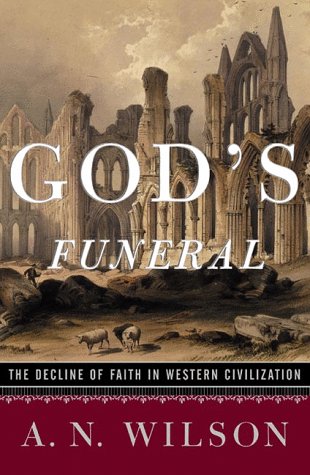冯象:误译耶稣
《读书》去年六月号有篇文章挺好,《新约圣经:绝对神授还是历史产物》,介绍艾尔曼先生的《误引耶稣》(Misquoting Jesus, 2007)。艾氏在北卡大学教授《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有年,著述极勤,文风活泼,还常上电视,在美国圣经学界可算个公众人物。他的书若能准确地译为中文,对于学界和普通读者,都是一件功德。
不过文章有两处小疵,经文引述则涉及《圣经》汉译的一个老问题,似可略加检讨。当然瑕不掩瑜,再说一遍,这文章大体是不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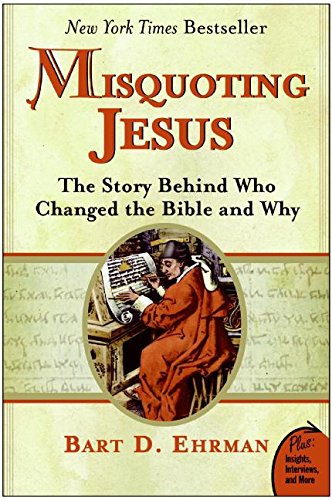 先说小疵。一本讨论经文传抄跟校勘的书,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而且连挂九周“售出三十八万册”,作者觉得“出人意料”,录了一句《华盛顿邮报》,称《误引耶稣》为“最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的畅销书”。其实“最不可能”云云,跟中译本把书名改作《制造耶稣》一样,是营销手法,上海人叫“摆噱头”。在美国,走出学界向老百姓和信众讲《新约》“误引耶稣”,那个效应,是毫不逊色于我们这边的写手言之凿凿,指毛主席诗词哪几首出自胡乔木之手的——要想不吸引眼球也难。此外,九十年代以来宗教全球复兴,圣经学、宗教研究在西方成了热门学科同传媒话题,也是《误引》得以畅销的市场条件。
先说小疵。一本讨论经文传抄跟校勘的书,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而且连挂九周“售出三十八万册”,作者觉得“出人意料”,录了一句《华盛顿邮报》,称《误引耶稣》为“最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的畅销书”。其实“最不可能”云云,跟中译本把书名改作《制造耶稣》一样,是营销手法,上海人叫“摆噱头”。在美国,走出学界向老百姓和信众讲《新约》“误引耶稣”,那个效应,是毫不逊色于我们这边的写手言之凿凿,指毛主席诗词哪几首出自胡乔木之手的——要想不吸引眼球也难。此外,九十年代以来宗教全球复兴,圣经学、宗教研究在西方成了热门学科同传媒话题,也是《误引》得以畅销的市场条件。
文章末尾,谈到艾氏的思想经历,怎样由虔诚的福音派信徒成长为“不可知论者”(agnostic),给人的印象,仿佛他是因为钻研了版本校勘,发现经书的历史“本源”才“离经叛道”的。事实上,艾氏在别处多次声明,放弃基督教,跟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接受现代圣经学知识与历史批判方法没关系。真正让他困惑、心生疑窦的,是所谓“约伯疑难”或“好人为什么受苦”的拷问。经过长久的思考和痛苦的内心斗争,他认为这道难题在一神教教义的框架内,不可能得到合理解决并升华为生活的慰藉;这才告别教会,转向了不可知论(参阅艾尔曼《上帝的难题》及《耶稣,被遮断》)。至于课堂作业要学生“横向读经”,就是找出福音书里的平行故事,比较语汇情节的异同,这办法古人早有记载,还列出一组组的“对观句段”(synoptic pericopes),发展了精微的神学解释。故此,承认部分经文为托名作品,或者由不同渊源(时代、地域、个人或社团)的片断或文本传统编辑而成,跟主张经书神授,奉为圣言或上帝之言,这两种立场虽然对立,却未必动摇得了信仰,是可以妥协而共存的。毕竟,信仰不靠(有时也不容)论理:人性孱弱,奥义无穷;宗派纷争,永无宁日。教义即人意亦即政治。传世抄本犹如历代译文,充满了消弭不了的歧义跟矛盾,原本是不足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