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诗人与城市
薛华 译
……让我们承认,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什么,
或者让我们受惠于这种疑问……
——威廉姆·燕卜荪关于诚实地进行生活这一主题的文字,很少有些什么、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无论是《新约圣经》还是《贫穷的理查德》(注:Poor Richard,即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作品《贫穷的理查德的年历》(Poor Richard’s Almanac)),都没有道出我们的生活状态。如果只看文学的话,人们决不会认为这个问题曾经扰动过一个独处的人的沉思。
——H·D·梭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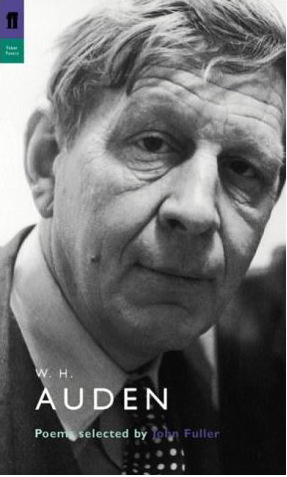 令人惊讶的是,当年轻的男男女女被问道想做什么工作的时候,许多人既不会作出理智的回答(比如说,“我想做律师,开旅馆或做农民”),也不会作出罗曼蒂克的回答(比如说,“我想做探险家,摩托车赛手,传教士或美国总统”)。相当一部分人会说,“我想成为作家”,这有些出人意外。他们所说的写作指的是“创造性的”写作。即便当他们说“我想做记者”的时候,那也是因为他们对记者的职业产生了错觉,误以为他们将能够进行创作。即便他们真正的想法是要赚钱,他们也会选择报酬较好的带有一点文学特性的职业,比如说广告。
令人惊讶的是,当年轻的男男女女被问道想做什么工作的时候,许多人既不会作出理智的回答(比如说,“我想做律师,开旅馆或做农民”),也不会作出罗曼蒂克的回答(比如说,“我想做探险家,摩托车赛手,传教士或美国总统”)。相当一部分人会说,“我想成为作家”,这有些出人意外。他们所说的写作指的是“创造性的”写作。即便当他们说“我想做记者”的时候,那也是因为他们对记者的职业产生了错觉,误以为他们将能够进行创作。即便他们真正的想法是要赚钱,他们也会选择报酬较好的带有一点文学特性的职业,比如说广告。
在这些想要做作家的人当中,许多人并没有显著的文学才能。这一点本身并不奇怪,因为任何方面的显著才能都是不常见的。真正让人吃惊的是,在没有任何显著才能的人当中,居然会有这么高比例的人把写作当作答案。人们可能会以为,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会觉得他们具有医学或工程学等方面的才能,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在我们的时代,如果一个年轻人天资贫乏,他就可能想去写作。(当然,也有一些毫无表演才能的人梦想着要成为影星,但是,他们至少还天生具有相当吸引人的脸蛋和身材。)
希腊人接受奴隶制并且为之辩护,他们比我们要更为无情,但是也比我们更为清醒——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劳动便是奴役,而没有人会因为是劳役者而觉得自豪。有人可能会因为作工人而自豪。换句话说,工人便是制造耐用物品的人。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制造过程已经被按照速度、经济和生产量来量化了,因此,单个工厂雇员所扮演的角色变得过于渺小,因而作为工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实际上,所有的工人都已经变成了劳动者。有些人没有显著的才能,因而有理由担忧他们将一辈子面对无意义的劳动,对于这些人来说,不能按照上面的方式来加以量化的艺术——艺术家本人仍然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应该会使他们着迷,这是非常自然的。这样的着迷并不是艺术的性质使然,而是艺术家工作的方式使然:他就是他自己的主人。在我们的时代里,其他任何人几乎都做不到这一点。做自己的主人的想法吸引着大多数的人,这很容易让人们异想天开,以为艺术创造的才能无所不在,人们只要去努力一番,纵然不依赖特殊的才能,单凭作为人这一点,也可以进行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