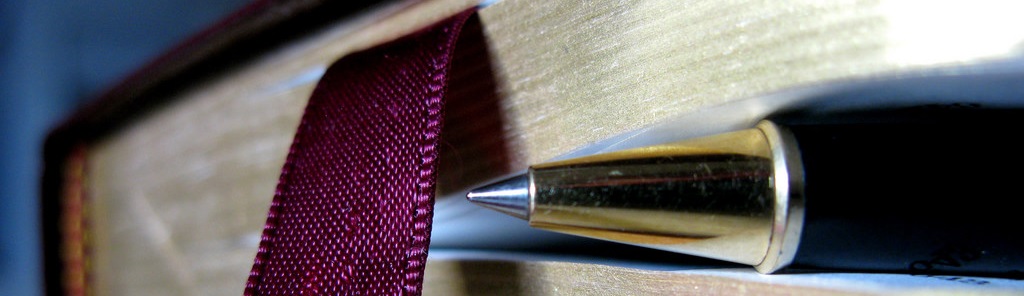
冯象:传译一份生命的粮——答冼丽婷
冯先生好。能否谈谈繙譯聖經,想達到甚麼目的?
译经的目的,我在《摩西五经》的前言及附录(彭伦先生的采访)里说了,一是为中文读者(包括信友和圣经学界)提供一个可靠的中文学术译本,二是如果可能,力求让《圣经》立于中国文学之林,即进入汉语主流文化。注意,我说的是“圣经学”,而非任何基督教宗派的神学或教义。后者在西方的历史和理论我做过些研究,算是老行当了吧。但传教“牧灵”跟做学问,是完全不同的事业,没有哪个译家可以兼而得之。因此,现实地看,我的译本也许会影响到“牧灵”译本的修订和术语措辞,但不可能取代其中任何一种。
你在繙譯新約上共用了多少時間?在舊約部份又用了多少時間?甚麼時候可以完成舊約全部繙譯,出版新約舊全書?
《新约》用了两年,因为先已译了两卷希伯来语《圣经》(基督教称“旧约”,但西方学界为了尊重犹太人的宗教和民族感情,通常用这一“中性”的说法),参考资料跟术语译名都有了准备,所以进展颇顺利。之后还有两卷,即《历史书》和《先知书》。何时竣事,不太好说,因为俗务繁多。
原先的聖經有甚麼謬誤呢?請舉例子。
市面上流通的中文译本不少,但我想您指的是和合本(1919)。和合本是上世纪初在华新教诸派达成妥协,英美传教士在上海合作搞的译本,底本是英语钦定本(KJV)的修订本。但由于传教士西学功底浅,中文更不济,未免错误百出。别的不说,《圣经》开篇第一句话,很简单明了的经文,就栽了跟头,详见拙文《上帝的灵,在大水之上盘旋》(网上可阅)。天主教的思高本(1968)要准确得多,但风格不如和合本直白,也不如和合本在普通读者中间传播得广。听说,和合本的修订快完成了,希望至少一些明显的硬伤、妨碍理解经文教义的舛漏能得到改正。和合本我批评过几回,然而,就传教“牧灵”的长远目标而言,着眼于新教进一步中国化的努力,我觉得目前还没有更成熟的译本。这一点,我在即将出版的《新约》的前言里谈了。
請介紹如何著手繙譯聖經。從結構到文字及搜證,如何處理?如何保證繙譯時能保存聖經的解讀功能?
这两方面的诸多问题,我专门写了一本书讨论,叫作《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北京三联书店,2007),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此处不赘言。其实,学术译经跟教会译经的方法差不多,困难也一样,并无什么特殊,只是出发点不同,还有就是注释的角度有异。比如我一般不讲教义,当然也不持任何教派立场,夹注只举出西方学界的通说和主流观点。所谓通说,指的是一二百年来,欧美学者在圣经学、宗教学、古典语文和考古等学科领域,涉及经文解读的一些业已广泛接受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光在大学课堂上讲授,也是西方主流神学院的课程内容,如《摩西五经》的片断构造和成书年代的考订、《新约》“对观福音”(头三篇福音文句内容重叠甚多,可平行对观,故名)的文本渊源、耶稣时代巴勒斯坦的宗教思想、异端文献和受膏者(基督)运动,等等。照 Bart Ehrman 教授的说法,如今一个主流神学院的学生,毕业后非得把课上学来的东西忘掉,才当得成牧师呢——有点像我们内地的法学院教育,学生一出校门,参加工作,不论律所法院还是政府部门,就把课本知识和教条原理通通还给老师了。
Ehrman 教授是学界公认的《新约》与早期基督教文献研究的专家,出身普林斯顿神学院,是 Bruce Metzger 的学生。Metzger 先生参与编订了希腊文《新约》的权威版本(NTG),也是流行的英语学术译本新修订标准本(NRSV)的主持者。现代圣经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美一部分较为“自由派”的教会对经文的理解。但是,中文教会恐怕一时还不会接受西方学界的学术成果,这跟中文教会自身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传教的大环境与应对策略有关,是不可苛责于中文教会的。我自己读经数十年,自然也有一点研究乃至一家之言,但不会放进译注里;准备等五卷《圣经》译成了,再另外著书敷演。
你認為你的譯本對一般讀者的吸引力及好處為何?
这些年来,收到许许多多读者、信友和学界同仁的电邮,有谈感想提问题的,也有建言商榷的,还有祈祷祝福的,都是莫大的支持。我想,一人独力,孜孜以求,这样完工的几卷译文,能够蒙读者喜爱,引起各方评议,而非如多数旧译那样默默无闻,可算是成功了一半吧。
嚴復也曾繙譯馬可福音,你有沒有看過?評價如何?
只翻了四章吧,我没细读。严几道于福音之道,恐不是麦都思、郭实腊、施敦力、杨格非之流的对手。此事香港中文大学的李炽昌教授探讨过,我在网上见到。他引了一段清人蒋敦复的话,蛮有意思,您听听:
“若夫天教,明季始入中国。利玛窦、南怀仁诸人,皆通天算舆地之学,材艺绝伦。其所著《七克》等书,切理餍心,颇近儒者,故当时士大夫乐与之游。今之教士,其来者问有如利、南其人者乎?无有也。所论教事,荒谬浅陋,又不晓中国文义,不欲通人为之润色。开堂讲论,刺刺不休,如梦中呓。稍有知识者,闻之无不捧腹而笑”(《啸古堂文集·拟与英国使臣威妥玛书》,引自李炽昌、李天纲《关于严复翻译的马可福音》,载《中华文史论丛》63辑,9/2000)。
蒋敦复(1808-1867)是上海宝山人,工词而才识过人,与王韬、李善兰齐名,曾在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工作多年,协助翻译《大英国志》,还写了凯撒、圣女贞德和华盛顿的小传。他对传教士的学养素质的评价,应该是出于切身体会。当然,以牙还牙,传教士也损他,“让吸食鸦片给毁了”。只是这些以拯救异教徒灵魂为己任的大人们忘了,鸦片是怎样登陆中国的;要不是托鸦片的福,托不平等条约跟治外法权的福,自家连一句“荒谬浅陋”的话,都没处去叨唠呢。
你認為基督徒中有沒有出色的繙譯聖經人才?或是為何沒有?
当然有,吴经熊先生是第一人。他用文言译《圣咏》和《新约》,琅琅上口,起伏跌宕,比那班传教士强多了。此外,还有一位高士——抱歉不是信徒——生前曾有译《新约》的宏愿,若是天假以年,必会成就一桩大功。那便是徐梵澄老人。徐先生是会通了中、印、西三大文明的罕见其匹的大学者,又是得了鲁迅先生亲炙的哲人和文章家,他未能如愿传译《新约》,实在是中文世界的一大遗憾。
繙譯聖經後,對基督信仰有沒有新感悟?你對自己信與不信基督教有沒有新的看法或預見?有沒有聖經學者在與你砌磋聖經繙譯時,向你傳道,希望你成為信徒?你認為你可能會成為信徒嗎?
呵呵,女流不忌问芳龄,男辈弗忧查信仰,这问题有点子“中国特色”。这么说吧,美国宪法有一条原则,名曰政教分离。贯彻到教育领域,教师在校园里借用学校资产传教,就有可能引发官司。美国的圣经学和宗教学界,更是什么信仰都有,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随便向人传教可是犯忌的事,谁敢做啊。诚然,译经须对古人的信仰与先知的启示有所感悟;但同时又要特别注意,那信仰的启示,同我们这个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教派政治和教义实践不是一回事。后者,如前文谈及的,实际是基督教进入本土化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个个新老宗派社团各不相像的“属灵的”生活。
你認為你的聖經繙譯達到了文化保育功能嗎?新譯本是要把聖經放到公共領域上嗎?
我想您说的“公共领域”不是我们法律上的概念,而是指常人想象中那个教会以外的“公共”空间吧。但教会绝不是一个封闭的组织,她从来就处于公共生活之内,深深地嵌入我们的历史、文化、公共道德和政治秩序。在香港,正如在内地,有哪一个教会不在散发《圣经》,不积极宣道、参与社会建构和社会斗争呢?不如此,她就不能够抚慰苦灵,传布福音,教人立信称义。在此意义上,译经,即使是“非教徒”的译经,也不仅仅是无伤大雅的“文化保育”。我想,圣法的教导、先知的呼唤、耶稣的受难复活的启示,随着宗教复兴和中国社会行将展开的伦理重建,是会为越来越多的国人聆听而认识的。一个日益多元化的容纳不同信仰的社会,需要这样一份“生命的粮”(《约翰福音》6:35)。
二〇一〇年六月四日于清华园
原载香港《信报》201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