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象:众神宁静——《圣诗撷英》代序
此书是圣诗的选本,取希伯来《圣经》四十一篇,《新约》十二篇,成五卷五十三章。译文既有新译,也有已发表而这次做了修订或调整的,各具导读和尾注。尾注的好处,是不必像拙译《摩西五经》《智慧书》《新约》《以赛亚书》的夹注受字数限制,可以扩充内容,并配合导读,阐发近年授课答疑及写作中的一些所思所得,与读者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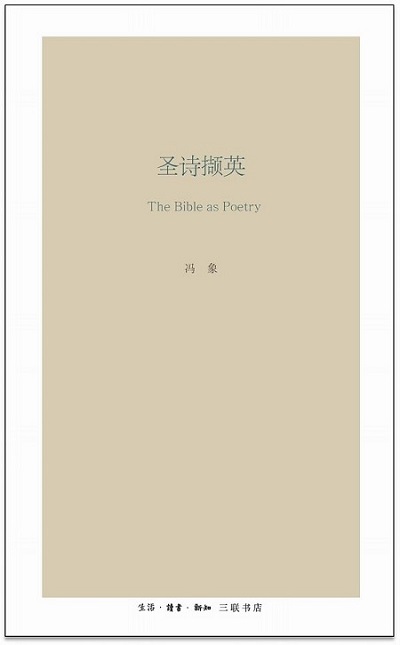 选本的想法,由来已久了。最先是我的老师波士夫人的建议。所以很早就定了书的献辞,用她喜欢的诗句,准备给老人家一个惊喜。不意末章《新天新地》的导读写完,感恩节刚过,夫人竟去了永恩之域。
选本的想法,由来已久了。最先是我的老师波士夫人的建议。所以很早就定了书的献辞,用她喜欢的诗句,准备给老人家一个惊喜。不意末章《新天新地》的导读写完,感恩节刚过,夫人竟去了永恩之域。
于是,完稿的欢愉就化作了思念,和回忆……
初见夫人,还是在昆明,三十八年前的事了。夫人是同三子派迪一起来云南大学执教的。其时知青战友M在云大外语系,是七七级的大姐;我在师院(今云南师大),一条马路之隔,按知青的习惯去她那里蹭饭,她就把我引荐给了夫人。从此,读书译诗每有疑问,便上夫人的小平房宿舍求教。一般是吃过晚饭,与几个同学在校园里溜达一圈,待自习开始,一人走去云大。
夫人善画,常外出写生。一日雨后,携书下翠湖访长者,见巷子口围着一群人,近前看,却是路人在观赏夫人作画。她朝我打个招呼。也是在乡下随便惯了,忽想到夫人讲过诗人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喜用雨、影的意象,便引一句作答: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然后就旁若无人,聊了起来,“人群里这些面庞”如何“幻现”,“花瓣儿”黏上“湿漉漉的黑枝”,入画可否。路人见夫人停了笔,又听不懂,只好散了。我说抱歉打扰了。夫人笑道,你帮我解围呢。
诗画之外,夫人聊天的另一话题,是批评校内外滋长的官僚作风。坦白讲,那年头的作风比照如今的大树,只是复苏了的旧习的一根嫩芽。可是她有点贵族气,厌恶身边的阿谀逢迎和勾心斗角。少时旅居伦敦,父母为她请了法国家庭教师,大约生活是十分优裕的。我劝她学学师院的帕蒂老师,斗争有理有节(参《信与忘·缀言》)。夫人叹道:她不一样,六八年闹学潮,炼过的呀。其实还有一层家庭背景,夫人不知,帕蒂老师已故的继父是印尼华人,当年共产党赫赫有名的一位领袖。
 夫人是日内瓦大学毕业,育有四子一女。丈夫英年早逝,是哈佛博士、优秀的外交官;一家人跟着,法国、波兰、伊朗、阿富汗、南非、毛里求斯、新西兰,走遍了世界。孩子在哪儿出生,就依当地习俗起名。夫人文笔好,一直同全国地理社(National Geographic)合作,撰写游记。来云南教书的一个缘由,夫人说,是看地图,国家外专局列出供选择的城市当中,昆明较挨近西藏,她的下一本游记的题目。三年外教合同期满,夫人便回到日内瓦湖畔(法国境内)的石头小屋专心写作。派迪则去了香港,做出版;之后入剑桥大学攻读藏学,自称是受了母亲游记的“诱惑”。
夫人是日内瓦大学毕业,育有四子一女。丈夫英年早逝,是哈佛博士、优秀的外交官;一家人跟着,法国、波兰、伊朗、阿富汗、南非、毛里求斯、新西兰,走遍了世界。孩子在哪儿出生,就依当地习俗起名。夫人文笔好,一直同全国地理社(National Geographic)合作,撰写游记。来云南教书的一个缘由,夫人说,是看地图,国家外专局列出供选择的城市当中,昆明较挨近西藏,她的下一本游记的题目。三年外教合同期满,夫人便回到日内瓦湖畔(法国境内)的石头小屋专心写作。派迪则去了香港,做出版;之后入剑桥大学攻读藏学,自称是受了母亲游记的“诱惑”。
一九八二年春,我上了北大,专业定在中世纪文学,论文写乔叟。国内图书馆文献寥寥可数,遂写信向夫人求助。她立刻寄来一箱乔学新著、古法语骑士传奇并普罗旺斯/奥克语(Occitan)游吟歌手的集子。这批书读完,同时每周两晚,跟李赋宁先生学古英语和中古英语,写读书报告,与先生讨论,才算是打好了基础(详见《木腿正义·“蜜与蜡”的回忆》)。而后留学哈佛,专业上就不感觉难。
夫人的小儿子鲁斯坦经商,做玩具生意,儿媳是建筑师。他俩有个朋友加拿大人汤姆,在哈佛学建筑。我一到剑桥,汤姆便受命前来探望,领我参观校园,讲解各派建筑:这一堆水泥叫艺术中心,是 Le Corbusier 忽悠有钱人的代表作;那两排法学院宿舍丑陋,不愧为 Gropius 的大师手笔,等等。还一同去波士顿看红袜队棒球赛,陪伴从多伦多来访的他的妈咪。
不久,夫人来信指示,某日抵剑桥,宿教女玛莎家,某街某号,几点晚宴。那天汤姆刚巧无事,说想见识夫人的风采,我征得主人家同意,就带他一同赴宴。也是缘分,他和玛莎竟一见钟情,趟进了爱河。夫人得知,戏称我有“特异功能”——或许真有也说不定。因为自“扎根云南边疆”始,经我无意间“撮合”的灵魂,少说也有十来对,且于今不断,每每令识者惊异。
玛莎就读于哈佛/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鲁斯坦说她是神童,极聪慧而活泼。她也主修文学,又是学生戏剧社的积极分子,同我很谈得来。当日库格尔(James Kugel)教授开讲《圣经》,课堂爆满,便是她告知并去占的座儿。库先生是正统派犹太教徒,精研圣者拉比的解经之道,兼治西方诗学。阐说圣诗,更是高论迭出,发前人所未发。尤其是他关于希伯来先知不拘“格律”或短句的平行对应,诗入散文、散文亦诗的分析,使我对圣书修辞的包容灵动与歧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参《智慧书·译序》)。
八五年春,内子来美团聚,继而进马里兰大学。恰好夫人的长子米歇尔是马大校友、建筑师,居处离学校不远。此后数年每逢圣诞,夫人返美,祖孙三代齐聚米歇尔家,我们便成了固定的宾客;直至内子毕业,回波士顿工作。米歇尔家过节,有一保留剧目:朗诵夫人的绘本。那是孩子们小时候常听的一则韵文故事,一个威尼斯小淘气鬼的历险记。大伙儿轮着扮演书里的角色,尽情发挥,往往还嘲讽一下时政。那欢乐的气氛,总让我联想托尔金(J.R.R. Tolkien, 1892~1973)给孩子讲《指环王》,或者小爱丽丝听卡罗尔(Lewis Carroll, 1832~1898)聊“漫游奇境”遇见的种种。
那“奇境”般的节日留下的美好印象,少不了一个关键人物:夫人的次子马木。他是纽约的杂技演员,绝顶好玩的性格。有一回,悄悄把我唤上阁楼,演示的却不是他拿手的魔术,而是吸大麻的幸福。
八七年夏,由导师班生(Larry D. Benson, 1929~2015)先生推荐,我申请了一笔专供“瓦伦屋中读书绅士”(瓦伦屋为哈佛英文系旧址)“瞻仰中世纪大教堂”的基金,偕内子游欧。那时各国的签证数法国最严,限制入境次数不说,还指定口岸,不得变更。夫人却说没事。抵达日内瓦那天,她带了一位朋友开车来接,叫我们躺在后座,拿几只商场的大纸袋遮盖了,由乡间小道人头熟悉的关卡,“走私”进入法国;后又照此送出。其间在湖畔小村伯爵古堡的见闻,记在《玻璃岛·圣杯》里了,此处不赘。
那次访问,另有一大收获:有幸结识了夫人的邻居、威尔士老人琼斯先生。老人出身于北威尔士望族,是热忱的民族主义者。一听夫人介绍,我在研究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他就沉下脸,历数盎格鲁·萨克逊人的野蛮卑鄙,对凯尔特人欠下的累累血债,恨不得“宰光了他们放锅里煮吃”。直到我说,中国古代的民族英雄也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的誓言,他才翘起雪白的虬髭,笑了。原来他二战入伍,开运输机,到过云南。战后移居美国,在费城一所私立名校教授历史,家住普林斯顿附近。我和内子去造访过。林子深处,挺大一座仓房改建的庐舍,门牌上写着威尔士语“老仓”二字,内有一间恒温的图书馆——说是太阳能供暖,曾获建筑设计奖——书架上满满当当,全是祖传的威尔士古籍。于是,请老人指点,学习中古威尔士语,读大卫·阿普规林(Dafydd ap Gwilym,约1320~1370)的诗集。读诗的心得,写了一篇文章《奥维德的书》,发表在《九州学刊》(《木腿正义》,页250以下)。
老人逝世时,我在港大任教。夫人来信说,遵其遗嘱,藏书一部分赠与普大,其余运去了南美,捐给设在那儿的威尔士独立运动的学术机构。
我转读法律,夫人也是赞许的。因为她女儿凯茜就在耶鲁法学院,高我两级。凯茜入学前曾赴印尼支教,毕业后投身于法律援助和公益诉讼,是极具社会关怀的政治精英。所以我到了清华教书,也鼓励学生转变立场追求进步,下基层挂职、做公益事业或者争取进国际组织。若有强烈的兴趣,走学术道路当然也支持,尽管现在一哄而上所谓“国际化”的“一流大学”,完全官僚化了,实在不是适合“青椒”学者待的地方。总之,当官赚钱不应是精英大学的教育导向,那条独木桥不用宣传,已经人满为患了。事实上,便是培养干部,也得从基层抓起。而法学跟别的学科不同,需要社会经验和人事的历练。诚然,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主要得自于早年在边疆兄弟民族中间的生活磨炼。但是夫人的谆谆教诲,一如凯茜的身体力行,为我树了一面理想的旗帜。
 二〇〇六年十月,拙译《摩西五经》面世,夫人十分高兴。感恩节,她来剑桥探亲,住在鲁斯坦处,约我们一块儿到友人家聚餐,顺便把新书带给她(见《信与忘·感恩节的语录》)。席间众人谈及译经,玛莎说,加州伯克利大学奥特(Robert Alter)教授译注《摩西五经》(2004),颇受好评,你觉得怎样?我以为奥译事倍功半,未能脱出钦定本《圣经》的语汇风格而另辟蹊径,再现圣法之“荣耀与大力”(参《摩西五经·前言》)。夫人遂问:相比之下,库格尔教授是否高明些呢,他是你推崇的权威?我说,库先生有一本《圣经诗粹》(1999),也是蜚声学界的。但一部希伯来《圣经》只选译十八篇,太过“俭省”,穿插在先生精彩的导读里面,几乎被遮没了。译文的弱点,则类同奥译,学究气,呆板。这两位虽是头等的圣经学家,论译经,才气和笔力还稍嫌不足。夫人笑道,你那是拿剧作家大诗人的标准,来衡量学者的业绩了——她还记得我翻译《贝奥武甫》,是受了哈佛的副导师阿尔弗雷德(William Alfred, 1922~1999)先生同修辞学老师爱尔兰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 1939~2013)的朗诵与文字的激励(见《以赛亚之歌·饮水思源》)。
二〇〇六年十月,拙译《摩西五经》面世,夫人十分高兴。感恩节,她来剑桥探亲,住在鲁斯坦处,约我们一块儿到友人家聚餐,顺便把新书带给她(见《信与忘·感恩节的语录》)。席间众人谈及译经,玛莎说,加州伯克利大学奥特(Robert Alter)教授译注《摩西五经》(2004),颇受好评,你觉得怎样?我以为奥译事倍功半,未能脱出钦定本《圣经》的语汇风格而另辟蹊径,再现圣法之“荣耀与大力”(参《摩西五经·前言》)。夫人遂问:相比之下,库格尔教授是否高明些呢,他是你推崇的权威?我说,库先生有一本《圣经诗粹》(1999),也是蜚声学界的。但一部希伯来《圣经》只选译十八篇,太过“俭省”,穿插在先生精彩的导读里面,几乎被遮没了。译文的弱点,则类同奥译,学究气,呆板。这两位虽是头等的圣经学家,论译经,才气和笔力还稍嫌不足。夫人笑道,你那是拿剧作家大诗人的标准,来衡量学者的业绩了——她还记得我翻译《贝奥武甫》,是受了哈佛的副导师阿尔弗雷德(William Alfred, 1922~1999)先生同修辞学老师爱尔兰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 1939~2013)的朗诵与文字的激励(见《以赛亚之歌·饮水思源》)。
的确,夫人是最能理解我的:也许,中文读者更需要一个选本——圣诗撷英,她说。
自从回国服务,因为过节多半不在美国,加之夫人年迈,行走不便,联系就少了。今年便有些预感。入夏,曾得一梦,像是一个征兆。
矇眬中,又一次置身于日内瓦湖畔的小村,石头屋子,玫瑰篱笆,一切都那么熟悉而亲切。夫人就带我去拜访伯爵,如从前一样,一路芬芳,曲曲弯弯穿过花园来到古堡。进大门,顺旋梯登上客厅,依旧是那幅褪了色的挂毯,“狮心王理查见萨拉丁苏丹”。伯爵倚着枴杖,微笑着,一点没变。面容却苍白了许多,布满皱纹的皮肤镶着一缕阳光,几乎是透明的。
“于此,我吸着你的未来的烟馨”;进到书房,看我拿出一册《玻璃岛》送他,伯爵轻轻念出这么一句。
哦,是大海,我的伯爵,夫人也放缓了语速,“大海,永远在重新开始”。说着,她走到窗台,凝望着窗棂外的湖光。
然而伯爵似乎有所触动,喃喃道:是呀,重新开始。如果未来能化作烟馨,给人“酬报”,亲爱的朋友;让你在“一番深思过后,放眼远眺于众神之宁静”。
想起来了,“烟馨”“酬报”“重新开始”云云,是化自夫人喜爱的瓦雷里(Paul Valéry, 1871~1945)的名诗《海滨墓园》。我便同伯爵探讨,那片墓园若是诗人预感中的归宿,这“众神之宁静”(le calme des dieux)应作何解释,取什么象征?
倾谈良久,忽而意识到,窗台那边保持着沉默。回头看去,夫人已经挪了位置,背光坐下,面庞披着一道阴影,大理石般的白皙。又聊了一会儿,她还是不语;再看,整个人都白了,渐渐地,竟变得通体透明。
我心头猛然一紧,脱口叫了一声夫人——就醒了。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于铁盆斋
- 冯象:《圣诗撷英》,活字/北京三联,2017。
- 库格尔(James Kugel):《圣经诗理》(The Idea of Biblical Poetry: Parallelism and Its History),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
- 库格尔:《圣经诗粹》(The Great Poems of the Bible),Free Pres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