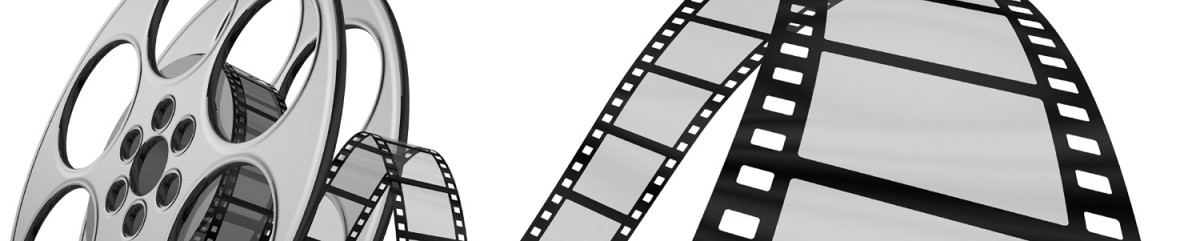
刘皓明:狼人病史:《阳光灿烂的日子》
Ce qui se réalise dans mon histoire, n’est pas le passé défini de ce qui fut puisqu’il n’est plus, ni même le parfait de ce qui a été dans ce que je suis, mais le futur antérieur de ce que j’aurai été pour ce que je suis en train de devenir.
我的故事中所实现的,不是那个为已经不再了的东西所定义的过去,甚至不是现在的我所包含的曾一度存在的东西的完成状态,而是那个我将会已经成为的样子之前的未来,当下的我正在走向它。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弗洛伊德在著名的《摘自一例幼儿精神病史》(Aus der Geschichte einer infantilen Neurose)中讲述了这样一个病例[1]:一个总是梦到窗外的树杈上坐着长着狐狸一样尾巴的白狼的成年病人,在弗洛伊德的诱导下把这个梦境还原为婴儿时目击的事件的回忆。而那个婴儿时目击的事件,依据弗洛伊德的分析,是尚在襁褓中的病人目睹了其父母交媾的场景。这个场景被称为“原初场景”(Urszene),而那个懵懂无知的婴儿因此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毁坏性的震撼,被称作“创伤”(Trauma)。婴儿把他当时看到的却完全不能理解的原初场景保留在了无意识的深处,并且同童年时听到的关于狼的格林童话《小红帽》(Rotkäppchen)混合起来。这一创伤的经验在日后以种种掩饰了的、扭曲了的形态出现在意识的表层,扰乱着成年的病人的精神状态,引发了诸如虐待、恐兽症、焦虑、耽迷等种种精神病症状。而狼的形象作为那一创伤经验的象征不断出现在病人的梦里,既指向了同时也掩盖了造成创伤的原初经验。在心理分析的疗程中,成年的病人对孩提时代的往事的追忆,由于身体竭力避免重新提出痛苦的创伤经验的自我保护本能而在实质上成为一种逆向的幻想(Zurückphantasieren)。这种以狼为其意象的逆向的幻想屏蔽了真实,为当下的意识构造了为它可以接受的故事:病人的所谓记忆实际上是虚构。
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以下简称《阳光》)就是这样一部仿佛是回忆、实际上是逆向幻想的虚构。主人公马小军(夏雨扮演)就是弗洛伊德的那个被称作狼人(der Wolfsmann)的精神病人;作为叙述自己童年经历的讲述人,他实际上潜在地把有识别力的观众当成了对他进行治疗的精神分析者和精神病学家;而作为他的经历的视觉再现的《阳光》则是我们在目前中国的文明中所能遇到的最经典的精神病病例。虽然没有迹象显示姜文或者原著作者王朔接触过弗洛伊德的《摘自一例幼儿精神病史》,然而《阳光》就其严格地符合弗洛伊德对所谓狼人所患精神病的种种症状的描述这一点,是不折不扣的当代中国的狼人病例;而其同狼人病例如此严格的契合又揭示了当前中国文明、文化和文艺中的一些深层的问题。因此电影所依据的原创小说的标题《动物凶猛》在不止一种意义上概括了这部小说/电影作品的内容:王朔的凶猛的动物在幻想的、扩展了和翻转了的意义上对应于弗洛伊德作为象征的狼(而且狼的确是为王朔所痴迷的一个意象,他有一部小说的标题就是《我是狼》,涉及同样的精神病症状),而王朔/姜文的《动物凶猛》/《阳光》就是我们当下的文明中所产生的狼人自叙的病史。
 《阳光》是通过主人公马小军和他同伴们的成长过程来展示叙述者幻想自己是狼的精神病症状的。这个幻想的故事是与主人公青春期的性觉醒同步的,但是却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狭义的力比多(Libido)被压抑与初次经验的告解录,它首先是一部揭示狼人幻想形成过程的故事,通过这一形成过程暴露出其意义远远超出主人公乃至创作者个人的重要性与普遍性,成为对我们集体无意识的精神病症的揭示。在马小军那里,被压抑的其实并不是单纯的青春期亢奋的力比多,而是同力比多混淆在一起的挣扎中和迷失中的本我和自我;作为他的病史的《阳光》主要不是一部叙述主人公同青春期性错乱挣扎的历史,而是一部寻找自我的历史,一部在对自我的寻求过程中的挣扎史。
《阳光》是通过主人公马小军和他同伴们的成长过程来展示叙述者幻想自己是狼的精神病症状的。这个幻想的故事是与主人公青春期的性觉醒同步的,但是却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狭义的力比多(Libido)被压抑与初次经验的告解录,它首先是一部揭示狼人幻想形成过程的故事,通过这一形成过程暴露出其意义远远超出主人公乃至创作者个人的重要性与普遍性,成为对我们集体无意识的精神病症的揭示。在马小军那里,被压抑的其实并不是单纯的青春期亢奋的力比多,而是同力比多混淆在一起的挣扎中和迷失中的本我和自我;作为他的病史的《阳光》主要不是一部叙述主人公同青春期性错乱挣扎的历史,而是一部寻找自我的历史,一部在对自我的寻求过程中的挣扎史。
贯穿故事始终的是有自闭症的少年马小军在被接纳为一个集团成员后在同辈面前不断证明自己的过程,而这种证明的欲望和必要性尤其因为他在这个集团的领袖刘忆苦(耿乐扮演)的面前所感到的自卑而得到极大的加强。刘忆苦这一形象主要是建立在大多以鬼魂形象出现在王朔的好几部小说中的人物卓越的基础上的(《动物凶猛》、《玩儿的就是心跳》等)。正像王朔小说中这一形象的原名所意味的那样,相对于第一人称的主人公而言,卓越/刘忆苦代表了主人公想要成为、在其面前感到不可救药地自卑的理想形象或者超我。作为主人公仰视的对象,卓越/刘忆苦又代表了马小军虽有犹无的父亲形象(拉康把这样的父亲形象叫法律la Loi),因此这个卓越/刘忆苦才是真正的狼,对应于弗洛伊德的狼人故事里狼人的父亲,并且具备弗洛伊德那里父亲所引起的所有的诸如俄底浦斯情结等象征含义和阉割焦虑等等。在超我和父亲面前证明自己同父亲一样也是狼的欲望驱使着马小军作出了故事中的几个最重大的行动。其中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在打群架时毫无必要地下手残忍,将一个被包围的男孩儿用砖拍昏。这种残忍一方面旨在证明自己的勇敢无畏,另一方面却也暴露了他缺乏领袖素质:同他们这伙孩子的王刘忆苦(他素有打架时手黑的名声)相比,他无谓的残忍表明他缺乏策略与统筹,缺乏作为这样的领袖所应该有的酷与自我控制,因此他同目光森森、不动声色的狼距离很远:这次斗殴并没有让他觉得自己变成了狼。马小军的第二个重大行动发生在“老莫”,即莫斯科餐厅,在一次在那里举行的生日宴会上他企图公开挑战刘忆苦。不管这次挑战是否真地发生了(这其实只是叙述者的妄想),马小军都遭遇到了深深的屈辱与失败。这次真的或想象中的失败成为构成全剧高潮的第三个行动的契机,即马小军强奸了对他友好的米兰(宁静扮演)。这是幻想自己是狼的狼人马小军最终的狼性行为,他企图通过在属于真的狼的那个女人身上证实自己的狼性,幻想自己是狼的狼人其这一行为的野兽性尤其通过他在这之前在滂沱的雨中凄厉的嚎叫得到充分的预示。
然而作为兽性的最终展示,马小军对米兰的强奸却是很成问题的。同前面打群架时对已经投降的男孩儿拍砖一样,作为狼的马小军选择了注定没有还手能力的弱者作为牺牲品;比拍男孩板儿砖还要复杂的是米兰是一个女性,而且还是一个名声不好的女性(至少在马小军心目中)。这就创造了一个让我们仔细观察主人公同异性的关系的机会。作为一个从年龄上到经验上都比马小军成熟的、肉体散发着吸引力的女人,即使撇开她成为了刘忆苦的女朋友这点不谈,米兰对马小军都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对于这种压力,同王朔小说中主人公对卓越、高阳等使他感到自卑或压力的同辈的态度一样,马小军本能的强烈反应是依恋。马小军先是认识了米兰的照片(即镜像)然后才认识她这个人的过程尤其强化了他同米兰的关系实际上属于拉康所谓镜子阶段(le stade du miroir)的初期自恋这一性质。在同米兰的这种初期自恋性质的关系里,马小军的对其镜像依恋只能是两人之间的、秘密的、属于内心的、肝肠肺腑的。这种依恋潜在地使我们的主人公或主人公正在形成的自我节制的超我机能感到难堪,使他极可能成为他的同伴们揶揄的目标,因为实际上这是一种口腔期的、有同性恋倾向的情感。米兰归属于刘忆苦使这种潜在的难堪变成了一种危机,它使两个对主人公最具压力的人物结合在一起,同时又凸显出自己有可能和米兰一样成为女性化的、服从的、被支配的,这就彻底让自卑的自我失去了被尊重的机会,失去了成为狼的机会。它对主人公脆弱的自我和他在他的集体里的脆弱的地位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因此最终导致了马小军的崩溃和暴力。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的马小军越是内心中对米兰有不可抵御的依赖感,越是要在他人面前对她粗暴,因为这就是他内心冲突的外化表现形式:社会的(或者他所属的那个小社会的)性别规定强迫性地压抑心理上性别错乱的冲动,这种压抑引起一系列危机。在电影里,这种内心的危机先是导致了前面提到的莫斯科餐厅的那场戏,然后又有了游泳池中对米兰的羞辱。马小军在公共场合和在同伴面前千方百计侮辱米兰,以借此显示自己对米兰在情感上和欲望上的解脱与独立。然而这种粗暴并没有把他心中的焦虑驱除掉,反而愈发激怒了自己,把自己推到崩溃的边缘,最终引向对米兰的强奸。
作为仇恨的最后表达的强奸最强烈地表达了马小军对女人的仇视。这种仇视不仅仅是针对一个女人的,也是针对自己内心中女性化的冲动的。这种产生于男性不安全感和自卑心理的仇恨由于感觉自己被背叛而急剧增强。此外马小军身上这种仇女症的根源还是源于大文化的。从老舍到王朔,北京文化乃至他们所代表的传统中国大众文化中对女人的干净或纯洁与脏的观念在《阳光》中从骑自行车的不良男孩在胡同横行时所哼唱的下流小调中得到了最粗俗、最赤裸的体现。这种观念一方面依据萨满道教的通俗理论认女人为肮脏的,一方面把防止女人不被污染视为同异性关系中最重要的义务。这种对女人的蔑视尤其令主人公对自己内心中的女性化倾向感到恐惧。这种文化的仇女观念还要求而且也只能接受“堕落”女人的堕落必须是被迫的,迫于经济或恶势力的,否则它会把“自甘堕落”的女人视为最肮脏、最危险、最万劫不复的。这种观念不能接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女人的性的自主。所以于北蓓(陶虹扮演)虽然更漂亮、更挑逗,却对马小军毫无吸引力,因为她是公开地、自主自愿地“堕落”的。不仅如此,她还有一种几乎与生俱来自如和自信,一种酷,一种令马小军不能正视的几乎胜过男性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同米兰因年龄和经验所具有的优势不同,它是先天的、绝对的、令人绝望的,其拥有者越是似乎对自己的优越浑然无知,她的优越就越是咄咄逼人。米兰则正相反,她对马小军降尊纡贵般的宽容与接纳实际上透露出她在同同龄的和年长于她的男子的关系中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这种对自身性别的不安全感是她的致命弱点,想成为狼的马小军本能地嗅到了米兰同自己共同的弱点,于是决定把她变成自己的依赖、心腹、乃至情人,而当这种依赖和依恋在他看来被背叛了时,他就像对那个已经失去抵抗力的男孩儿下毒手那样,敢于把她当作自己暴力攻击的对象、当作自己的猎物和牺牲品。她的原本可以让他找到道德优越感的“堕落”成为这种暴力的道德理由,使他至少在诡辩的层次上心安理得地为他的强暴行为辩护(这种心理变化过程在王朔的《玩儿的就是心跳》中表现得最淋漓尽致)。所以在强奸了米兰之后,马小军朝她报复性地吼道:“有劲!”这是对他强暴的动机的充分揭露。因此她首先是他满足和实现自我的目标与发泄内心最深处的挫折感的对象,作为欲望目标的她降为他行动的次要的甚至非常次要的动机。
 除了电影中俯拾皆是的种种经典的弗洛伊德式形象和象征(马小军对父亲的旧军装的摆弄,把避孕套当作气球吹等等),《阳光》之所以应该被视为一部精神病史尤其是因为作为成年的叙述者显现出严重的精神疾病的症状。片末坐在大轿车中的成年的主人公(由导演姜文本人亲自扮演)及其昔日的伙伴由于黑白的效果在视觉上强化了他们精神的病态,从而同彩色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形成强烈的对比。虽然电影的格式和结构不允许详细正面交待主人公及其朋党当下的状态,但是这部电影作为自叙行为已经说明了主人公当下的病理状态。况且由王朔及其读者(其中首先包括姜文)所构成的社会和文化层次是那么广泛,也根本用不着在电影里详细铺陈患者们目前的症状。虽然姜文把原著更直接地揭示其与心理分析的密切关系的标题换成了现在这个似乎更有诗意的标题,他并没有改变原著作为一份精神病史的基本要点。如果把动物改成阳光多少淡化了“狼人”的痕迹,它却加强了全剧作为逆向幻想的虚构性回忆的实质。这是因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阳光实际上并不灿烂,整部电影自始至终笼罩在一种黄昏般的老照片色彩中,这是一种回忆的色彩,对比于黑白的、黯淡的“现在”。而黄昏般的过去仿佛又是在暗示“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暗示说我的童年是宿命的,是绚丽地黯淡的,是建立在儿童对痛苦的迅速遗忘之上的开心的,是凄楚岁月中的美仑美奂的,是感伤的,是自怜和自恋的。的确,仅就电影本身透露的种种迹象看来,主人公/作者的精神病症状最突出地表现为严重的自恋情结。虽然这种情结在王朔的原著中比姜文的电影来得更触目惊心,但是就是在电影中其表现也已经很经典了:正像自恋的神话原型纳尔西斯(Narcissus)是因为在水边看到自己的映象而死于对自己的相思那样,《阳光》让马小军象征性地死在游泳池的水面上。当姜文让镜头紧跟马小军以慢动作缓缓爬上十米跳台又让镜头久久定格在马小军漂浮的尸体上时,作为精神病症状的自恋达到了顶点。从选择酷似少年姜文的夏雨主演《阳光》到原作者王朔作为后来“殉难”的一个黑帮老大角色出现并接受元首般的礼遇,《阳光》并不屑于掩饰这种极度的自恋和自我膨胀。这种自恋和自我的膨胀仿佛在向作为医生和分析家的观众们说明少年时代一直苦于自卑和自我不平衡的主人公通过小说和电影的形式在这个媒体和娱乐业发达的时代里终于虚幻地克服了自卑的情结,最终打败了昔日自己自愧不如和在他面前自惭形秽的优异者。在这一点上,姜文改变了王朔的原作,在结尾处作为迟到的报复让刘忆苦变成一个失去了记忆的痴呆,把这种持续地同父亲般权威和优越的形象的心理较量及其幻想中的满足用漫画般的手法揭示出来,从而不容置疑地说明了叙述者精神病的延续性和严重性(顺便说,王朔小说中的卓越在海军服役时死于一次奇怪的事故)。另外一个作用相同的情节就是王朔本人出现在莫斯科餐厅的那场戏,它其实就是电影在自己里面替自己颁奖的场面。从经典意义上的叙事结构的完整这个角度说,这两个情节都是蹩脚的,是败笔;然而作为一部真实的精神病史,它们却都是应有的,合理的,真实的。它们的存在仿佛说明作为精神病病历、作为病理档案,《阳光》是原始的、未剪裁的、未经编辑加工的,因而对于一个把它当作精神病纪录的心理分析家来说也就是最可靠的。
除了电影中俯拾皆是的种种经典的弗洛伊德式形象和象征(马小军对父亲的旧军装的摆弄,把避孕套当作气球吹等等),《阳光》之所以应该被视为一部精神病史尤其是因为作为成年的叙述者显现出严重的精神疾病的症状。片末坐在大轿车中的成年的主人公(由导演姜文本人亲自扮演)及其昔日的伙伴由于黑白的效果在视觉上强化了他们精神的病态,从而同彩色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形成强烈的对比。虽然电影的格式和结构不允许详细正面交待主人公及其朋党当下的状态,但是这部电影作为自叙行为已经说明了主人公当下的病理状态。况且由王朔及其读者(其中首先包括姜文)所构成的社会和文化层次是那么广泛,也根本用不着在电影里详细铺陈患者们目前的症状。虽然姜文把原著更直接地揭示其与心理分析的密切关系的标题换成了现在这个似乎更有诗意的标题,他并没有改变原著作为一份精神病史的基本要点。如果把动物改成阳光多少淡化了“狼人”的痕迹,它却加强了全剧作为逆向幻想的虚构性回忆的实质。这是因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阳光实际上并不灿烂,整部电影自始至终笼罩在一种黄昏般的老照片色彩中,这是一种回忆的色彩,对比于黑白的、黯淡的“现在”。而黄昏般的过去仿佛又是在暗示“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暗示说我的童年是宿命的,是绚丽地黯淡的,是建立在儿童对痛苦的迅速遗忘之上的开心的,是凄楚岁月中的美仑美奂的,是感伤的,是自怜和自恋的。的确,仅就电影本身透露的种种迹象看来,主人公/作者的精神病症状最突出地表现为严重的自恋情结。虽然这种情结在王朔的原著中比姜文的电影来得更触目惊心,但是就是在电影中其表现也已经很经典了:正像自恋的神话原型纳尔西斯(Narcissus)是因为在水边看到自己的映象而死于对自己的相思那样,《阳光》让马小军象征性地死在游泳池的水面上。当姜文让镜头紧跟马小军以慢动作缓缓爬上十米跳台又让镜头久久定格在马小军漂浮的尸体上时,作为精神病症状的自恋达到了顶点。从选择酷似少年姜文的夏雨主演《阳光》到原作者王朔作为后来“殉难”的一个黑帮老大角色出现并接受元首般的礼遇,《阳光》并不屑于掩饰这种极度的自恋和自我膨胀。这种自恋和自我的膨胀仿佛在向作为医生和分析家的观众们说明少年时代一直苦于自卑和自我不平衡的主人公通过小说和电影的形式在这个媒体和娱乐业发达的时代里终于虚幻地克服了自卑的情结,最终打败了昔日自己自愧不如和在他面前自惭形秽的优异者。在这一点上,姜文改变了王朔的原作,在结尾处作为迟到的报复让刘忆苦变成一个失去了记忆的痴呆,把这种持续地同父亲般权威和优越的形象的心理较量及其幻想中的满足用漫画般的手法揭示出来,从而不容置疑地说明了叙述者精神病的延续性和严重性(顺便说,王朔小说中的卓越在海军服役时死于一次奇怪的事故)。另外一个作用相同的情节就是王朔本人出现在莫斯科餐厅的那场戏,它其实就是电影在自己里面替自己颁奖的场面。从经典意义上的叙事结构的完整这个角度说,这两个情节都是蹩脚的,是败笔;然而作为一部真实的精神病史,它们却都是应有的,合理的,真实的。它们的存在仿佛说明作为精神病病历、作为病理档案,《阳光》是原始的、未剪裁的、未经编辑加工的,因而对于一个把它当作精神病纪录的心理分析家来说也就是最可靠的。
L’ambiguïté de la révélation hystérique du passé ne tient pas tant à la vacillation de son contenu entre l’imaginaire et le réel, car il se situe dans l’un et dans l’autre. Ce n’est pas non plus quelle soit mensongère. C’est qu’elle nous présente la naissance de la vérité dans la parole, et par-là nous nous heurtons à la réalité de ce qui n’est ni vrai, ni faux.
对过去的歇斯底里的揭示所包含的两可性并不主要是由于其内容在想象和现实中间的摇摆不定,因为它在两者中都居处着。也不是因为它就是谎言。其原因是它向我们托出了诞生在语言中的真理,通过它我们冲撞上既不真也不假的东西的实在性。
——雅克·拉康
如果《阳光》是这样一部在症状上可靠地记录了一例童年精神病史的作品,那么最初造成这种精神病的原初场景是什么呢?我们能够像弗洛伊德那样或者像弗洛伊德那样有信心地复原某个事件,认定它是那个原初场景吗?不难联想到,马小军在抽屉里翻出父母使用的避孕套、懵懂无知地把它当气球吹的情节可以看作同弗洛伊德构造的狼人还是婴儿时所见证的父母行房的原初场景形成完满的对应。然而在留下明显的创伤这一点上,这一情节远比不上他在北京展览馆前被警察拘留时所受到的屈辱来的强大,而且这样的屈辱连同他的父亲给他的耳光是经常的、慢性的、其第一次的出现已经无从记忆了。这种由叫做法律(la Loi)的机构所强加的屈辱极大地加深了主人公普遍的挫折感,造成了马小军的妄想症:在那次被拘留后他在家里一个人自言自语,在幻想中打败了在现实中他只能懦夫般地服从和忍受其侮辱的人们。这是电影中最关键的一个情节,它成为整部电影的写照,因为电影中其他最重大的那几个情节——斗殴,挑战刘忆苦,直至强奸米兰——都不过是受挫的叙述者/主人公像在自己家中自言自语那样所制造的虚构或幻想而已,其动机是把自己投射到一个凶猛的狼的形象上以平衡在现实中所遭受的不平衡和屈辱。这种叫做法律的留下巨大创伤和引起精神病的暴力是所有那些代表父权的势力——他自己暴躁的父亲、几乎所有的成年人、刘忆苦等等——的最终极的代表。在这种权威的法律面前,马小军甚至在想象中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像颠覆刘忆苦那样颠覆它的希望。叙述者可以让刘忆苦最后变成痴呆,但他却不能让威慑和凌辱他法律变得无能,虽然如果他愿意的话,随着他成年,他可以——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加入它,使自己成为法律的一部分,从而成为新的压抑者。不过叙述者最终还是像弗洛伊德的狼人那样下意识地选择了逃避,用种种表层记忆(Deckerinnerung)掩盖了他见证过的原初场景。
如果狼人马小军所经历的原初场景不是其父母行房而是法律进行强暴的场面,那么对这个原初场景的暗示实际上在《阳光》中触目皆是,不,不仅触目皆是,而且充耳皆是。《阳光》里那些来自文革时代的进行曲就是这样的法律的声音,它们成为那些同样代表了这种法律的苏联式旧军装以及其他种种制服的听觉对应,成为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阳光》中在视觉和听觉上的两个主要母题。这种由多媒体直接表现的和象征出来的压抑性的父权形象同伤感的自恋与怀旧的主题密不可分地混合起来,配合着故事情节从气氛上烘托出叙述者的精神病状态。这种烘托同时也构成了这部电影的抒情性。而且正是这种抒情性使得《阳光》具有一种超出其故事的历史背景参照框架的普遍吸引力,使得它成为中国少有的真正青春片,加入了由《没有信经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 Nicholas Ray导演)、《青春残酷物语》(大岛渚导演)、《坏孩子的天空》(北野武导演)等所代表的那种电影的族类(genre)。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阳光》所属的这个体裁都是非常不稳定的。在创作者这一方面尤其如此。这种不稳定的根源在于它赖以在观众那里制造会道门式崇拜的抒情性是同其精神官能症分不开的,特别是同其自恋情结分不开的。从根本上说,这种不稳定性就是导致王朔“江郎才尽”的原因(姜文在《阳光》之后便告别了这种公然的自恋)。这是因为作为心理分析的原始材料和精神病史的叙述作为临床精神分析的疗程本身就是有治疗效果的;而一旦这种疗程成功了(即便就在其相对于日常生活最低程度的正常化而言),作为病人的叙述者的叙述冲动就停止了。然而艺术家从定义上说是应该超越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病态的;艺术就其定义而言也是应该超越精神病人虚构性叙述的自发性的。因此像《阳光》这样同心理分析学严格吻合的作品在艺术上其实是成问题的,这种吻合并不是一种荣耀和保证其艺术价值的资本,反而标志着其在更深刻的文化意义上的缺陷。因为《阳光》不是把弗洛伊德的《摘自一例幼儿精神病史》自觉地作为大纲而撰写的,它不是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等作品那样自觉地、反讽地利用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而创作的,而是一种完全暗合于弗洛伊德文本的情不自禁的、发自肺腑的、没有反思没有批判的倾诉。它是“真诚”的,想要进行灵魂搜索的,自以为是深刻反思的(王朔本人不止一次地说《动物凶猛》是他自己最钟爱的作品)。正是这种“真诚”感染了观众,是作品产生抒情性的主要因素。然而这种抒情性却被它可以成为心理分析学经典的原始病史这一事实所削弱乃至颠覆了。而由于这种可以被心理分析学所涵盖和颠覆的抒情性是触动广大观众底蕴的根本因素,是其成功的秘密,因而又暴露了作者和观众所共享的一种广泛的集体无意识。由于这种集体无意识是在其创作者、观众、乃至批评家的反思和自我意识范围以外的,这种原始状态就潜在地成为文化意义上的集体歇斯底里和集体精神官能症的绝好土壤。事实上,以自恋为其主要特征的这种精神官能症一直在泛滥,并且正在妨害中国的精神生活的健康和发展。
《阳光》同弗洛伊德的狼人病史乃至同他的心理分析学说不自觉的契合还意味着一个更深层次上的问题。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实质上是一种彻底唯物主义的、反理想主义、反浪漫主义、反超验主义的、本质上是非利士人(Philister)的学说。一部作品乃至整个国民心理可以被完全置于这样的学说的解释框架之下而并无自觉,并无超越,就像没有文字和历史的大洋洲部落成为以研究社会的无意识基础为其任务的欧洲人类学的绝好原始资料与活标本一样,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和应该引以为耻的。而理应成为国民的神父、导师、分析家的批评家和学者们居然也无力诊断《阳光》和《阳光》背后集体的精神官能症与集体无意识(他们给王朔的终审判词是一句听上去不悦耳的“小骂大帮忙”),则令人几近绝望。从根本上说,在姜文和王朔那里原初场景留下的创伤无异于这种绝望。
(原载于文静编《楼上楼下,屋里屋外》,北京:三联书店,2004:59-72)
——————————————————————————–
[1] Studienausgabe, S. Fischer, VIII, 126-231。
這譯文簡直糟透了:
Ce qui se réalise dans mon histoire, n’est pas le passé défini de ce qui fut puisqu’il n’est plus, ni même le parfait de ce qui a été dans ce que je suis, mais le futur antérieur de ce que j’aurai été pour ce que je suis en train de devenir.
我的故事中所实现的,不是那个为已经不再了的东西所定义的过去,甚至不是现在的我所包含的曾一度存在的东西的完成状态,而是那个我将会已经成为的样子之前的未来,当下的我正在走向它。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第一,這是中文嗎?有人可以理解嗎?儘管拉康以「艱澀」見稱,也未至於這樣不可理喻吧?
第二,撇開慘遭「虐待」的中文不談,原文也被劉先生嚴重扭曲:
1. “le passé défini” 不是「所定义的过去」,而是法語動詞的一個時態,又叫 “le passé simple”,指過去情境中一個完結了的動作,此動作與「現在」已再無關係。譯成「所定义的过去」,表示劉先生似乎連基礎語法也未能掌握。
2. “le parfait” 和 “le futur antérieur” 跟 “le passé défini” 一樣,也是時態名稱。而且這些字眼分別對應之後的 “a été”,”aurai été” 及 “fut”,其結構非常明顯,而身為文學研究者及譯者的劉先生居然對這種修辭技巧如此麻木和生疏,實在令人意外。
現在我嘗試翻譯一下拉康:
「在我故事裏真正發生的,不是既成陳跡的過去時態,因為它已不復存在了,更不是在當下之我中,記錄那些現成事實的完成時態,而是一種先將來時態,為那個我所不斷發展以求實現的自己,述說我首先將會如何。」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以劉先生的水平,真有資格批評錢鍾書嗎?而錢鍾書會犯劉先生這些錯誤嗎?治學最重要的,是老實和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