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猛: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
“In my youth,” said his father, “I took to the law, And argued each case with my wife; And the muscular strength, which it gave to my jaw Has lasted the rest of my life” —— Lewis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一、理性化的命运与人的自由:韦伯的问题与困境
(1)韦伯的问题域
二战以后,德国学界逐渐恢复了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兴趣,随着对韦伯思想的研究渐趋深入,美国社会学界生产的韦伯形象受到了越来越广泛和严厉的批评。在美国社会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韦伯的思想肖像”,通过将韦伯“实证社会学化”、“去历史化”和“单面化”,将韦伯充满张力的复杂著述简化、改造为与主流社会学理论相容的教条学说,并利用这种教条化的韦伯形象(一种以规范秩序为核心问题的社会学理论)来为主流社会学界的诸多实践意识形态提供依据,无论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和支配社会学,还是他的“科学学说”(Wissenschftslehre)都经历了类似的命运。
不过,同样受到挑战的还有某种在欧洲知识界中一度占据重要地位的韦伯解释。这种解释的突出代表就是卢卡奇(Georg Lukács)及此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如果说,美国社会学界生产的“韦伯的思想肖像”是一个乐观主义社会理论的“偶像”,那么,卢卡奇这位与韦伯在海德堡交往密切的“朋友和学生”就创造了一个悲观主义社会理论的“偶像”,只不过这个“偶像”,没有在理性化的进行曲伴奏下的现代化“喜剧”中出场,而是在理性毁灭的悲剧中扮演主角罢了。但从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对韦伯毫不留情的批评中,我们可以发现,韦伯的这两个形象之间实际上相去不远。[1] 如果套用韦伯本人的说法,帕森斯和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对韦伯的解释与马尔库塞的理解,分歧只在于他们各自的价值评判立场不同,但他们对韦伯著作却采用了类似的解释原则,甚至作为这种读解基础的 “世界图景”,都是同一个话语空间的产物。[2] 只不过一方将韦伯的理性化看作是现代化,而另一方则将这种所谓“现代化”的“理性化”看作是工具理性肆无忌惮的扩张,其实质是异化或者说是一种十足的疯狂。[3] “在理性的效率之中有计划地消灭成百万的人,有计划地毁灭人类劳动这个进一步繁荣的源泉”。[4]
在1975年,针对这些主流解释,德国学者腾布鲁克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挑战:韦伯的核心问题倒底是什么?腾布鲁克指出,现有的韦伯形象存在严重的问题,而要重新理解韦伯,就要弄清楚韦伯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抛弃将韦伯的著述神圣化(或者说是教科书化)的做法,从著作发展史出发,注意韦伯著述中各种不同文本在形态上的差别,将韦伯笔下成熟的、确定的观点与那些尚在摸索过程中,属于“未完成”性质的著述区分开。从这个角度出发,腾布鲁克指出,理解韦伯思想的关键并非韦伯去世后由韦伯夫人与温克尔曼等人编纂的《经济与社会》,而是韦伯本人生前亲手编订出版的《宗教社会学文集》,尤其是韦伯在临终前为这一文集撰写或修订的几篇提纲挈领的文章:《文集》“前言”(Vorbemerkung)[5],“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6] 的“导论”(Einleitung)以及著名的“中间反思”(Zwischenbetrachtung)[7]。这些文章是我们理解韦伯的中心问题的“钥匙”。[8]
 尽管对于腾布鲁克的具体观点,尚存争议[9],但腾布鲁克的方法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他对韦伯本人作品的“除魔”工作提醒我们:一方面,如果想探讨韦伯所分析的各种实质问题,首先要从韦伯的整体思路着眼,从构建韦伯的问题域入手;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韦伯本人对他关注的这些问题的回答,并未构成一个结构完整、无懈可击的著述体系,相反,韦伯的著述是由不同创作时期,出于不同目的撰写的文本构成的一个充满张力与冲突的 “战场”,这些在韦伯思想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所形成的文本,既必须放在韦伯乃至整个德国知识界的各种问题域中来理解,又要考虑到文本本身的“实验性”,毕竟韦伯有许多论述只是尝试性的探索,而非最终答案。当然,上述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尽管韦伯文本解释过程中的“解释学循环”问题要比通常情况复杂得多,但如果我们能够同时考虑腾布鲁克提醒我们注意的这两个方面,我们也就有可能掌握了一条解释韦伯社会理论的重要方法原则,使我们去运用韦伯的思想,通过发展他的问题与思路,从而在一个与韦伯共同探索的高度来重建韦伯的文本,而不是将这些文本当作可以不加思考地“寻章摘句”的神圣语录。毕竟,真正追随韦伯的人并不是要去创建韦伯学派,而是要和韦伯一起提问。[10]
尽管对于腾布鲁克的具体观点,尚存争议[9],但腾布鲁克的方法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他对韦伯本人作品的“除魔”工作提醒我们:一方面,如果想探讨韦伯所分析的各种实质问题,首先要从韦伯的整体思路着眼,从构建韦伯的问题域入手;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韦伯本人对他关注的这些问题的回答,并未构成一个结构完整、无懈可击的著述体系,相反,韦伯的著述是由不同创作时期,出于不同目的撰写的文本构成的一个充满张力与冲突的 “战场”,这些在韦伯思想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所形成的文本,既必须放在韦伯乃至整个德国知识界的各种问题域中来理解,又要考虑到文本本身的“实验性”,毕竟韦伯有许多论述只是尝试性的探索,而非最终答案。当然,上述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尽管韦伯文本解释过程中的“解释学循环”问题要比通常情况复杂得多,但如果我们能够同时考虑腾布鲁克提醒我们注意的这两个方面,我们也就有可能掌握了一条解释韦伯社会理论的重要方法原则,使我们去运用韦伯的思想,通过发展他的问题与思路,从而在一个与韦伯共同探索的高度来重建韦伯的文本,而不是将这些文本当作可以不加思考地“寻章摘句”的神圣语录。毕竟,真正追随韦伯的人并不是要去创建韦伯学派,而是要和韦伯一起提问。[10]
运用著作发展史的方法,腾布鲁克重构了韦伯的理性化命题。在腾布鲁克看来,韦伯“毕生的论题”就是“何为理性”的问题。[11]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韦伯着手研究了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在韦伯的笔下,这一历史过程的核心就是“除魔”。[12] 因此,要理解理性化的历史阶段和各个环节,就必须考察除魔的历史。
腾布鲁克的文章在方法论上的出发点博得了广泛的赞赏,但他的具体结论却受到了许多非议。学者们指出,仅仅将韦伯的核心问题归为除魔的论题,未免过于单薄,似乎无力支撑整个韦伯著作的复杂性,毕竟“除魔”这一说法在腾布鲁克自己认定的几篇韦伯关键文本中,也只出现了两、三次而已,很难称得上是韦伯的核心概念。[13] 而且,“除魔”的概念本身果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韦伯的整个著述吗?一些学者也深表怀疑。施路赫特就对腾布鲁克的命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腾布鲁克有关《经济与社会》的“解构工作”尽管在方法论上意义重大,但却不免矫枉过正。过于强调《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重要意义,却忽略了《经济与社会》[14] 的重要性。[15] 尽管《经济与社会》不再象以往那样被看作是韦伯的社会学遗嘱,但其中包含的丰富论述无疑是理解韦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中的大量文本(特别是第一卷)属于韦伯在1915年后的成熟期作品,对于理解韦伯思想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不过在有些学者眼中,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腾布鲁克的观点表面上是要批评美国式的韦伯形象,实际上却是在捍卫这种已经濒临危机的观念。而要真正理解韦伯的思想,就必须彻底抛弃这种从“现代化”角度思考理性化的思路,真正回到韦伯自己的问题域中。[16]
在亨尼斯看来,韦伯的理论与今日所谓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所谓“社会学”关注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17] 要理解韦伯关心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就要将韦伯的论述重新放回当时德国思想界,乃至一个更广阔的思想传统中,不受今天狭隘的专业化学科体系的束缚。在这样的视角下,韦伯一方面被视为整个德国哲学人类学传统的一个现代传人,直接继承了德国哲学人类学和性格学对人(特别是人格与个性)的关注;另一方面韦伯又与马基雅维里以降,以卢梭与托克维尔为代表的经典政治哲学传统血脉相连,关注的焦点是现代政治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韦伯的核心问题就在这两个思想传统的交汇处,即“现代命运下人的发展”的问题。根据洛维特的经典论述,也就是在一个“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灵”的“除魔的世界”中,如何拯救人最后的尊严,而人的尊严就是人的自由,没有自由,也就谈不上什么尊严。[18] 亨尼斯强调,只有从这样的问题域出发,才能理解韦伯的理性化命题:“韦伯的主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理性化过程,而是实践的生活行为的理性化过程”,韦伯关注的“只有那些与‘所有实践伦理的形式’和‘生活方式的理性化’有关的‘理性化过程’”。[19] 这一思路是理解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键。韦伯在这本书中关心的问题并非新教如何通过造就资本主义的“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早在1902年,桑巴特(Werner Sombart)就已经在他出版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分析过这个问题,而韦伯明确告诉读者,他关心的问题与桑巴特不同。[20] 韦伯关心的问题是新教如何塑造了一种伦理意义上的生活风格(ethical Lebensstil),而正是这种生活风格标志着资本主义在人的“灵魂”中的胜利。
亨尼斯的解读无疑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但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将韦伯放在更为广泛的思想背景中并没有错,但因此忽视了韦伯一代学者重建社会思想的努力,仅仅将他的观点看作是数百年的经典问题的延续,不免矫枉过正了。韦伯本人一再讥讽对科学问题采取一种半吊子的业余作风或文人习气[21],而亨尼斯的做法却恰恰是在将韦伯的论述“业余化”。[22] 而且,隐藏在亨尼斯具体观点背后的理念似乎更令人怀疑,将韦伯视为一个对现代性充满怀疑,对古老的农业社会式的自由抱有强烈怀旧情绪的浪漫主义者,尽管在文本上并非毫无依据,但却很难与韦伯的总体形象相符。[23] 最后,亨尼斯与腾布鲁克一样,也未能均衡地考虑韦伯的整个文本,往往忽视了《经济与社会》,以及《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有关中国和印度宗教的研究。大概因为这些成熟的研究往往不符合亨尼斯的“反社会学”(anti-sociology)取向,反而被弃置一旁。
也许理解韦伯的问题,就需要做韦伯的同伴,而不是死人或僵尸。需要和韦伯一起,甚至要走得更远,站得更高。在腾布鲁克的基本思路、洛维特-亨尼斯的解释传统与施路赫特的文本重建基础上,考察韦伯留给现代社会的,无论在思想和实践中都始终难以逃避的问题:理性化与自由。
(2)新教伦理命题: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
韦伯晚年开始注意到,并不仅仅存在一种形态的理性化,在中国等非西方地区同样存在理性化的形式。但是,韦伯始终反对进化-历史观念中的相对主义。[24] 在韦伯眼中,“近代西方形态”的理性化仍然具有“独特性”,[25] 而这种“独特性”就体现在理性化是“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有效性的发展”,用韦伯的话说,就是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问题”。[26] 正如腾布鲁克一再指出的,作为“普遍历史意义的”理性化,并非纯属偶然的历史事件,而具有内在的逻辑。[27] 在我看来,理性化的普遍历史意义,正体现在理性化是“发展的”。换句话说,西方理性化的独特性,之所以具有普遍历史的意义,在于理性化是能动的理性化。
有关韦伯思想中的“发展”(development)或“进化”(evolution)的问题聚讼纷纭,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这一极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只能简明地指出:必须区分“发展”与“进化”,韦伯笔下经常出现的“发展”一词并没有任何历史规律的意涵,它的意涵往往是(1)历史运动的逻辑,这往往是多重因素造成的局势效果;(2)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普遍历史”的意涵:即西方理性化由于内在的张力,从而具有了进一步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事实上,“发展”的这两个意涵是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因为理性化本身是开放的,多元的,所以才是能动的,从而具有普遍历史意义,即能够通过吸纳越来越多的异质性力量,通过抗衡与冲突来发展。[28]
那么独特的西方理性化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呢?在韦伯早期有关新教伦理问题的分析中,就是作为历史命运的理性化与作为人的自由的“理性化”之间的复杂张力关系。亨尼斯认为,韦伯思想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生活秩序与个性之间的张力,但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秩序与个性或伦理理性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韦伯在为《宗教社会学文集》文集撰写的前言中指出,西方理性化的独特性体现在诸如系统严密的史学、政治思想和法律体系,“理性的和谐的音乐”、“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理性的国家和“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这些都属于韦伯所谓的“诸社会秩序”(die geselleschaftlichen Ordungen)。[29] 而这些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其突出表现就是各种系统化的程序技术的发展,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概念系统和逻辑方法,西方音乐中以记谱系统为手段的和声,西方绘画中的空间透视法,作为理性国家前提的科层制,以及作为理性资本主义企业核心的以复式簿记制度为基础的货币形式的资本核算等等。[30] 但自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核心问题就并不仅仅是这种不同社会领域中不同形态的程序技术的“自主”发展逻辑,也不是不同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如何影响了程序技术的发展[31],而是程序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实践行为的伦理理性化,以及与人的个性形塑之间的关系。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前言中,韦伯明确地表明了他关注的这一焦点:“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践理性的生活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性情倾向”。[32]
 因此,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人的生活方式或实践行为的伦理理性化就成为分析的焦点。因为,正是这种伦理理性化的出现,即人们的生活行为的纪律化(disciplinieserung)和条理化(methodisierung)[33],构成了理性资本主义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关键环节,将“新教伦理”与所谓“资本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而随着韦伯将“新教伦理命题”进一步推广到整个西方的理性化进程,这一分析思路,就具有了普遍历史的意涵。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正是因为这种理性化根植于人的生活行为的伦理理性化,它才具有了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体现在,社会秩序理性化的动力来自于伴随伦理理性化过程的冲突与张力。
因此,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人的生活方式或实践行为的伦理理性化就成为分析的焦点。因为,正是这种伦理理性化的出现,即人们的生活行为的纪律化(disciplinieserung)和条理化(methodisierung)[33],构成了理性资本主义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关键环节,将“新教伦理”与所谓“资本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而随着韦伯将“新教伦理命题”进一步推广到整个西方的理性化进程,这一分析思路,就具有了普遍历史的意涵。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正是因为这种理性化根植于人的生活行为的伦理理性化,它才具有了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体现在,社会秩序理性化的动力来自于伴随伦理理性化过程的冲突与张力。
在为“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撰写的导论中,韦伯清晰地表述了这一伦理理性化中蕴含的张力。在这篇充满对现代社会理性化深刻洞察的文章中,韦伯指出,在近代西方的历史中,推动生活秩序彻底理性化的力量,恰恰是救赎宗教中有关彼岸的“伦理预言的观念力量”(die ideellen Macht ethischer Prophetien)。[34] 救赎宗教的预言从礼仪转向伦理是与理性的世界图景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伴随着这种“世界的除魔”,在先知和救世主的宗教与世俗世界及其秩序之间,形成了持久的紧张关系。[35] 在这种紧张关系下,与宗教与救世道路改变了,从冥想地“逃避世界”转向积极苦行地“改变世界”。这样,“大师式”的宗教信仰(Virtuosen Religiositāt),就通过形塑信徒的惯习(Habitus),使其日常生活实现了伦理的理性化。这种“英雄主义“或“大师式”的宗教信仰(新教诸教派)的宗教资格,“…正是在日常考验出来的。不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日常,而是为神服务的、有条理的,理性化的日常行动。将日常行动以理性的方式上升为天职,成了救赎的保证。在西方,宗教大师们的教派成了生活行为有条理的理性化的酶,而不象亚洲那些冥想的或纵欲的或麻木的神魂颠倒的人们的团体那样,充当渴望脱离人世间活动的无意义状态的活塞”。[36] 因此,作为社会秩序理性化的关键,伦理理性化的原动力,正是来自对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行为加以理性化,这种理性化,就是要根据救赎宗教的“使命预言”,将每个人的日常行动转变为具有特定惯习(即条理化和纪律化)的生活风格。因此,韦伯指出,这一伦理理性化的特征就在于,“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眼前的、此岸的,对于那些寻求救赎的人来说恰恰是最基本的,这是他们的惯习”。[37]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中,以塑造人的惯习为核心的伦理理性化,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具有重要意义,它通过“天职”的观念,使日常生活中的现世义务成为塑造个性的关键,从而为社会秩序的程序技术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洛维特指出,推动韦伯思想发展的原动力就是“在当代世界中人的命运”。而这种人的命运,就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作为“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上。[38] 但在韦伯的笔下,这种命运绝不是人的自由的反面[39],与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盛行的异化命题相反,在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中,理性化的命运与现代人的自由相反相成,而二者关联的环节就是一种体现在新教徒的“天职”中的个性形塑的技术。
人们往往容易忽略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尾处对歌德的个性观念的讨论。[40] 韦伯指出,歌德在其巅峰时期创作的《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和《浮士德》的第二部中告诉我们,现代的个性不再是古典主义理想中那种追求完美的个性。不过,它也不是浪漫主义式的总体个性。现代人的个性,不是脱离日常生活,到艺术或某种神秘体验中去寻找个性形塑的空间,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探索一个人的个性。 [41] “天职”就是这种个性的鲜明表现。因此,在韦伯的眼中,现代人的个性并非力图到专门化的工作之外,去寻求那种看不见的总体,而是放弃了“普遍个性” (universal personality)的渴望[42],面对一个“破碎的世界”(world in fragments)和破碎的灵魂(fragmentation of soul),现代人个性的“总体”就体现在他的工作中,在他的工作中寄托了自由的可能性。这样,韦伯的社会理论就摆脱了现代社会理论中常见的怀旧或乌托邦式的主题[43],通过专门化的个性塑造与伦理理性化,将自由问题与理性化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这里,腾布鲁克强调的“世界的除魔”这一命题的重要意义就展现出来了。正是“除魔的世界”要求人们实现一种“英雄主义的伦理”。这种伦理对每个人所提出的根本要求,只有当这个人在其生存非同寻常的“杰出”状态中,才有可能实现。[44] 但正如韦伯在分析“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时所指出的,面对这种“杰出”状态以及超验秩序与日常现实之间的紧张,不是逃避这种紧张或者借助符号手段来协调二者的紧张,而是利用这种紧张,作为人的伦理理性化的动力,象新教徒当年的选择一样,从人的天职入手,完成这一天职的“日常要求”[45]。用韦伯的话说,在现代社会中,人要获得个性与自由,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都找到操持他的生命之弦的守护神(daemon)”。[46]
(3)理性化与自由的悖论:从支配社会学透视韦伯的困境
韦伯有关“新教伦理”的命题,实际上是在社会理性化与自由的伦理理性化之间找到了一个重要衔接点,即纪律。纪律一方面构成了社会理性化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个人对自身生活进行全面的组织与安排的技术,形塑个性的技术,最终也是新教徒获得自由的技术。因此,纪律既是“除魔的世界” 中的历史命运,又是“禁欲者”的守护神手中操持的个人的命运。
不过,理性化的难题就在于如何能够始终维持,甚至发展“除魔的世界”的历史命运与“禁欲者”个人命运之间的张力。是否理性化不可逆转的进程意味着,巨大的历史命运终究会吞噬每个人的个人命运?这种危险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将“除魔的世界”的历史命运看作系统的工具理性扩张,将个人的纪律实践等同为人的自我异化。这些理论上的严重问题,也许不过是现实困境的征兆。事实上,正是因为无法维持世界的除魔,才会导致对“怨恨或一种伪神义论的要求”[47],听命于各种虚幻观念或神话的摆布;而同时,也正是因为缺乏现代的禁欲式的自我技术,我们才最终远离了新教徒的紧张与纪律,而沦为一种功利主义逻辑下的“没有精神的专家”。
由此看来,韦伯的社会理论,既不同于那些将社会秩序的理性化等同于与人的自由无关的程序技术的功利主义或实证主义,也与强调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相去甚远,事实上,这种研究传统同样将社会秩序的理性化看作是对个人自由间接的威胁甚至直接的剥夺,而背后人的观念是一种全面的,总体化的完美个性[48],以及由这样的人自愿构成的共识的共同体。
不过,伴随韦伯自己研究的深入,上述有关理性化与自由的论述却面临着严峻的困境。早在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韦伯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入世禁欲主义的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亲合力”(Wahlverwandschaft)并不会永久存在。因为“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49] 作为理性社会秩序核心的程序技术既无需伦理理性化的推动力,也不再“试图寻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因此,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从清教徒肩上轻飘飘的斗篷,变成了一只铁的牢笼。在几年后,韦伯又进一步指出,无论美国资本主义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还是德国所谓的“福利供给”,甚至俄国的工厂制度,处处都体现出一种倾向:“迈向新的奴役的铁笼”。[50] 脱离了伦理理性化的“支持”和“充实”的社会理性化,是否最终会演变为一种非人的异己力量?“就仿佛是身处一列不断加速的列车,不知道扳道工是否正确地设置好了下一个转向”。[51]
如果考虑到韦伯的比较历史分析实际上是一种“现在史”(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即通过历史研究来理解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52] 那么韦伯对现在的诊断就并非无关紧要的政治感慨了。正如蒙森一再强调的,现实的政治关注是韦伯的另一副面孔,对他的学术研究始终具有强大的影响。[53] 身处在德国古典自由主义文化衰微的时代,韦伯一方面对此深感痛惜,但另一方面他也一再要求政治家和学者正视现实,面对所谓“科层制的时代”,必须重新探讨自由的可能性。[54] 因为他清醒认识到,“科层制与安排生活的现代、理性方式的其他历史载体的区别就在于,科层制更加难以逃脱。”[55]
韦伯对政治现实的这种关注,在1915年前后,伴随着他思想的进一步“突破”,将理性化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尖锐地带入了社会理论问题域的核心。
尽管蒙森和施路赫特存在诸多分歧,但两个人都承认在1914至1915年左右,韦伯的社会理论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56] 一方面,韦伯社会分析的研究策略(即通常所谓“方法论”)有所调整。而另一方面,伴随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深入,理论的方法论观念有所变化韦伯整个社会理论的视野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韦伯不仅关注通过伦理理性化,宗教的世界图景如何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理性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还进一步考虑各种其他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因素对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进而,这些领域自身的理性化进程,也成为韦伯关注的对象。[57] 在韦伯面对的这些新问题中,支配社会学的问题以系统的方式出现在韦伯的社会理论之中。可以说,在1915年以后,韦伯就同时从宗教社会学和支配社会学两个角度思考理性化的问题。
但随着韦伯通过支配社会学的研究将他一直关注的政治问题纳入社会理论的问题域中,新教教派的伦理理性化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理性化之间的基本思路却面临了与韦伯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悲观预言”的诊断类似的困境。
可以说,韦伯思考支配社会学的问题与他以往思考宗教社会学的思路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他关心的核心问题仍是理性化与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在不同的条件下,特别是高度科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自由如何是可能的”。[58] 但对于韦伯的支配社会学分析来说,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分析中仍有两点关键的不同。首先,韦伯对支配问题的探讨主要不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的 [59],而是特别关注了对科层制的程序技术特点的分析,政治理性化与其他社会秩序的理性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理性化),程序技术在韦伯以往的分析中往往是作为背景来处理的,而现在作为社会秩序理性化的核心的各种程序技术,成为韦伯直接关注的焦点。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韦伯着手分析不同的社会秩序中的理性化过程,韦伯思想中的“诸神之争”的主题开始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 1915年以后,韦伯多次提到穆勒(John Stuart Mill)晚年的观点,即在经验世界中,人们只可能拥有多神论的经验。韦伯就此指出,“事实上,任何生活在现世(基督教意义上的世界)的人都只能感到自己是在面对不同的价值之间的斗争,其中的每一种价值,单独看,似乎都在他身上强加一种义务。他必须选择他想要哪一种神,想为哪一种神服务,或者何时想为其中一个神服务,而何时又为另一个神服务。但在任何时候,他都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场发生在此世中的诸神之争。而首先,他总会发现,他已远离了基督教的上帝,或至少是山上宝训中宣扬的那个上帝。”[60] 因为,在韦伯看来,实际上,“诸神之争”是“除魔的世界”中的题中之义,而对于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的现代人来说,又是价值自由的前提和结果。
但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韦伯的“诸神之争”和价值自由与新教伦理命题中在“理性化”和“自由”之间建立的反题结构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61] 韦伯的“诸神之争”,意味着在现代政治秩序中,理性化意味着要搁置与超验的“神”的联系。因为,韦伯敏锐地意识到,在现实政治中,任何绝对的伦理价值出发的政策,都无视“后果伦理”(ethics of consequentialism),沦为一种泛道德主义[62],在一战期间撰写的一封公开信中,韦伯就尖锐地批评了从福音观念出发的和平主义思潮。在韦伯看来,这些“乌托邦”观念,与当年他在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讲中就开始倡导的“现实主义”取向完全相悖。在韦伯看来,无论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还是“乌托邦”的自由主义,都难免沉湎于一些陈旧或者空洞的观念,无视我们面对的历史命运,我们生存的现实与条件。[63] 这也正是韦伯晚年关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关系的一个原因。[64]
但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问题来说,绝对不容忽视的一点是,韦伯对现代政治的这一看法却丧失了“新教伦理论题”中超验的彼岸世界与日常生活的此岸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韦伯对支配社会学的分析也就丧失了在宗教社会学分析中借助这一紧张关系建立的伦理理性化的推动力。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宗教社会学的分析中,伦理理性化不仅构成了社会秩序理性化在发生学意义上的“亲合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正是伦理理性化与社会秩序理性化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为人的自由提供了可能空间与现实技术。
在政治支配的领域中,个人不再能够诉诸一种超验的、彼岸色彩的“神”,来抗衡现世科层化中的例行化力量,因为,韦伯在分析支配社会学的例行化时,在探讨科层制与法律制度中的惯习的形塑时,没法再象“新教伦理命题”中那样,将个性和自由通过生活风格的伦理理性化,与政治秩序的程序技术方面的理性化联系起来,而是“在政治理性中彻底消灭一切伦理的东西”。[65]
这一点特别体现在现代社会的政党-议会政治中。在政党经营的条件下,政治科层化这种社会理性化的伦理理性化动力丧失了。在高度组织化的政党中,职业人士并非象新教企业家一样,“为政治而生”(live for politics),而是“靠政治谋生”(live from politics)。[66] 这正吻合韦伯当年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做的区别,“清教徒想在一项天职中工作;而我们工作则是出于被迫”。[67] 因此,在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发现的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之间的关联——天职——在现代社会的政治根本就没有位置,理性与自由之间的二律背反的关联实际上也就丧失了。面对这一困境,韦伯的一个重要尝试,就是提出了克里斯玛的观念,试图从中找到对抗徒具例行化,丧失自由色彩的理性化的出路。
在1915年前,韦伯理论中的克里斯玛概念主要指一种传统类型的权威,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权威形式。不过,1914-1915年前后,韦伯理论中的“克里斯玛”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以一种彼岸形式的个人理想价值为取向的创造性行动的源泉。[68] 围绕政治支配与权威的建立,社会秩序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个性与自由)的关系这一问题,就进一步具体化为例行化与克里斯玛之间永不终止的斗争。因此,宗教社会学中,通过纪律实现的理性化与自由之间的张力关系,变成了政治社会学中“纪律与个人克里斯玛之间各种各样的冲突”[69],这一主题不仅贯穿了韦伯的政治著作,也隐含在庞杂的《经济与社会》的字里行间[70],蒙森精当地概括为,“韦伯政治思想中的二律背反结构(antinomical structure)”。[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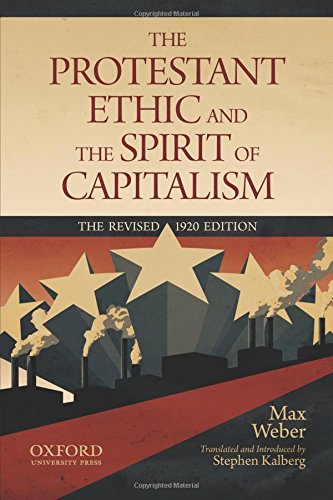 克里斯玛,作为历史命运中的“革命性力量”,之所以能够为政治秩序带入了动态力量,正是因为它具有伦理理性化方面的意涵。腾布鲁克认为,韦伯的克里斯玛学说深受德国学者迈尔的影响。迈尔指出,“所有主要的和革命性的运动…都来自为宗教观念所占据的那些个人的个性…在这些形象中,他们不可能再听命于外在的权威…因此,它〔指独特的信念,引者按〕的出现就总是革命性的,并导致变革…在任何时候,它都是通过与对手的艰苦斗争来确立自身的…”。[72] 信念与斗争,使这些人的行动打上了他们的个性的烙印,并正是借助他们的这一个性,为历史带入了革命性的力量,对抗作为例行化的习惯或传统。
克里斯玛,作为历史命运中的“革命性力量”,之所以能够为政治秩序带入了动态力量,正是因为它具有伦理理性化方面的意涵。腾布鲁克认为,韦伯的克里斯玛学说深受德国学者迈尔的影响。迈尔指出,“所有主要的和革命性的运动…都来自为宗教观念所占据的那些个人的个性…在这些形象中,他们不可能再听命于外在的权威…因此,它〔指独特的信念,引者按〕的出现就总是革命性的,并导致变革…在任何时候,它都是通过与对手的艰苦斗争来确立自身的…”。[72] 信念与斗争,使这些人的行动打上了他们的个性的烙印,并正是借助他们的这一个性,为历史带入了革命性的力量,对抗作为例行化的习惯或传统。
从这一角度看,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分析的新教教派的“英雄伦理”和“使命预言”,实际上同样具有支配社会学的意涵。不过,在支配社会学中,象在宗教社会学中一样,这一伦理力量同样难以持久。韦伯清醒地意识到,克里斯玛的革命性力量,最终也无法摆脱例行化的命运。而一旦克里斯玛例行化,政治支配问题就面临了艰巨的困境,这与脱离了与禁欲新教关联的资本主义的状况颇为类似。[73] 在两个领域中,都面临着“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灵”的危险未来。但从韦伯的支配社会学来看,正是克里斯玛与例行化之间的这种二律背反的结构,构成了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使韦伯的支配社会学中的理性化,摆脱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发生学的限制范围,具有了普遍历史的意涵。这样看来,韦伯“政治思想中的二律背反结构”,比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发现的理性主义的反题结构,就有了非常重要的进展。不过,这样的进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就是克里斯玛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在政治秩序的理性化问题中,社会理性化的程序技术,不再与个人的伦理理性化发生关联,借助后者的“亲合力”,推动理性化的发展,遏制理性化的空洞化的趋势。相反,人们必须在僵硬的例行化与领袖色彩的克里斯玛中进行选择。面对来自这两个极端的挤压,韦伯究竟可以在哪里找到“自由的活动空间”呢?
在韦伯笔下,现代社会政治秩序中的克里斯玛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革命性的力量。另一种是新的非教条性的“大众动员式的领袖民主” (plebiscitarian leader democracy)。[74] 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韦伯认为,革命性政治背后的“信念伦理”观念隐含着某种不可忽视的危险,因此,韦伯非常关注这种“领袖民主”的可能性。在大众动员的领袖身上,韦伯看到了挣脱例行化的“铁笼”的可能性。因此,在晚年的韦伯眼中,理性化与自由的命运,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科层制的机器与有领袖的民主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讲演中所指出的,德国“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做以选择:或者是借助科层‘机器’的领袖民主制,或者是无领袖的民主制,即没有天职感的职业政治家的支配,这些职业政治家恰恰缺乏真正造就一个领袖的内在的克里斯玛的素质。”[75] 不过,身为自由派的韦伯,同样预感到了领袖民主的潜在危险,而且在俾斯麦留给德国的政治遗产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危险的现实反映。[76]
就俾斯麦本人而言,无疑是韦伯心目中的克里斯玛的典型形象。这位“铁血宰相”不仅领导了以普鲁士为主导的德国统一进程,而且一手塑造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传统。但韦伯却对这种由克里斯玛色彩的伟人进行的统治带来的历史效果深表怀疑。韦伯指出,这种“凯撒制”,由一个天才来进行统治,给德国政治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对一个政治家的个性的毫无节制的景仰,竟然使一个骄傲的民族如此毫无保留地牺牲了它自己的客观信念”。[77] 这位伟大政治家的传奇,实际上建立在习惯听命他的决定的国民的基础上,从而使洪堡和康德的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政治意志。
“凯撒制”之所以导致了这样的问题,就在于俾斯麦拒绝接受甚至容忍在他之外存在任何独立的权力,这意味着,在这样的体制,除了领袖自己以外,不允许存在任何根据自身责任来行动的人。[78] 实际上,这正是韦伯一直痛惜的德国市民阶级个性的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曾一度为自由而抗争的市民阶级,在俾斯麦的伟大个性和政治权谋面前五体投地,不再进行独立的政治思考,争取自身的权利。也许,这才真正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衰微。而在韦伯看来,德国政治的不成熟正在于缺乏担纲政治领导权的阶级,这是整个德国为俾斯麦个人的个性付出的代价。结果是德国政治摇摆于市民阶层的冷漠、政治市侩和工人阶级的“怨恨”。[79] 而俾斯麦的这种克里斯玛的统治,正是结合了大众动员的所谓“民主”,以“普遍公民权”为幌子,实质却意在借助习惯于被动服从的大众,通过“普选”[80] 来获得保守势力的支持。[81]
因此,从韦伯对“凯撒制”的讨论[82],我们可以发现,当宗教大师的英雄伦理,变为政治领域中具有克里斯玛的领袖,那么原来“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最伟大和高贵的性格”[83] 的伦理理性化力量,却很可能只会导致牺牲每个人(或至少市民阶层)对自己个性的形塑,来成就一个人(领袖)的个性崇拜。自由的动力,却蜕变成了自由的敌人。
因此,在领袖民主中,不仅找不到自由的活动空间,似乎理性化的动力,也会流失在领袖“半是凯撒制,半是家长制”的政治统治形式中。在这种形式下的民族,完全不知道任何真正的政治教育,也完全不具有任何政治意志,实际上,没有任何政治传统,只知道以被动的宿命态度听从凯撒式的权威而已,它的公民根本就没有什么性格可言。[84] 而当一个民族甘于象羊群一样被统治,就不可能有自由。[85]
那么还有其它选择吗?正是这里我们触及到了韦伯政治思想中饱受争议的部分,就是韦伯的所谓“民族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思想倾向。蒙森和亨尼斯将这些倾向看作是韦伯为自由留下空间的最后尝试。用蒙森的话说,就是“有必要在社会生活的所有层次上都保持最大限度的动态力量,或借助各种手段来促进这种力量”。[86] 洛维特简明地将之概括为,“通过斗争获得自由”。也就是说,面对例行化、纪律化和条理化无所不在的程序力量,用一种充满激情的否定性力量,来冲破特定的牢笼,这就是“自由的活动空间”的意涵。[87]
但无论是亨尼斯和蒙森的尼采式解读,还是洛维特的另一种“总体性”似乎仍然不能解决韦伯的困境,因为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实力政治 “(Machtpolitik)[88]与“凯撒制”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没什么两样,因为在这种所谓通过斗争获得的自由中,并没有为每一个“自助”的人的性格留下任何理论位置,某种政治上的“辉煌”并不能掩盖背后的空虚,和俾斯麦当年的情况一样,这仍然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虚荣政治,而不是荣誉政治;是伪神义论,而算不上真正的信念伦理。
因为整个支配社会学中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在政治领域中无法找到与宗教社会学中的“社会秩序理性化和个性塑造”的反题结构相应的张力。无论是所谓的“革命”,克里斯玛,还是以民族或国家面目出现的政治斗争,都无法真正成为例行化的对抗力量,而不如说是和后者构成了共谋的关系,谋夺自由的残存空间。因此,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在理性化(科层化、纪律化、条理化与理智化)的条件下,韦伯的自由方案就面对了两种可能的紧迫危险,一种危险是,如果诉诸克里斯玛式的领袖,那么最终的结果并非普通公民的自由,也谈不上他们的责任与性格,而不过是个别领袖专擅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恣意”。另一种危险是在政治中强调尼采式的斗争的意义,而这样做的结果则助长了民族主义甚至国家主义的倾向,最终“集体的斗争”与其说是保留了个人自由的动力,不如说是以集体的名义压制了个人自由的空间,最终以“敌人”或“战争”为借口彻底剥夺了自由的可能性。韦伯去世后德国的历史也许正是面对现实的政治处境追求“自由”的这两种危险的写照。
所以,韦伯的困境实质上在于在韦伯对支配社会学的分析中,无法在现代社会中找到一套继续维持新教徒的生存张力的伦理理性化的精神张力,结果使理性化的历史命运,不再是个人命运的另一面,而变成了个人自由与命运的历史对立面。在宗教社会学的比较历史分析中,“除魔的世界”与个人的自由的相反相成。但在他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在“除魔的世界”中似乎没有任何个人自由的可能性,而要创造个人自由的空间,似乎就需要将世界重新着魔,这个“诸神之争”的世界中反而没有禁欲者的守护神的任何位置,禁欲者的“守护神”不得不要附身在各种各样的“伪神”之上。
蒙森曾经称韦伯是一个“身陷绝望的自由派”(liberal in despair)[89],不过在他的笔下,“绝望”不过体现了韦伯的悲观主义观念罢了。蒙森没有看到,绝望正是韦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位现代性的社会学家的根本立场。在社会学家曾经写下的一段最完美的文字中,韦伯告诉我们,正是“越来越具有毁灭力量的无意义性”,带来了世界的除魔,使我们超出了平淡的自然主义和有机循环,而且恰恰是这种“世界绝对的不完美”,最终使禁欲者在实践中尝试最彻底的伦理理性化。[90] 唯有绝望,才能正视我们面临的历史命运,担负它,将它变成个人的命运。一句话,唯有绝望,才开始知道如何挣扎。因此,我们需要探问,面对经典自由主义的危机,韦伯的社会理论中除了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之外,是否还包含了潜在的“出路”。是否有可能从韦伯社会理论的基本思想出发,探寻一种自由的可能性,在政治领域中,既无需将自由看作一种天赋的权利,占有的财产,或者自然的秩序,而是一种不断努力的自由行为,通过斗争赢得的自由空间,一种自由的生活风格,而同时又不会流于德国历史揭示的两种现实危险?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必须做我们的工作,趁着白日’。现在,必须为那些属于大众,那些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的个人们,赢得‘不可让渡’的自由与个性的空间。必须在现在,也就是在下几代的时间内,趁经济‘革命’和思想‘革命’,深受鄙视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同样受到鄙视的‘主体观念’(subjectivism)尚处巅峰的时候。因为正是它们,并只有它们,才使个人能够获得自由与个性的空间。一旦世界在经济上‘充分’发展,在理智上‘得以满足’,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永远不再可能赢得这些空间了。至少面对不可洞察的人类未来的迷雾,我们单薄的双眼能够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91]
也许,真正能够塑造伟大政治传统的,既非运用辉煌的政治口号来进行大众动员的伟人,亦非民粹主义者心目中的那些被动员的“沉默的大多数” [92],而是“那些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真正能够在政治中找到“自由与个性的空间”的孤独的人,以及在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超越日常的惯习”(ein ausseralltaglicher Habitus)[93],而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要探讨“英国法”问题的原因。
二、“英国法问题”:法治国的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
(1)韦伯眼中的英国法
帕森斯认为,“韦伯的实质社会学部分的核心,既非他对经济、政治问题的处理,亦非他的宗教社会学,而是他的法律社会学”。[94] 但显然有许多学者并不同意帕森斯的论述。在本迪克斯笔下,政治社会学在韦伯的实质社会学中的地位更重要,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属于政治社会学的一部分。 [95] 撰写专著研究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的克隆曼也指出,“在绝大多数时候,韦伯对法律问题的讨论从属于他关注的其它问题,例如,他对政治权威和经济行动的性质的分析”。[96]
不过仔细来看,双方的分歧并不象表面看上去那样大。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韦伯从1910年到1914年左右的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支配社会学在韦伯整个社会理论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法律社会学的论述恰恰是整个支配社会学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的部分。从韦伯的理想类型的角度来看,法理权威在韦伯的支配社会学的概念体系中占有枢纽地位。《经济与社会》中阐述的整个概念体系也可以看出是以支配社会学,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以法理权威及其制度化的核心问题组织起来的。例如,有关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组织活动的论述,就是从法律角度来加以定义的。[97] 特别是《经济与社会》较晚写峻的第一部分,这一点尤其突出。从这一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在分析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时,将它放在整个支配社会学理论中来理解,这一点恰恰为许多分析韦伯法律社会学的学者所忽视;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样要认识到,韦伯法律社会学在支配社会学中占有的特殊地位,使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可以说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分析是理解韦伯的支配社会学的关键环节。[98]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才使韦伯法律社会学中的所谓“英国法”问题,在整个韦伯社会理论中成为一个“要害”。韦伯处理“英国法”问题时所面临的困境,突出地体现了韦伯整个思想的关键问题:在“诸神之争”的除魔世界中,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理性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早在直接讨论法律社会学之前,韦伯的一些论述就涉及到所谓的“英国法问题”,或法律社会学界更常说的“英国问题”(England problem)。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为了证明理性主义的发展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中并不是并行的,韦伯就以法律理性化与经济理性化之间的关系为例指出:
“譬如,假如我们将私法的理性化看成是对法律内容的逻辑简化和重新安排,那么这种理性化在古代后期的罗马法中就已经达到了迄今已知的最高程度。但是这种私法的理性化在一些经济理性化达到相当高程度的国家中却仍然十分落后。在英国,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在那里,罗马法的复兴为各种法律公会的强大力量所挫败;与此相反,在南欧的天主教地区,罗马法的复兴一直保持着支配地位。”[99]
而在《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社会学”部分,韦伯屡次谈及了英国法在理性化程度不仅难以与查士丁尼时代的晚期罗马法相比,而且难以与欧陆通过罗马法的继受逐渐发展起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但问题在于,英国法较低的理性化程度似乎并未妨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助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不过,尽管总的基调如此,但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韦伯有关英国法的理性化程度问题的具体论述,包含了相当复杂,甚至多少有些模棱两可的论述。
当然,韦伯首先也承认,在某些方面,英国的普通法也具有相当高程度的理性化。这一方面体现在程序方面,英国法具有相当高的理性程度,尤其是许多法律技术,如令状。[100] 韦伯指出,英国法早在中世纪就在技术上高度发展。[101] 因此韦伯认为英国的普通法具有严格的形式主义特征。另一方面,英国法在保障契约自由方面,例如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合同法方面,韦伯认为英国法具有可以与罗马法、印度法相提并论的理性化程度,有助于保护贸易,在某些方面,甚至只有古代罗马共和国可以与之相比。[102]
但是,在韦伯眼中,英国法更多是在许多地方表现出“非理性”的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英国法尽管具有严格的形式主义,但却缺乏以晚期罗马法为代表的逻辑意义上的形式理性。英国的判例法,既没有在法律推理过程中严格遵守三段论式的演绎理性,也没能(或不愿)实现“将所有可以设想到的事实情境都在逻辑上纳入无缺陷的规则系统中”的系统化目标,因此,英国法并没有实现“逻辑升华”意义上的理性化,只不过仍采用一种罗列式的关联方法,一种法律的“决疑术”(legal casuistry)[103],而且这种基于类推的判例原则,根本也不可能产生法律的理性系统,也就不可能产生法律的理性化。[104] 而另一方面,英国法中采用的许多技术(如陪审团),很容易导致在判决过程中不是由普适性的规范(general norms)来统一决定,而是受到特定案例中的各种具体因素(如以伦理、情感或政治为基础的价值评判)的影响,而这正是韦伯眼中“实质非理性”的法律的主要特征。[105]
所以,英国法在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都具有强烈的非理性色彩。首先,在韦伯看来,法律的形式主义有两种迥异的形式,一种是“拘泥于事实的外在特征……或是履行某种具有固定意涵的象征行为”,这是一种最严格类型的法律形式主义。而另一种则是“运用意义的逻辑分析方法揭示出事实中所有与法律有关的特征,并因此能够以一种高度抽象的规则的形式阐述和应有确定的法律概念”。在韦伯看来,正是后者的这种“逻辑理性”标志外在因素不再在法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相反,英国法却依旧保留了大量的具体形式主义对事实的外在特征(而非明确的一般特征)的强调,所以,英国的普通法只是一种“外在”的、严格的形式主义,但却并未形成真正的“逻辑的形式理性”,而后者,在韦伯眼中,才是法律在形式理性化方面的真正标准。[106] 所以,英国普通法尽管具有相对比较发达的“形式”技术,但这些技术却没有被“逻辑理性”整合为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因此,发达的“形式”技术不仅没有使英国法具有较高的形式理性,相反,这种外在的形式主义,倒是英国法较低形式理性的体现。
从历史的角度看,韦伯还进一步指出,英国普通法的这种严格的形式主义,表明英国普通法残留了大量的巫术因素,从而才带有浓厚的仪式主义的色彩。[107] 例如,英国运用陪审团进行判决,有相当强的克里斯玛色彩[108],与古代法中的神谕(oracle)相对应,尽管判决中的判例本身相对来说是理性的,但在韦伯看来,判例法的诸多法律技术却因为缺乏“系统化”的逻辑升华过程,因为是非理性的,是巫术色彩的原始法律的现代遗留物。而之所以英国法残存了大量巫术色彩的技术,主要因为英国法中保留了大量中世纪法律的痕迹。而在韦伯眼中,西方中世纪法律的思想有许多方面是“落后”的。[109]
其次,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英国普通法较低的理性化程度,不仅体现在形式理性化方面,同样也体现在实质理性化方面。[110] 因为,普通法中运用的各种法律技术,固然没有被任何法律的“逻辑形式理性”整合起来,也同样没有被任何伦理命令、功利标准或者政治准则整合为一套无缺陷的体系。因此,英国普通法中充斥着“卡迪司法”(Khadi-justice)的痕迹。[111] 由此可见,普通法在“实质理性”上也很“落后”。[112]
但是悖谬的是,尽管英国法无论在形式方面,还是在实质方面,都未能实现较高程度的理性化,但却一方面,英国法似乎并没有阻碍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13] 而另一方面,从政治的角度看,普通法国家的民主政治较为稳定,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稳定民族政治的国家有许多是那些采纳普通法系的国家。[114] 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韦伯的社会理论,乃至整个法律社会学中所谓的“英国问题”。
不过,在试图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一个必要的迂回,来进一步澄清一下韦伯笔下法律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到底意味着什么,从而更深入地探究韦伯社会理论中所谓“英国法问题”的实质。
(2)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
在韦伯的社会学概念体系中,所谓目标理性[115] 与价值理性一直被视为是最重要的对立范畴,这对范畴也对后来整个社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而相比来说,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这对范畴的影响就要小得多。许多讨论韦伯“理性”概念的学者往往对此避而不谈[116];即使谈及这对范畴,也经常将形式理性等同于目标理性,将实质理性等同于价值理性。 [117] 但如果要理解韦伯复杂的“理性”概念[118],就必须充分重视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分的意义。不过要理解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这对范畴,首先要理解它们与目标理性/价值理性这两对范畴在韦伯的问题域中的不同位置。
在韦伯的著作中,直至1913年才出现“目标理性”这一用法,而“价值理性”概念出现得更晚,几乎是在1920年才为韦伯所正式采用。 [119] 不过,学者们将这对几乎在韦伯临终前才成形的范畴视为韦伯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并没有错,因为从回溯的角度看,这对反题概念可以说一直是韦伯社会理论的核心环节。但关键在于,这对范畴究竟是针对什么问题出现的呢?缪勒敏锐地指出,不能将韦伯的这对概念等同于腾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这对范畴,因为在韦伯的理性类型学中,“情感”和“传统”理性属于韦伯所谓的“共同体性”(Vergemeinschaftung)的社会行动,而目标理性和价值理性则同属 “社会性”(Vergesellschftung)的社会行动。[120] 与“情感”理性和“传统”理性不同,目标理性与价值理性都是分化社会中的理性行动,它们都涉及社会行动者对实践行动进行有意识的、审慎的“组织”过程,也就是说,这两种理性类型都与分化社会条件下的伦理理性化[121] 有密切的关系。[122] 从这个角度看,目标理性和价值理性确实是韦伯的理性类型学的核心,因为在《经济与社会》中,正是借助这两个概念,韦伯从系统化的概念体系出发,重新思考了他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来一直关心的西方理性化的问题。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之间的关联与张力直接涉及了韦伯始终关注的伦理理性化与社会秩序的理性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对范畴出发,我们可以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就是,借助新教徒的伦理理性化过程中,新教伦理的“价值理性”与作为理性资本主义特征的“客观的经营活动”的“目标理性”的理性化之间建立了“亲合力”,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推动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教徒的伦理理性化,既是“价值理性”的,也是“目标理性”的;而在《经济与社会》和晚期的政治作品中,无论是对支配社会学的分析,还是对经济生产的技术效率与实质正义或社会目标之间的关系,韦伯关注的核心问题却是这对范畴的另一个侧面,即在价值多元的格局中,价值理性与目标理性之间的冲突,不同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以及目标理性在这种价值理性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在这里,韦伯有关法律社会学的论述的意义凸现了出来:是否有可能找到一种理性形式,既超然于政治领域中价值理性的“诸神之争”,也同样超然于国家科层制与私人企业的科层制两种目标理性之间的冲突[123]?无疑,韦伯有关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对立范畴就和这一努力有关。
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中,所谓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对立既非是事实与价值的对立[124],也与《经济与社会》第一部分中讨论经济行动中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125] 不同,更准确地说,是逻辑系统化与价值系统化的对立。而在这两种系统化对立的背后,隐藏了法律形式化与伦理理性化之间复杂的历史关联与理论纠葛。
韦伯主要从神圣法(sacred law)理性化的角度来考察法律的实质理性化问题。[126] 韦伯指出,神圣法理性化的条件,首先就是相应宗教的伦理原则要摆脱巫术性质或仪式主义性质的形式主义。[127] 在这方面,基督教的教会法较之其它文化中的神圣法,占据相对特殊的位置,因为它在许多方面都要远为理性,特别是在形式方面十分发达。[128] 除了斯多亚学派的“自然法”学说、罗马法的法律技术和教会理性的科层等级制之外,在教会法的理性化过程中,韦伯没有直接提到的基督教自身的理性图景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29] 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中论述的“教皇革命”,尽管不免有些偏颇和夸大,但仍然有力地证明了:在精神界与世俗界之间更强有力的张力关系下推动伦理理性化的努力,在这一背景下理性的教会法对抗各种地方习惯法的斗争,“产生了西方的法律传统”。[130] 宗教改革之后,神圣法对于推动世俗法的理性化,发挥了更为明显的作用。尽管早期路德宗对人创造作为永久法的人法的权力这一点抱有怀疑态度[131],但在所谓“第二次宗教改革运动”中,伴随着加尔文教派等新教教派的信条化(confessionalization)[132],新教教派日益强调按照更加理性的世界秩序图景来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他们想要的不是自由和宽容,而是独立与支配”。在这一观念下,对法律的理性化首当其冲。这一点,突出体现新教教派,特别是加尔文宗和清教诸派的反抗理论,对后世宪法理论与“高级法”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33] 因此,法律的实质理性化,在很大程度上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的命题有很大的相似性,即除魔的世界秩序图景,是如何通过伦理理性化的动力学,来建构一套发达的形式技术。[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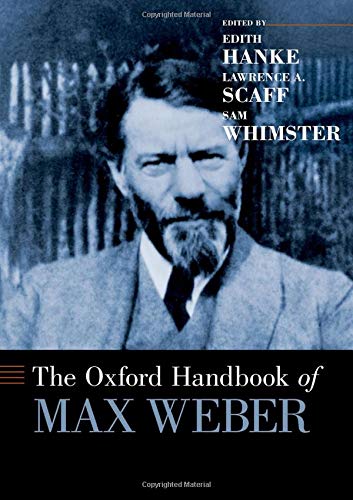 不过,韦伯更关心的是形式理性本身的发展。受德国的罗马法编纂学派(Pandectist)的法理学及此后的概念法学(Begriffsjurisprudenz)的影响,韦伯强调法律是一种由系统性的规则支配的无缺陷的体系,将这一点视为真正的形式理性的标准。 [135] 从这种概念法学的视角来看,法律“正象自动贩卖机,从上面投入事实,在其中适用预先决定的所谓法律规定,然后从下面自动出来结论”。[136] 这一形式理性的“技术装置”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前提是法律能够与伦理等实质理性分离,构成“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法律秩序。换句话说,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与韦伯在支配社会学中采取的一般立场是一致的,就是不得不割断伦理理性化与社会秩序理性化之间的直接关联,从而保证价值自由。
不过,韦伯更关心的是形式理性本身的发展。受德国的罗马法编纂学派(Pandectist)的法理学及此后的概念法学(Begriffsjurisprudenz)的影响,韦伯强调法律是一种由系统性的规则支配的无缺陷的体系,将这一点视为真正的形式理性的标准。 [135] 从这种概念法学的视角来看,法律“正象自动贩卖机,从上面投入事实,在其中适用预先决定的所谓法律规定,然后从下面自动出来结论”。[136] 这一形式理性的“技术装置”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前提是法律能够与伦理等实质理性分离,构成“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法律秩序。换句话说,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与韦伯在支配社会学中采取的一般立场是一致的,就是不得不割断伦理理性化与社会秩序理性化之间的直接关联,从而保证价值自由。
不过,在韦伯笔下,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要比这种纯粹类型的构建复杂得多。因为,如果考虑自然法对实定法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实质理性化是形式理性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前提,而且即使实定法实现了相当高程度的形式理性化后,实质理性化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背影。在韦伯看来,作为形式理性法核心的抽象的法理制度结构,正是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自然法不仅是实定法的规范标准,更重要的是,自然法构成了实定法在发生学意义的动力。“在形式上,自然法学说强化了迈向逻辑上抽象的法律的趋势,特别增强了法律思维方式中逻辑的力量”。[137] 与许多非理性的公理相比,只有自然法公理中的法律理性主义,可以创造形式性质的规则。[138] 因此,作为“价值理性合法性的最纯粹类型”[139] 的自然法,也就成了具有最高形式理性的实定法的前提。[140] 韦伯的这一观点,对于理解他的整个社会理论的重要意义,我们不久就会看到。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中,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之分,实质上是解决价值理性与目标理性在现代社会相互冲突的一种方式。韦伯希望通过法律的形式理性化(这种形式理性化吸收了作为最高程度的价值理性的代表,自然法的规范标准),借助目标理性来为价值理性留出自由的空间。不过,在实定法的时代,形式理性法律与各种实质理性之间的冲突,仍然再现了我们在前面所探讨的韦伯整个社会理论的一个困境,即一旦脱离了发生学的问题,涉及到理性化的持续发展时,社会秩序理性化与自由的伦理理性化就分裂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而一个自由主义者不得不面对“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而就法律社会学而言,这一艰难的选择与德国“法治国”学说中的两种不同倾向密切相关。
(3)“法治国”的二难抉择
克隆曼敏锐地指出,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的核心是从法是如何被管理(administration)的这一问题入手的,正是这一问题将韦伯的思路与法学的思路区分开来。[141] 但究竟韦伯法律社会学分析的核心概念,如理性,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与法律的管理问题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却很少有学者论及。
当然,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韦伯的这些思想与德国的“法治国”(Rechtsstatt)的观念有关,不过仍然语焉不详,缺乏实质性的分析。[142] 借助下文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韦伯有关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的二元对立,与“法治国”学说发展的历史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而且正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发现,韦伯对法律理性化的分析是他的支配社会学理论的关键环节。[143]
“法治国”这个词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144] 从一开始,这一概念就具有非常明显的调和性。一方面出于扩充军备、增强国家实力的考虑,另一方面受到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西欧启蒙思想的影响,普鲁士等德意志地区试图摆脱治安国(Polizeisstaat)的传统。[145] 而“法治国”作为取代治安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则试图在强调新的自由的同时,保留原有的权威,特别是国家结构方面的传统主义特征。尽管随着市民阶层力量的上升和自由主义观念的日益广泛的影响,在18世纪30年代以后,“法治国”越来越成为自由派的思想武器,但它与英美经典自由主义的许多观念有很大距离。在绝大多数使用这一概念的学者那里,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并不是将其视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更不用说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形式,而不如说是“一种看待旧的国家的新方式”。借助这种观念,传统的政治权威的正当性,有意识地建立在“个体公民的自由”和“人民的自由”基础上。自由派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排除绝对主义国家中的恣意因素,因此,在他们看来,“法治国”就是“理性国”(state of reason)。[146]
这种“法治国”的理性色彩实际上是逐渐将以往二元对立的绝对国家与自然法学说揉合成一个整体,将国家的绝对目标看作是执行自然法。 [147] 从这一角度看,以往以自然法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与以治安国为工具的绝对主义之间的斗争,结果以绝对主义吸收了自然法,扬弃“治安国”,接受“法治国”而告终。现在,国家不再仅仅是自由的敌人,相反,却被视为是自由的庇护者和引路人。因为,在一个后进国家中,单靠孤立的个人,不仅不能对抗保守势力,来实现自由,还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只有国家出面,通过实定法的规则来履行自然法的原则,才有可能保障个人的自由。[148] 正如一位观念史学者指出的,“自然法丧失了作为独立的社会规范来源的地位。实定法被重新界定为永恒伦理原则的分支或盟友。理想化的国家成为一种道德代理人,一种教育制度,因此,不受外在约束限制的自由转为伦理上自我引导的个人的内在自由”。[149] 所以,德国“法治国”形式的“法治”,其特点就在于法律的性质与国家具有不可解脱的关系。[150] 或者更准确地说,强制的理性化,暴力由国家这一政治单位来垄断地运用,权力结构的非人身化,这些都是通过“法治国”来实现的。[151] 而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这种所谓“行政管理内部的宪政安排”(intra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alism)[152],体现了德国市民阶层“政治化”能力的薄弱,也导致了后来韦伯论及的市民阶层习惯服从,对民主总是充满恐惧的怯懦和“无力状态”。[153]
在这样的思想史-社会史的背景下,尽管“法治国”的学说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日益形式化,但这种带有强烈自由派色彩的形式主义学说并没有使国家彻底摆脱治安国时代的管理任务,而不过是通过形式化的法律来重新组织国家的管理任务。正如形式化取向的“法治国”理论的代表人物斯达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所言:
“国家要成为法治国,这一口号实际上表达了现代发展趋势。有必要借助法律手段来准确地界定,并牢固地确保国家公民自由的领域的同时,界定和确保国家作用的方向和界限;因此,国家只能直接实现那些属于法律范围内的事物。这就是法治国的观念,这种观念并不是说国家只能施行没有任何管理目标的法律秩序,甚至也不是仅仅保障个人的权利。它首先指的不是国家的目标和内容,而只是国家作用的方法和性质”。[154]
因此,“法治国”的目标就不仅仅是法,而是“通过客观法的形式,并且在这种形式中,尽可能地实现全民的德行与人性,并因而使他们获得幸福”。因为,“一个没有实定(positive)的道德追求的国家就象一次婚姻,一个家庭,徒具法律形式,但却没有爱情”。[155]
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边缘人物,德国法学家纽曼指出的,所谓“法治国”的根本原则就是管理的法理性。它既指国家的日常管理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的任何干预都可以还原为法律,并借助法律来完成。[156] 而国家的科层体制,也通过这种治理的法理化,获得了合法性,这就是所谓“通过法理性获得合法性”(legitimacy through legality)。[157] 通过法理性,科层体制将立法与行政管理的功能集于一身,得以逐渐瓦解传统等级国家中的法团力量,将所谓法团意义上的“德国式自由”转变为法治国下受监护的自由;而在全国范围内,就是作为国家科层体制对立面的议会的作用日趋下降。导致韦伯的政治作品中经常讨论的议会的“无权”状态。[158]
不过,“法治国”这种新的治理模式,作为将绝对主义时代的二元对立(治安国的管理任务与自然法的理性)揉合在一起的尝试,却将原有的绝对主义国家机器与自然法批评家之间的外在对立转化为一种内在的“政治二元论”(political dualism)。[159] 在外在的“政治二元论”中对立的双方,一方是完全控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却不遵循普适的法律理性的治安国,[160] 而另一方则是没有国家权力支撑,也未介入司法实践,只具教育意义的,超然的理性法律观念。[161] 而内在的“政治二元论”的新格局则是在同一理性支配下的二元对立。也就是说,一方面,“法治国”试图运用同一种理性将法律的“管理”与国家的治理联系起来,即一种普适法律(the general law)的原则,它强调国家借助形式理性的法律来组织它的一切活动,同时也保障公民的自由与安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公民的自由正是通过国家的这种法律理性支配下的管理活动保障的。但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的法律理性又与“国家的目标和内容”相分离。法律理性(普适的、形式的)的治理与国家目标的二元论,逐渐成为19世纪后半期德国政治和法律在实践与理论方面斗争的焦点。而韦伯有关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的区分正与“法治国”这种的政治二元论有关。“法治国”的“政治二元论”的实质是国家的形式实定法的法理性与背后的自然法的正义和合法性之间的紧张。尽管从“法治国”的逻辑来看,正是在韦伯关注的“形式性”的自然法原则的基础上,法律的形式理性才能够与国家支配的形式理性结合起来,构成了法理权威。这一结合既赋予法律以执行力量,而又赋予国家的支配以合法性,法理性与合法性在国家的形式实定法上获得了结合。但一旦国家试图运用法理权威来实现政治、伦理、功利等方面的实质目标,那么实定法中的自然法原则(rightness of the law),就不再仅仅是形式性,而变成了实质性的,而实质自然法的价值理性,就与形式实定法的目标理性之间构成了尖锐的冲突,这一冲突正是“法治国”观念中政治二元论的内在根源。不过在19世纪早期,“法治国”的倡导者主要主张仍是强调实定法及其法理权威的形式性,将法理权威与运用法理权威实现的实质目标严格地区分开来。
但自19世纪中叶开始,就有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形式法律的实质化来克服法治国的这种政治二元论,将“国家的目标与内容”与法律理性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些学者中,既有激进倾向的学者,也有保守倾向的学者。保守派的学者试图采用某种“有机国家”的方式将国家的绝对主义色彩的权力与个体公民不可侵犯的权利结合在一起。[162] 因为,个人自身的权力不足以保障他们的权利,必须运用国家的“总体权力”(total power)。[163] 这样,法治国的学说就将整合而不仅仅是保障个人的自由,作为一个运作政策,纳入到整个国家的管理之中。人身权利与公民权利都成为强大的、独立的政治权威的最终产品。在这种背景下,“自由即秩序,自由即权力”。[164] 而相对来说,激进派的学者则力图将政治正义与社会福利纳入法治国的法律制度中。尽管双方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针锋相对,但在基本思路上却没有什么差别,都希望将“法治国”的形式法律理性实质化,要求国家履行更多的文化与福利方面的功能。[165] 所谓“自由法学派”、强调“一般原则”和自由裁量权以取代形式理性化的倾向,所谓“社会法”以及“社会法治国”(Sozialrechtsstaat)的观念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并从20世纪初开始德国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66]
作为一位现实主义的自由派学者,韦伯对这种“当代法律发展的反形式主义倾向”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167] 他敏锐地察觉到“法治国”实质化倾向中蕴含的“总体性”(totality)危险,是对个人价值自由的潜在威胁。这一点,在他对斯塔姆勒的批评中,就可以看到。[168] 将法律的“应然”与“实然”混淆的结果,不仅是方法论方面犯了康德早已抨击过的错误,更在道德与政治上悖离了康德与洪堡的立场。[169] 韦伯预感到,当“法治国”通过实质化,转变为所谓“社会法治国”[170],就可能和社会主义企业一样,蕴含了铁笼的危险。因此,韦伯在许多场合表达了他对将国家实质化的思想与社会的趋势的担忧,并一再强调国家不具有任何内在的价值,国家只不过“是实现完全不同的其它各种价值的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辅助手段,国家只能从这些其它价值那里来获得自己的尊严,因而也只有当国家坚守自己的这一行动使命的时候,它才能保住这一尊严”。[171]
但作为一个在德国法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社会理论家,“法治国”的观念深刻地体现在韦伯的法律支配概念中。[172] 面对法律实质化中暗含的个人完全受制于国家治理的危险,韦伯唯一可以利用的理论抉择就是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但正如我们在前面论述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已经指出的,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不过和整个科层体制的例行化一样,同样也可能会吞噬了任何个人自由的空间,将所谓的个人自由完全笼罩在国家巨细靡遗的法律世界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不过是用一种逻辑上的形式理性体系重构了治安国“万能管理”的梦想:“要一劳永逸、面面俱到地规定其臣民的所有生活关系”。[173] 因为只有在这种完备的形式理性体系规定的范围内,个人才有自由和权利可言。面对这样的形式理性化的法律,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中举足轻重的自由的伦理理性化毫无位置,因为归根结底,这种法律仍是一种监护型的法律,个人的伦理不过是国家的伦理的一个映射罢了。这种将一切行为规则都整合为一个没有缺陷的体系的法律,“无论是使这些臣民们远离错误,还是给他们指明一条正确的轨道,它都立即去教训其臣民,即使是违其所愿,就象它应安排自己的家务一样”。 [174]。“它的雄心是想要预见所有可能的偶然情况,并将人类行为的范围规定到无微不至的家庭生活琐事”。[175] 因此,尽管国家不是在实质的意义上无所不能,但却仍然在形式规则的意义上无所不能。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差别,仍不过是“一种实质伦理化的非人格化”。 [176] 最终我们再次陷入了韦伯在政治社会学中面临的困境,只不过法律社会学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反映了这一困境的症状:没有自由的理性化,最终将我们带入了新的奴役的铁笼。魏玛德国的历史,正验证了这一点,面对纳粹的兴起,无论是形式理性的倡导者,还是“自由法”和自由裁量权的鼓吹者,都无力抗拒。[177] 在魏玛德国的一些法学家的笔下,纳粹德国这一“庞然怪兽”(Behemoth)的出现与“法治国”观念的内在缺陷有关。而英国的的法治(the rule of law)与德国的“法治国”,从字面上看有些类似,实际上却大相径庭。[178] 那么,从法治的角度看,在韦伯眼中,无论实质理性意义上,还是形式理性意义上的“法律理性在本质上低于欧陆,在类型上也不同于欧陆”[179] 的普通法,对于理性化与自由的二难困境,是否意味着另一种可能呢?
三、“普通法心智”的内在视角[180]:作为技艺理性的司法理性
(1)普通法、自然法与实定法
如果放在政治思想史和法学史中看,韦伯法律社会学里对英国普通法“理性”的较低评价,也许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甚至比起普通法在英国国内遭受的一些批评来说,还要温和得多。
在边沁的眼中,当时英国的法律,充满了各种缺陷、神话、虚构与误解:制定法含糊不清,类似奇谈怪论;法庭程序复杂、昂贵;取证方式完全人为决定,纯属非理性。边沁所震惊的还不仅仅是这些问题,更让这位社会福利的数学家震惊的是,英国律师心安理得地宣称这些弊病陋习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借助这种迷信观念来拒绝改革。[181]
而在边沁之前,霍布斯在他虚构的“哲学家”与“普通法学者”之间的对话中就指出,普通法所宣称的所谓“法律理性”(legal reason)是一种含混不清的东西。因为并不存在特殊的法律理性,在世上的生灵中,只存在一种人类理性,而普通法却拒绝承认这一点。这就是主权者的自然理性。[182]
和韦伯的论述一样,霍布斯与边沁的批评并非普通人对法律职业的敌视的一种“哲学升华”。[183] 这些“对话”和批评的实质,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及法律在其中的意义)之间的冲突。
在边沁对普通法大加鞭挞的背后,是他的伟大梦想:建立一种完善、全面的法律体系,一种“万全法”(pannomion)[184]。借用哈特的说法,就是将洞幽入微的青蝇之眼与总览全局的苍鹰之眼结合起来,力图让普遍、完善的法律之眼洞察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185] 这样的努力,在边沁看来,即使不是要彻底铲除普通法,至少要澄清英国法中“普遍性的不准确与紊乱之处”。[186] 而边沁对英国法的澄清工作的核心,就是将普通法“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揭露那些宛如“窃贼黑话”的律师行话和装神弄鬼的古怪装束背后的虚妄与迷信,而在这一切努力的核心就是将法律变成表达更加清楚,更加易懂的“常识”。尽管边沁并不接受霍布斯思想中的自然法观念,在他眼中,自然法与普通法的许多逻辑虚构一样,不过是神话而已。但是,至少有一点边沁和霍布斯是一致的,他们都认识到,普通法律师津津乐道的神秘“理性”,实际上却是拒绝承认以国王为代表的权威理性。[187] 在霍布斯看来,没有立法权的人,就不能创制法律。因此,象普通法学者那样,认为除了国王之外的所有法官加在一起,构成了所谓“完善的理性”(summa ratio),纯属虚构。[188] 而在边沁看来,普通法律师宣称的“自然理性”并不自然,真正的“自然”是常识性的规则,一个普通人的头脑就能够理解。[189] 表面上看,这种对“常识”的尊重继承了整个英国“普通法心智”(common law mind)的传统,但实际上是为通过立法权力来重构法律秩序铺平了道路。在边沁看来,在法官与律师这些专业人士支配下的法律秩序中,充满了恣意的非理性因素。必须借助彻底的法律改革,才能建设真正理性的法律秩序。
理性,又是理性!无论信奉普通法的律师或法官,还是秉持自然法的哲学家,推行效用原则的社会改革派,理性都是他们津津乐道的概念,但在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词背后,却包含了迥然不同的法律与理性的观念。
从霍布斯到边沁,希望建立的是一种“理性法律”(law of reason)。他们希望能够从有关人类与社会的本性出发找到建立社会秩序的一般原理,根据这种理性的原理建立一套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从这一普适性的制度出发规定每个社会成员行事的规则和拥有的权利。相反,在普通法的律师和法官看来,他们寻找的是一种法律理性(legal reason),这是一种弱意义上的理性,一种类似“常识”的推理能力。能够给出可接受的理由,“合情合理”的理性。[190] 前者是一种立法的理性,而后者却是一种司法的理性。[191] 边沁的“万全法”是一种建立在总体性逻辑上的立法理性观念的样板,和他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异曲同工。[192] 而普通法的司法思路的法律理性,是一种“根植性的治理实践”[193],一种混合式的社会秩序安排方式(mixed forms of social order)。[194] 两种理性之间的差别,正如克洛斯在评论边沁与布莱克斯通之间的争论时做出的精辟断言,边沁绝对是一个为一种观念所左右的人,而布莱克斯通却并不知道为一种哲学观念所左右是什么样子。而这一概括,也同样适用于整个实定法或“法治国”的治理逻辑与普通法的治理逻辑之间的巨大差异。[195]
因此,英国法之所以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理论中找不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不过是整个普通法问题的一个尖锐反映。无论是自然法学说,还是法律实证主义,尽管彼此相互攻讦,但却构成了主流的法学和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域。但无论对于法理学,还是社会理论,都确实象一位评论家所言,“普通法依旧不同寻常地令人感到困惑”。[196] 而这种困惑的原因就在于普通法与在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中占主流的“立法理性”的法律治理观念不相符合。
奥斯汀曾说,“从英国法的研究转向罗马法的研究,你就好象从一个混沌和黑暗的王国中逃脱出来,进入了一个比较起来,充满秩序和光明的国度”。[197] 而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普通法这种以“司法理性”为核心的法律治理观念,我们就需要从“法治国”或边沁的“万全法”这个“充满秩序和光明的国度”回到“混沌和黑暗的国度”,探究其中自然法哲学家和法律实证主义者们“不具有,也不打算研究”的各种技艺。[198]
(2)普通法是一种完善的理性
在霍布斯眼中,柯克不过是法律和政治上的老顽固,守旧派。而在普通法的史学家看来,柯克是使英国法现代化最重要的人物。[199] “对于所谓英国式自由的正统学说,没有一个辉格党人比柯克表达得更有力,比他拥有更深厚的学养”。[200] 可以说,是柯克一手将英国普通法从中世纪带入了现代,从而奠定普通法的理性传统。[201] 在柯克有关普通法的论述,他以独特的方式奠定了普通法的法律理性的基调,确立了现代普通法学说的传统。在一段广为引用的论述中,柯克断言:
“…理性是法律的生命,普通法本身不是别的,就是理性。应该把这种理性理解为通过漫长的研究、考察和经验而实现的一种在技艺上对理性的完善(an artificial perfection of reason),而并非每个人都具有的自然理性,因为没有人生来是有技艺的(nemo nascitur artifex)。这种法律理性是最高的理性(summa ratio)。而且因此,即使散布在这么多头脑中的所有理性都结合在一人头脑中,他也仍然不能产生英国法这样的法律,因为它是经历了许多时代的兴替,为无数伟大的博学之士一再去芜取精,完善而成,并借助漫长的经验,这种法律才成长为这一领域中治理的完善状态,这正验证了一句古老的法则:没有人,出于他自己私人的理性,能够比法律更有智慧,因为法律是完善的理性。”[202] 这段话集中体现了柯克有关普通法的法律理性的论述中包容的许多丰富意涵。首先,在柯克看来,普通法本身就等于是理性。对普通法这一法律理性传统的特点,当代普通法学者辛普森做了简明的概括:“在普通法制度中,说一些问题的特定解决方式是遵循法律,与说它是理性的、公正的或正义的解决方式,事实上,这两种说法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203] 这一观念并非无用的同义反复,而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涵。它意味着在普通法之外,无论在实质意涵上,还是在形式意涵上,都并不存在另外的“高级法”,或别的理性,来作为普通法法律理性的规范基础或价值依据。[204] 不太恰当地套用继承柯克思想的英国大法官和法学家哈勒(Sir Matthew Hale)的话说,“普通法就是英国的自然法”。[205] 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可以说,普通法的法律理性的特点就在于理性是内在于法律的,它与没有内在理性的立法理性构成了对立的两极。后者属于没有内在理性的意志过程,只与理性具有外在关系。[206] 其次,在柯克笔下,普通法是完善的。“法律是完善的理性”并不是说法律本身没有任何缺陷,而意味着普通法对社会生活中的任何困境都可以做出回应。 [207] 而且,普通法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是“一贯”的。“一贯性”(consistency)是普通法作为完善的理性的核心意涵。哈勒指出,每一种道德行动都因境况的差别而不同,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两次道德行动在各方面都一模一样”,这样就带来法律和治理方面诸多的不稳定性,而法律的“一贯性”正是为了克服这一危险。因此,普通法作为完善理性的学说,暗含了某种特定的法律发展的模式。[208] 法律是理性历久经年的产物,而不是立法者一时的恣意之举。这正是杰出的观念史学者波科克概括的“普通法心智”(common law minds)的最重要的特点:普通法是“超出记忆”(immemorial)的法律。[209] 针对这一问题,哈勒曾经举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普通法宛若阿尔戈英雄的船舰,尽管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最初造船的所有材料几乎都已经更换过了,但却仍然是原来的船。[210] 普通法的法官、律师和学者都一再强调,普通法的理性是历代贤人智者几百年经验的结晶。正是基于这一缘由,他们才和哈勒一样,“宁愿采纳这种完好地支配了四五百年的英国法,而不是听凭我个人的某种新的理论(尽管比起王国的法律,我对自己理论的合情合理之处,要更加熟悉),来推进王国的幸福与太平”。 [211] 哈勒的这一论述大概正是许多普通法的批评家经常攻击的靶子。在这些批评家(无论是自然法哲学家,还是实证主义者)眼中,普通法的“保守性”渗透在整个英国政治思想中,阻碍更加理性化的改革。但实际上,柯克和哈勒这些普通法法官对一贯性的强调蕴含了非常重要的普通法理性,这突出地体现他们区别“不便” (inconvenient)与“伤害”(mischief)的学说中。所谓“不便”实际上就是“不一贯”(inconsistency)[212],是对整个法律理性的一个威胁。在柯克看来,“任何不便之物皆非法律。而作为完善理性的法律不能忍受任何不便的东西。”而相比之下,个别案例所带来的“伤害”,其影响就小得多。因此,“法律宁肯承受不幸,而不能忍受对许多人造成的不便”。[213] 因为正是这一点将法律与恣意区别开来。所以哈勒才说,“一种恣意带来的不便是不可容忍的,而因此,某种多少导致一些伤害的法律要比恣意好”。[214] 事实上,这正是全部先例原则的司法理性基础。即使猛烈攻击普通法的“反对改革的狭隘情感”的边沁,也接受普通法的这一理性,反对法官任意违背先例。 [215] 最后,普通法的这种“完善理性”不是通过封闭的逻辑形式体系建立的,而是通过开放的法律技术完成的,这就是柯克所谓的“技艺理性”(artificial reason)。这种理性能力是与“智慧、审慎或技艺”联系在一起的。[216] 这是一种“逐渐的,推理性的”(gradual, discursive),是一种“推理过程”(ratiocianation),而非“唯理化”过程(rationalisation)。[217] 其核心是法庭论辩时控辩双方在相互争执时为自己的论述提供依据的修辞学意义上的理性,而非逻辑学意义上的理性。[218] 这也是我们称普通法的理性为一种司法理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普通法的“完善理性”就是借助各种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采用的技艺来建立、维持、再生产法律的 “一贯性”。而普通法就是这些技艺理性在时间上的积累与完善。
普通法的这种“技艺理性”与自然法学说和实证主义倡导的“自然理性”相去甚远。当1608年,詹姆斯一世试图自己断案时,柯克援引先例拒绝了国王的这一要求。詹姆斯一世的回答是,既然法律是基于理性的,那么他和法官一样具有这一理性。柯克断然拒绝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在这段著名的论述中,柯克指出,“确实上帝赋予陛下天纵神明,自然的伟大秉赋;但是陛下并没有研习过他所治下的英国的法律,而与陛下的臣民的生活、继承、动产或财产有关的案件的判决(decided),不是依据自然理性,而是依据技艺理性和法律的判决(judgement)。法律是一门艺术,要求长期的研究与经验,之后一个人才能了解它…”。[219] 因此,普通法的技艺理性就是一种“通过运用与练习才能习惯的…推理能力(reasonable faculty)”。[220] 而正是这种与普通法在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等方面的特点密切相关的技艺理性,构成了普通法的司法理性的核心。
(3)普通法的司法理性:例行案件与疑难案件
普通法的法律理性是一种司法理性,也就是说,普通法的法律理性是一种以法庭为核心的理性,这正是技艺理性的实质意涵。而在这种技艺理性中,例行案件的审判与疑难案件的审判担负了不同的角色,共同构成了普通法的程序技术。
对于普通法的司法理性来说,例行案件(routine cases)[221] 与疑难案件(hard cases)的区分[222]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试图建立一种“万全法”的立法者眼中,所有的案件都应该并能够成为例行案件。而实定法的逻辑也就是将全部法律体系中的案件都等同于例行案件,而所谓“疑难案件”不过是法律规则体系中缺陷的产物,是实定法理性的一个伤疤。在理想的“实定法”中,是没有位置的。而在普通法中,不仅承认疑难案件存在,而且对于普通法的发展来说,疑难案件审判中的法律推理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然,强调疑难案件在普通法中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例行案件不重要。[223] 二者在普通法的技艺理性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通常认为,在例行案件中,可适用的法律规则是十分清楚的。对应任何操作性的事实p,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款“如果p,那么q”来涵盖这种情况,所以法庭就应该执行相应的法律后果,q。[224] 但是,这样的分析方法实质上又把普通法还原为制定法,将司法理性还原为立法理性。[225] 而现实中,判例法对例行案件的法律推理技术,要比许多皈依立法理性的学者想象的微妙得多。
在例行案件中,法官的工作实际上既涉及到处理复杂性的问题,也涉及所谓“特殊化”的过程。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它的逻辑都不是三段论式的,而是决疑术(casuistic)式的,或者说是修辞术式的。
任何法官面对的案件都是具体案件,这意味着案件所处理的事件,都是由复杂的和特殊的事实构成的。面对复杂的事实,法官需要区分重要和不重要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与韦伯的说法相反,大陆法和普通法没有什么差别。[226] 区别之处在于,如果说大陆法中的法官寻找的是使适用类型化的法律规则成为可能的操作性事实(上述所谓“p”)的话,那么在普通法的法庭中,焦点则是使该案件与先例之间的类推成为可能的所谓“类推关键”(analogy key)。[227] 借助操作性事实,法官能够将一个案件的事件归类,从而援用实定法中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换句话说,正是一个案件中的操作性事实,将具体案件与在一定的适用范围内具有绝对性的规范联系起来,使“若-即”(if/then)的条件程式能够发挥作用,后者是所有实定法的法律规范的基本程式。[228] 但在普通法中,先例与具体案件之间的关系,并非类与个别项的关系。先例并非一个普遍性的范畴,而是一个范例(example)。而范例与规范不同 [229],它与具体案件的逻辑地位是相同的,都是针对特定的事实。也就是说,作为范例的先例,即使在适用范围内,也不是绝对性的,而只具有一般性。 [230] 因此,“类推关键”也并不是要将一个具体案件还原为一个一般性的模板,而是在两个具体案例之间建立类推联系。当然,在进行类推时,我们对两个具体案例的了解是不同的,我们对先例更“了解”,否则就无法,也没有必要进行类推了。[231] 而这种“了解”,并不是说先例中蕴含着“规范”,而是因为先例中的判决理由提供了将“实质事实”(material facts)[232] 与各种法律原则联系起来的范例。“没有发现原则的地方,也没有办法使用类推”。[233] 而先例中的“判决理由”实际上并非一种规范陈述,而是将“实质性事实”与“法律原则”联系起来的实践理性方式。类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这种实践理性方式的延伸。普通法的这种实践理性,形成了面对每个具体案件中的特殊事实的程序技术,培养了对特殊性的尊重。无论是法官,还是律师,养成了专注案件中的特殊事实的“普通法心智”。正如本世纪初,哈尔斯伯里勋爵(Lord Halsbury)在其判决中所指出的,“每一个判决都应该理解为是针对业已认可或假定如此的特殊事实,因为在判决中发现的表述,其一般性并不在于要澄清整个法律,而在于能够支配会与这些表述连在一起的一些案例的特殊事实,并且这些表述也从特殊事实中获得了一般性的资格。”[234] 因此,在例行案件的司法管理中,严格遵守先例的原则就是要运用类推的修辞术,而非逻辑三段论,兼顾待决案件实质事实的特殊性与一般性(通过与先例中的实质事实进行类推),在保障法律的“一贯性”和稳定性,保证同等案件同等对待的同时,使案件事实的特殊性受到应有的重视。[235] 实际上,这是一种通过特殊化建构普遍主义的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吸纳特殊性因素,将它们作为迈向普遍主义的动力。而这种方式在普通法(通过先例原则体现出来)中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反映了司法理性的特点。韦伯有关普通法的实质非理性与形式非理性都与此有关,但这正是普通法“理性”乃至“理性化”(法律发展)的特点。
从司法管理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例行案件是适用法律的话,那么疑难案件则是“发现法律”,或者采用经典普通法理论的说法,是“宣示(declare)法律”。
在普通法中,疑难案件的根本特点在于,在案件中,双方能够将案件的特殊事实与不同的“法律原则”联系起来。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要么是因为双方在构成案件的事件中发现了不同的“类推关键”,从而将案件与不同的先例系列建立起类推关系;要么是因为尽管双方对案件中的“类推关键”没有分歧,但对先例中的“判决理由”的看法却大相径庭,也就是说,双方对先例中的“实质性事实”没有分歧,但却对先例将这种“实质性事实”与何种法律原则联系在一起,以及联系起来的方式,无法取得一致。[236] 而造成这种“疑难”状况的原因,既可能由于“先例”过多或者不足,也可能是因为以往的先例难以理解,范围不清,甚至由于时代久远等原因而失灵。[237] 不过总之,疑难案件就意味着法庭难以象例行案件一样,借助类推,找到一种简便易行的处理案件特殊事实的方式。
因此,疑难案件的判决过程就是先例得到明确或再生产的过程。而这种“再生产”先例过程的核心就是重新构建事实与“法律原则”之间的关联方式,从而修正或完善法律原则。而疑难案件中再生产先例的过程,既是普通法发展的重要方式,也突出地体现了普通法司法理性的主要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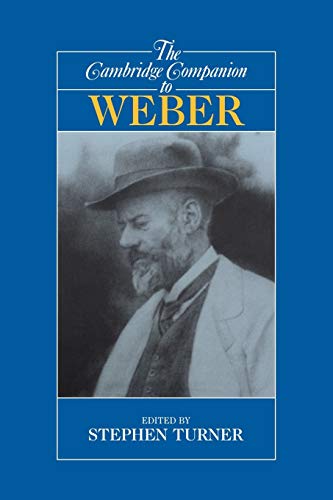 一般来说,在疑难案件中,双方都能够提出有说服力和正当依据的论述,并能够在案件中找到相关的实质性事实,来支持本方的法律主张(claims)。在这些论述的背后,往往涉及了相互抵触的不同价值,无论这些价值是道德的、宗教的,还是经济与政治的。而在这些不同的价值中,包含了社会成员各种不同的权利。对于这些相互冲突的价值,无论在法律之外,还是法律之内,我们都找不到一种“元”价值,从而在这些价值之间建立等级制的关系,来决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疑难案件实际上正是“除魔的世界”的困境在法律中的体现,即在“诸神之争”中,没有一种“了结”现代社会中多元价值冲突的超越性的一元途径。[238] 疑难案件是现代社会“价值自由”的一个突出反映。而且,还进一步体现了这种“诸神之争”中相互斗争的特点,一种所谓“敌对的文化”(adversial culture),而在普通法中,也蕴含了一种借助司法理性的修辞来展现这种对抗性的方式。[239] 不过,在普通法的疑难案件的抗辩和判决中,无论律师还是法官,实际上都很少直接诉诸这些相互冲突的价值,他们论述与争辩的核心却是各种法律原则。这些原则不能等同于这些价值,而是涉及这些价值的实现方式、手段或技术。[240] 例如在广为讨论的“里格斯诉帕尔默”案(Riggs v. Palmer)[241] 中,厄尔法官与格雷法官实际上就诉诸了不同的法律原则,判里格斯胜诉的厄尔法官认为,“任何人不得因为其过错获得利益”,因此,毒杀祖父以获得遗产的帕尔默无权得到遗产;而正如德沃金所指出的,判帕尔默胜诉的格雷法官尽管没有明言,但也诉诸了一定的原则,尽管是不同的原则,如一个人有权合法获得遗产。当然在法官对这些原则的论述背后,涉及了许多更基本的价值,如对立遗嘱人的自由意志的尊重,如传统的正义观念等。而这些价值,归根结底,是人的一些基本权利。
一般来说,在疑难案件中,双方都能够提出有说服力和正当依据的论述,并能够在案件中找到相关的实质性事实,来支持本方的法律主张(claims)。在这些论述的背后,往往涉及了相互抵触的不同价值,无论这些价值是道德的、宗教的,还是经济与政治的。而在这些不同的价值中,包含了社会成员各种不同的权利。对于这些相互冲突的价值,无论在法律之外,还是法律之内,我们都找不到一种“元”价值,从而在这些价值之间建立等级制的关系,来决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疑难案件实际上正是“除魔的世界”的困境在法律中的体现,即在“诸神之争”中,没有一种“了结”现代社会中多元价值冲突的超越性的一元途径。[238] 疑难案件是现代社会“价值自由”的一个突出反映。而且,还进一步体现了这种“诸神之争”中相互斗争的特点,一种所谓“敌对的文化”(adversial culture),而在普通法中,也蕴含了一种借助司法理性的修辞来展现这种对抗性的方式。[239] 不过,在普通法的疑难案件的抗辩和判决中,无论律师还是法官,实际上都很少直接诉诸这些相互冲突的价值,他们论述与争辩的核心却是各种法律原则。这些原则不能等同于这些价值,而是涉及这些价值的实现方式、手段或技术。[240] 例如在广为讨论的“里格斯诉帕尔默”案(Riggs v. Palmer)[241] 中,厄尔法官与格雷法官实际上就诉诸了不同的法律原则,判里格斯胜诉的厄尔法官认为,“任何人不得因为其过错获得利益”,因此,毒杀祖父以获得遗产的帕尔默无权得到遗产;而正如德沃金所指出的,判帕尔默胜诉的格雷法官尽管没有明言,但也诉诸了一定的原则,尽管是不同的原则,如一个人有权合法获得遗产。当然在法官对这些原则的论述背后,涉及了许多更基本的价值,如对立遗嘱人的自由意志的尊重,如传统的正义观念等。而这些价值,归根结底,是人的一些基本权利。
因此,面对疑难案件背后无法妥协的价值,法官的任务并非是要认同其中某项价值,从而认可某种权利,或者否认某种权利。[242] 在疑难案件中,法官的工作实际上是要确立:当两种(或多种)不同的价值发生冲突时,人们进行自由选择,并采纳不同实践技术来解决冲突的可能范围。实际上,在任何具体偶变的互动场景中,当不同的背景权利面对面地发生冲突时,法官的任何判决都并没有直接触及这些权利,而只是禁止在类似的情境中采纳某些权利的实践技术,或者容许采纳某些实践技术,或者对一些方式采取置之不理、不闻不问的态度。简言之,普通法中的法律判决的实质,是对实践权利的技术的管理,而不是对权利本身的管理。就“里格斯诉帕尔默”案而言,案件的最终判决并没有否认格雷法官所诉诸的价值:一个人获得遗产的自由权利,以及对立遗嘱人的意志的尊重。但这一案件明显禁止一个人采用谋杀这样的方法来实践他的权利;同样,尽管确实象格雷法官所言,很可能即使祖父知道帕尔默会毒杀自己,他仍会将遗产留给帕尔默,但这一判例明显也限制了立遗嘱人实现自己立遗嘱的自主权利的某些方式。因此,法官的判决并非道德判断,而是对面对价值冲突时的实践技术所做的程序性判断。拉斯柯尔尼柯夫斯基并非因为想成为一个尼采式的“超人”而被判刑入狱,而是因为他成为超人的实践方式。
而从普通法的技艺理性来看,尽管法官的判决,涉及了相互冲突的不同价值的实践行为,但却并非自由裁量权的产物,也不意味着恣意因素的增加。普通法的法官通过对疑难案件的判决,使法律对实践权利的技术的管理具有“一贯性”。这也正是对疑难案件做出判决时,法官考虑先例的重要原因,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先例中的判决理由往往只具有建议性或劝导性,而不具有拘束性的力量。因此,将普通法法庭中的法官的工作与面对狄更斯小说的文本解释学者的工作做类比是危险的,因为法官要比所有的解释学者,甚至圣经解释学家,更关心“解释”过程中的程序色彩。[243] 在这里,“权衡”(weight,或“权重”)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就体现了出来。正如韦伯所一再指出的,价值是不可权衡的,因为价值是绝对的,排他的。但当面对一个疑难案件时,价值与案件的特殊事实之间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案件的特殊事实涉及的不是价值本身,而只是当事人具体实践这些价值的方式,因此,双方争执的焦点也是在这些实践价值的方式上。而双方援引的原则实质上是法律在管理实践技术时的“一贯”做法。这种做法,与实定法中的条件程式样态的法律规则不同,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要么是要么不是(either/or,或所谓“all or nothing”),而是涉及不同的权重。面对一个案件,没有任何一种原则能够宣称己方具有绝对的权重。[244] 也就是说,对处于价值冲突中的当事人来说,作为疑难案件焦点的实践技术,总会在以往的判例中找到一些技术依据。而疑难案件的判决,则进一步明确了法律对这样的技术的“一贯”管理倾向,这种倾向正是法律的“理性”所在。因此,疑难案件往往可能成批出现,这一般体现了现有法律在实践技术的管理方面面临一些问题,而疑难案件的判决和先例的建立,则意味着法律对相关的实践技术确立了比较明确的管理方式。[245] 疑难案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普通法的法律理性的程序性特点,即普通法采用何种方式在技艺理性与法律之外的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建立联系。如果说,韦伯敏锐地洞察了现代社会中各种价值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殊死斗争…没有相对化或者妥协的可能”[246],那么他面对这种“诸神之争”的解决方案,却忽略了尽管价值之间不可妥协,但相互冲突的价值的各种实践方式确实可以“权衡”和“斟酌”。而从观念史的角度看,这也反映了普通法理性背后隐藏着亚里士多德面对价值冲突时的实践智慧。[247] 另一方面,如果说德沃金的权利命题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疑难案件对于背景权利来说,确实意味着一种制度化的过程。因为背景权利(价值)本身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甚至可以说是“空”的,人们可以采用无限多样的方式来践行这种权利,充实这种权利。而法律的重要任务正在于对人们实践权利的方式进行管理。权利并非法律规定的,甚至权利的实践方式也不是来自法律,但法律的发展却等于实践背景权利的技术的发展,这既意味着法律中提供了许多实践含糊的背景权利的方式(法律规则的构成性一面),也意味着排除了许多实践这些权利的方式,因为在这些实践方式中,可能危及了同样重要的其他一些背景权利(法律规则的制约性一面)。例如,言论自由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背景权利,但这项权利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哪些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实践权利,哪些方式是可行的,对其它同样重要的价值或权利造成的损害是社会可以容忍的;而哪些实践言论自由的方式,严重妨碍了其它价值的实践,从而是社会不可容忍。而当美国法庭的判例确定,除非出于恶意新闻中的错误报道不属于诽谤,那么这一判例同时意味着某些非常具体的实践言论自由的方式,获得法律认可的空间。说到底,所有的价值都是危险的,因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绝对的和排它的,所以实践这种价值总是可能(或许是必然)导致对其它一些价值的损害,但并非价值的所有实践方式,都是不可容忍的,只有某种价值的实践方式,严重损害了其它价值,才是不可容忍的。价值的潜在危险,由道德哲学或社会分析来揭示,而实践价值的方式是否可以容忍,却是经由普通人的实践来探索和尝试,并由法律来管理。
因此,无论法律实证主义,还是法律的各种道德化论述,事实上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将价值或权利与其实践技术混淆起来。人的基本权利仅仅是一种可能,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同样也只是一种可能,它们都是人们行动的潜在背景,而真正得以制度化的从不是含糊但却趋于绝对的这些彼此相互冲突的权利,而是实践权利的技术。因此,制度化形成的既非实证主义眼中的法律“权利”,也不是通过法律来认可的基本权利,更不是道德主义者心目中的自然法则或正义,而不如说是践行这些权利的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化意味着技术化。在各种“实体法”中,充满了对这些实现权利的技术的可能空间的规定。而对法律发展的比较研究表明,发达的法律与不发达的法律之间的差别,正在于这些与权利的具体实践方式有关的原则,而不在于基本权利方面含糊的“一般条款”。[248] 不过,普通法实现权利技术化的方式[249],既不象“法治国”那样采取主动干预的方法,也不是象二十世纪依赖的社会福利国家中的“集体主义”立法措施,而是一种“被动”的方式。普通法是等待公民的自由行动,然后才认可或否定这一行动所采取的实践技术。[250] 不过,惟其被动,方才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法,不是一种庇护型的法律,而是一种自助型的法律。但在这样一种自助型的法律中,法官本身面对了更大的 “理性化”压力。他需要通过先例的再生产机制(上诉法院面对的疑难案件),通过原则的再生产,维持这种法律的“一贯性”。[251] 一方面,保证社会中人们在“自由”互动时的技术相容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法律不是禁闭型的――限定活动的边界,而是永远留有或者引发更广阔的技术开发空间,等待人们的“努力”。因此,普通法的判决,要通过各种程序性逻辑(如严格遵循先例的原则),来维持普通法的“一贯性”,确保个人在创造各种实践技术时,可以参考以往法律的先例,借助或发展其中的技术。只有这样,才使各种法律之外的所谓非正式“创造秩序”的安排得以进行,使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生活的 “法官”。[252] 因此,韦伯在普通法中发现的严格的程序性特点,并非“外在的仪式主义”,而正是普通法作为司法理性的突出特征。
(4)司法理性与程序技术
埃文认为,韦伯在分析法律理性时,实际上谈到了两种不同意涵的法律理性。一种是法理意义上的逻辑理性,另一种则是形式正义和正当程序。而在韦伯有关资本主义兴起的论述中,更重要的不是逻辑上的形式理性,而是对司法的形式理性的管理。[253] 埃文的论述揭示出我们一直强调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法律理性在韦伯的著作中也仍然存在。不过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韦伯的分析中,法律理性的象征是以晚期罗马法为样板的法学家的法,它渗透在整个大陆法的“精神”中,特别强调将所有法律“纳入公理和法规的有机的理论系统之中”,采用系统化原则支配下的演绎推理机制。[254] 而埃文发现的另一种法律理性,实际上在整个法律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中都居于边缘地位。这种法律理性的代表就是普通法。而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实际上是因为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中,受到德国“法治国”理念和概念法学的影响,普通法这种主要以司法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法律理性,在理论中才找不到恰当的位置。而在立法理性支配下的视角看来,普通法成了难以理解的“怪胎”,无论从实质理性角度,还是从形式理性角度,都乏善可陈。
但正是这种“理性程度较低”的普通法理性,却可能提供了一条解决韦伯的理性化与自由的困境的思路,给我们留下了在除魔的世界中争取自由的可能性。不过,要理解这种普通法的理性,就需要从审判视角的法律理论出发,将法律过程本身看作是法律的核心。[255] 普通法这种强调审判过程的法律理性,与以立法理性为核心的德国“法治国”相比,实际上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法治观念[256],它的核心特征是程序性与自助性。可以说,普通法的法治是一种以程序为中心的“被动”取向的法律管理。
当然,韦伯本人就已经注意到普通法的程序化,但正如我们指出的,韦伯认为普通法对程序的强调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主义,一种带有浓厚仪式色彩、传统色彩的形式主义。从普通法程序的历史渊源来看,韦伯的论述有一定的道理,普通法对程序的强调来自封建法。例如,被视为英国自由观念基础的《大宪章》,其有关“正当程序”的核心条款几乎原封不动地抄自封建法律。[257]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普通法的程序特点,是一种无实质内容的形式主义。事实上,普通法的这种程序化,既与韦伯所说的逻辑理性的形式化不同,也并非韦伯所认为的那种外在的形式主义。
德国学者托伊布讷指出,现代法律的进化经历了形式化,实质化与程序化这三个阶段。如果我们放弃这种一元进化论的观念,我们就会发现,普通法法律发展的特点,正是程序法先于实体法,在普通法早期,就体现了对程序超出寻常的关注。[258] 这种对程序的关注,并非如韦伯所言,出于仪式主义或巫术的考虑,而更多是为了尽可能地消除司法判决过程中的恣意因素。[259] 而且正如下面我们会看到的,从普通法的形成角度来看,这种对程序的强调,意味着普通法能够吸收当时在英国盛行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法律,利用这些来源丰富普通法。因此,普通法在法律程序(以及法律职业)方面的封闭性,正确保了普通法在司法管理方面的开放性。普通法的这一特点也验证了托伊布讷的论述,程序化的法律,最具封闭性,也因此最具开放性。[260]
普通法通过封闭程序实现的开放性,就体现在普通法具有能够容纳不同的法律渊源,管理不同的实践技术的“反身性”的法律要素。[261] 正是普通法中带有“反身”色彩的法律程序,使普通法的法律理性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复杂的价值多元格局。这一点在柯克爵士当年的判决中就有突出地体现。
无论就实质理性看,还是从形式理性的角度来看,柯克爵士在卡尔文案(Calvin’s case)与邦海姆案(Bonham’s case)中的判决都是自相矛盾的。从司法审查或宪政的角度看,在邦海姆案中,柯克爵士强调了法律高于君主,而在卡尔文案中,则似乎完全相反;从判决的潜在依据来看,在邦海姆案中,柯克爵士提出了著名的技艺理性的原则,而在卡尔文案中,则援引了自然法学说。[262] 但这样的看法完全忽视了柯克爵士在两案中的对普通法理性的建设性意涵。如果我们从法律管理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在卡尔文案中所援引的自然法,其意涵与诸多大陆学者的态度仍然有重大的区别。在柯克眼中,自然法构成了英国法的一个渊源,但仅仅是英国法诸多渊源的一个,“自然法是英国法的一部分”,但却并非英国法的基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自然法并没有构成英国法的理性,相反,英国法是依据自身的技艺理性来对待自然法的。这就是哈勒所谓“有限的自然法” (limited law of nature)。[263] 因此,无论邦海姆案,还是卡尔文案,尽管柯克爵士的论述援引了不同的价值,但却依据了同样的理性。[264] 在柯克的学说中,既没有试图清除自然法的学说[265],同样也没有依据自然法的学说为他的判决理由寻求更基本的依据,而是一种能够通过程序技术来使自然法的价值发挥作用的技艺理性。
事实上,正是这种技艺理性构成了英国法程序技术的关键环节。从韦伯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技艺理性似乎既非实质理性,亦非形式理性。它的要害是如何发展一套复杂的技术来将多元实质理性中各种相互冲突的主张与稳定性、可预见性和持续性的形式理性要求协调起来。正是这种技艺理性,使普通法法律活动既没有演变成自然法学说意义上的实质理性法,也并非实证主义者心目中的那种形式理性法,而是能够以特定理性方式回应实质理性的技艺理性法,正是这一点,将普通法的“理性化”与吸收自然法理性的实定法的“理性化”道路区分开。
因此,理解普通法的程序技术,既不能将其“形式化”(当然,同样也要警惕过分实质化的危险),更不可将其“工具化”。在普通法的程序技术中,蕴含了将法律的内在管理与外面的价值在区分的前提下借助程序关联起来的方式。而普通法的这种关联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与德国分析实定法“程序化”的学者的论述不同,并非只讲“系统”,同时也非常重视普通法律行动者的作用。这是一种强调个人的自主努力的“程序技术”,强调借助法律的程序技术来推动生活中的实践技术,借助后者来“发现”法律。
如果说,德国的“法治国”实际上是由国家来担任个人自由的保护者和庇护者,因此,这种法治是一种主动干预型的法治。那么英国以普通法为核心的法治,直到18世纪,则始终主要是一种低调的,自助型的,被动取向的治理。正如我们上文在论述审判“疑难案件”的技艺理性所揭示的,这种法律管理,主要是借助个人的司法行动来完成的。用富勒的话说,这种法律管理是一种将公民看作自决行动者的法治形式。在这种法治中,“人是,或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行动者,能够理解、遵循规则,并为其行为负责任”。[266] 这样一种“强调个人艰辛与努力”[267] 的法律制度,能够运用个人的自主行动来创造自由的空间,而同时又能够运用法律的程序技术,来维持法律的稳定性与中立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普通法是一种“根植性的治理实践”。普通法的经典理论认为,法官并没有创制法律,而只不过是在宣示法律。奥斯汀认为,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孩子气式的虚构,当代的普通法的法学家也很少接受这样的理论,把它看作是一种迷信。[268] 但实际上这一学说却精确地反映了普通法的法律管理的特点,普通法本身并不预先规定人们的行为模式,相反,普通法是以被动的方式对普通人的实践技术来进行管理。普通法的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普通法的“回溯性立法”的问题上。
边沁尖锐地批评说,普通法的法官在适用法律之前,没有人知道这种法律是什么,即使律师也不知道。这就象你对待自己的狗一样,当你想训练它的时候,你就等它做了一件事以后,再因此打它。而普通法法官的做法和这种做法没什么两样。[269] 这一批评尽管尖刻,但却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普通法理性的重要特点:诉讼当事人和法官、律师一起,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法律本身的建构。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普通法的任何一次判决,都并没有“立”法,因为这次判决并未凭空生产了新的原则,而只是在这一判决与以往的一系列先例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从而在不同的原则之间进行了新的权衡。从普通法的法律理性来看,疑难案件并没有危及“完善的法律理性”,相反,通过它,普通法得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并在法律调整的过程中再生产出法律的“一贯性”。但是普通法的特点在于这种法律的调整,肇始于诉讼当事人利用法律程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其实质正是对业已发生过的权利实践方式的认定。[270] 可以说,正是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实践,构成了法律对于相关权利的实践方式进行规定的前提。事实上,这有可能意味着在这一案件中总有一方的当事人可能受到了某种伤害,他有可能为他的权利实践行为付出代价。不过在我看来,比起普通法制度,“万全法”中巨细靡遗的行为规定,或者“一般条款”中含糊、空洞的权利规定,倒更容易将社会行动者变成巴甫洛夫的狗,一旦没有了“若-即”的条件反射的铃声,就无所适从。实定法大概比普通法,更象是“狗的法律”,因为只有狗才不需要自由的活动空间,更不愿意为所谓“自由”付出代价。
所以,正如布莱克斯通所指出的,所谓“英国式的自由”的实质就在于普通法是经人民之手引入的。“我们之所以自由,是因为治理我们的法律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自由不是因为我们拥有它,支配它,有权使其为我所用,而是我们感觉完全与之融汇在一起,它成为我们内在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完全参与了它”。[271] 当然,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普通法的这种法律发展模式,实质上是利用普通法的技艺理性来吸纳普通人对法律之外的各种价值所进行的实践尝试。普通法中的各种法律原则并非立法者凭空制定出来的,亦非法官的自由意志的产物,而是一方面能与各种法律之外的价值保持开放的关联,另一方面又传承和丰富“超出记忆”的普通法的技艺理性传统,这些传统以一种强调个人自助的方式,建立了如何实现法律之外的价值的实践技术的特定谱系。
在现代社会,“疑难案件”的日益增加,验证了韦伯的基本观点,现代社会是一个诸神之争的除魔世界。日益抽象化,但同时也异质化的观念体系之间构成了尖锐的冲突。这种规范的“过度生产”[272],就对法律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稳定性与弹性、自主性与容纳性提出了挑战。对于这个问题,法律实证主义力图通过广泛的集体性立法行动来完成,而普通法则倾向于利用个人的司法行动(诉讼)来完成的。因此,疑难案件的实质,就普通人而言,是个人借助司法手段,来创立实践权利的技术,开辟“自由活动的空间”。而就法官而言,则是通过对这些不同的权利技术的程序化干预,权衡法律原则,来协调这些技术之间的内在理性。
可以说,普通法采用自身的办法(例行案件与疑难案件)实现了卢曼所谓面对社会复杂性的规范封闭与认知开放的二难问题。[273] 普通法的做法也许并不象表面看上去那样更不合理性,或许象富勒所言,更理性。因为“普通法有一个好处,就在于它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人类复杂多样的经验,它忠实地体现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令人困惑的地方,而不是将这些隐藏在一种法典脆弱的几何结构中。”[274] 而对于我们的讨论至关重要的地方在于,普通法将推动这种法律理性化的力量,留给了能够担负自主行动本身面临的危险的公民。在普通法下生活,就意味着要象韦伯笔下的清教徒一样,有勇气和智慧认识到,“上帝只救助那些自助的人”。[275]
四、“普通法心智”的外在视角:司法理性的治理
(1)司法理性的治理:普通法的形成
我们说,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围绕普通法的技艺理性进行的“法治”则主要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这种治理的突出特点是借助程序技术推动并容纳普通人发展实践权利的方式。那么英国何以能够发展形成这样一种司法理性的法治,而没有象绝大多数大陆国家那样,借助 “强”国家的科层体制的推动,通过罗马法的继受,建立了一种结合了“立法者”的法律与“教授”法律的法理权威呢?
从普通法的形成过程来看,这种司法理性的发展,与英国独特的治理实践的历史密切相关。从11世纪开始,在英国,当早期现代国家试图发展中央权威时,中央力量相当薄弱,而它面临的治理问题却十分复杂。[276] 王室权力、议会、教会、地方行政、封建势力与社区自治等各种力量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制衡关系。而普通法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最初正是为了解决早期现代国家面临的治理问题,尤其是治理的超人身化(depersonalization)和跨地方化(translocalization)问题。不过,颇具悖谬色彩的是,为了解决王室治理问题,发展中央权威,普通法逐渐趋于专门化、职业化和自主化,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司法理性,而伴随这种借助法律的治理的理性化,最初作为王室治理工具的普通法,却慢慢发展为具有“宪政”色彩的法治的核心环节。而独特的司法理性,也成为社会成员,尤其是士绅与市民培养权利实践技术的主要手段。
英国司法理性的治理,在11世纪随着“诺曼征服”,与英国早期国家政权的建设联系在一起。这种治理的主要制度框架,主要是在12世纪晚期金雀花王朝国王亨利二世进行的著名改革中确定下来的。尽管与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以后的治理相比,这一时期英格兰的治理,仍非常有限,但英国法的这一形成阶段,对于后来司法理性治理的发展影响颇大,并对整个英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非常持久的影响。
从欧洲的视角来看,亨利二世在位期间(1154-1189),法兰西与德意志两个欧洲大国,也同样试图加强王室的权力,并同样诉诸法律来强化这种中央化的权力。但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只有英国亨利二世的法律改革留下了持久“一贯”的影响,无论借助罗马法复兴来推动法律制度建设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红胡子腓特烈(Frederick Barbarossa, 1152-1189),还是法王菲利浦二世(Philip Augustus, 1180-1223),他们推行王室控制之下的法律权威的努力,大都只在王室直接控制的领地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而且从法律统一的的角度,在欧洲大陆上,具有普遍意义的罗马法与具有浓厚习惯法色彩的所谓“外省法”、“日尔曼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法团类型的法律和特权一直长期并存。[277] 法国直至旧制度末期,仍未充分完成法律的统一。[278] 可以说,整个欧洲,除了英国以外,所有的政治单位,都只有地方习惯法和全欧意义上的“普通法”,而没有遍及单一的国家领土意义上的“普通法”,作为民族法的普通法。[279] 从治理的角度看,直至18世纪末,德法两国都未能找到超人身化和跨地方化的法律治理方式,而英国的情况则非常特殊,部分由于领土范围狭小与岛国的封闭性,部分由于“诺曼征服”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统一治理的基础,英国的王室能够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逐渐在整个英格兰领土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法律治理,这也正是“普通法”一词最初的意涵,即超越复杂多样的地方习俗与习惯法的英格兰王国“共同的法律”(ius commune)。[280] 因此,从法律治理的角度看,普通法并非习惯法,而是吸纳各种地方性的习惯法,均衡不同的习惯法的产物。
在“金雀花改革”(Angevin Reform)之前,尤其是“诺曼征服”之前,司法治理主要是地方性,尤其是社区性的和封建性的,较少由中央权威来统一进行;断续的,治理针对的并非日常事务,而是各种突发事件。在这一时期,大量案件都是由领主的封建法庭和更基层的社区的庄园法院来处理,这些法院都是不定期的,主要采用各种习惯法性质的规则和程序。[281] 事实上,即使在法律制度的创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亨利一世,在位期间,其治理的主要方式,与法德等国的“人身化”的治理方式也没什么两样,尽管国王可能是具有强大权威的“强人”,但治理却很少例行化,缺乏稳定的基础,需要依赖国王的“具体在场”,来保证这种生杀予夺的大权。治理的统一性和一贯性,受到国王有形身体的局限。而且一旦国王的身体死亡,而没有一种看不见的“身体”,国王的另一个“不朽身体”来保证治理的连续性与稳定性。[282] 所以,当亨利一世这位政治强人去世后,整个英格兰和欧陆后来几百年的情况一样,围绕“继承”问题展开的争执和战争迅速使整个国家陷入无序之中,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王室权威瓦解的迹象,而日益增长的土地所有权方面的纠纷也不得不经常诉诸武力来解决。
与后来18、19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许多民族国家及其借助“法典化”在领土范围内推行统一的“普通法”相比,12、13世纪在王国领土范围内推行司法理性治理的“金雀花王朝”的力量要有限得多,而恰恰是这一点,对英国的“法治”模式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283] 从亨利一世到亨利二世时期,金雀花王朝设立了许多王室法院,既有设立在西敏寺(Westminsiter)的高等法院〈如理财法庭(Exchequer),高等民事法院(Common Bench)〉,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设立了巡回法院(General Eyre),在整个王国领土内进行定期的巡视;以后又通过委派高等法院的法官组成民事巡回法庭(assize),审判有关土地占有方面的案件,进一步促进了法律的统一与稳定。从治理的角度看,这些王室法院意味着定期的、连续的、相对稳定和统一的它司法治理的出现。[284] 用当时一位来自欧陆的观察家的说法,英国皇家法院的特点就在于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始终一贯地,统一地”适用法律。[285] 而且,王室法院要求保存判决过程和最终判决的书面记录,也为后来法律报告的编纂,以及整个先例原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普通法治理的发展来看,在征服者威廉以来的司法改革过程中,王室法院并没有立即取消旧有的地方法院、庄园法院和教会法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王室法院一直与这些法院相互竞争,相应地,普通法也始终与各种不同法律相互竞争。[286] 直至1628年,柯克还列举了英国当时存在的16种法律,而普通法只是其中的一种。[287] 而正是通过各种法律之间的并存和竞争,普通法逐渐吸纳了地方习惯法、教会法、罗马法与自然法等各种法律中的学说、技术,从而形成了普通法强调理性均衡(balance of reasons),强调多种法律渊源的技艺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法发展过程的“理性化”本身就是一种“司法理性”意义上的理性化,即作为程序技术核心的技艺理性的发展,而不是象后来欧陆国家通过罗马法的继受进行的法典编纂化运动一样,是一种立法理性逻辑下的发展。[288] 这一点是普通法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正象著名法律史学者密尔松指出的,“在普通法发展过程中,没有计划,这一点甚至比通常法律史学家有时认为的还要突出。相反,没有计划正是进步的一个条件”。[289] 不过,在与其它法院进行的竞争过程中,“普通法”的法院,由于程序稳定,能够保证执行,得以吸引更多的案件[290],不断提高王室法院的地位,还促使许多其它法院也采用“普通法”,从而逐步促进了普通法的发展。而相对来说,普通法的这一扩散过程,同时也是普通法吸收其它法律的过程。
经过亨利二世和其后的爱德华一世的改革,英国法的发展以一种英国特有的方式,逐渐与国家治理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而适用所谓“普通法”的王室法庭,逐渐取代了以往主要借助习惯法判决的地方法庭,这不能仅仅理解为集权的治理取代了地方性的自治,而是具有更为复杂的意涵。一方面,普通法的发展使治理超越了国王可见的身体,通过治理的超人身化实现了治理的例行化。以往,“国王在哪里,法律就在哪里”。[291] 而无论是设立在西敏寺的固定法院,还是涉足英格兰全境的巡回法庭,其最初的目的都是使整个王国的统一治理能够超越国王的具体身体的限制。[292] 这些措施,使法院作为司法制度,逐渐摆脱了作为行政制度的御前会议的支配,,得以形成稳定普遍的“普通法”。这也是王室法院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案件的原因。而另一方面,“普通法”意味着通过法律的治理逐渐取代了地方社区解决纠纷的方式,成为主要的治理方式。这样治理就主要是“国王的太平”(King’s peace),而不再是“自由人的太平”(mund)或“郡守的太平”(sheriff’s peace),更不是欧陆“上帝之下的太平”(the peace of God)。[293] 因此,通过普通法,英格兰,实现了治理的“跨地方化”和国家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完成了治理的普遍化,从而逐渐向所谓现代治理方式迈进。
或许,“金雀花改革”对于普通法理性的形成来说,其重要意义就在于,与后来欧陆民族国家主要通过行政长官的设立进行治理相比,这种王室法院的治理,是一种所谓连续性的,低调的治理,一种波兰尼所谓“有节制的干预政策”。[294] 而且直至18世纪,由于在英国由政府机关进行的行政治理始终是非常薄弱的,治理任务一直交给法庭。这与德意志的情况有很大区别,在德意志,一方面是中央力量始终很薄弱的“德国式的自由”,在德国同时存在各种自治力量,尤其是各种自治城市,而另一面却是这些自治区域内采用“治安国”这样巨细靡遗的治理方式。 [295] 英格兰这种“弱国家”借助司法手段完成治理任务,对于普通法的“内在视角”的技艺理性的发展,有持久的影响。而从治理的角度来看,通过“普通法”进行的中央权威的治理,也并没有取消地方自治。中央权威的行政治理,地方的自我治理与“普通法”法院系统的自主治理,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所谓“英国式自由” 的主要特征。因此,与其说奠定普通法“法治”基础的“金雀花改革”,是基于集权化或(立法)理性原则,不如说是基于例行化、科层化和专门化。[296] 韦伯为了证明普通法的理性程度较低,曾经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令状,另一个是陪审团。然而,正是在普通法中占据中心地位的这两项程序技术中,鲜明地体现了普通法是如何通过例行化来实现治理方式的超人身化和跨地方化。
令状是中世纪英国法律教育的首选课程。[297] 它最初来源于盎格鲁-萨克逊诸王的行政令状。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得以司法化。由于在普通法的早期发展阶段,王室法院仍是一种例外的司法形式,主要是提供司法补救的手段,或者用来迅速恢复法律和秩序。随着令状的日益司法化,令状也摆脱了以往与国王的人身化权威联系在一起的随意性特点,避免了发布令状时国王流于偏听偏信的专制问题。因此,令状的司法化可以看作是对旧的补救措施,对私人抱怨的王室干预进行了司法化。[298] 司法化的令状,往往与法律诉讼的具体程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突出体现了普通法的司法理性特点:程序制度先于实体法。[299] 同时,这种令状的发展,使各种案件越来越与中央司法权威发生关联(购买令状),而同时随着案件越来越向适用普通法的王室法院倾斜,原有的社区司法与封建性的领主法庭及其所适用的地方习惯法或封建法律,或被吸收到普通法中,或逐渐萎缩。[300] 此后,直至16世纪末17世纪初,普通法的主要著作,无论“格兰威尔”(Glanvill),还是“布莱克顿”,探讨的都是令状及与其有关的程序问题。在 1534年时,一位普通法法官断言,“令状是整个法律依赖的基础”。[301]
如果说,中世纪普通法的学生上的第一门课是令状,那么第二门课就是抗辩。从18世纪末开始编纂的年鉴(Year Books),主要内容就是有关法庭抗辩的内容。而普通法的法庭抗辩是与陪审团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陪审团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他们不是上帝,“上帝不需要人来告诉他适用何种规则,或请求来显示其理性”,但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却需要。正是通过面对陪审团进行的讨论,从而促进了普通法的逐渐理性化。[302] 普通法对案件特殊事实的关注,也来源于面对陪审团进行的抗辩过程。[303] 与令状一样,陪审团最初并非要提供司法方面的正当程序,更谈不上是什么“自由的堡垒”,而只是中央权威利用社区司法的形式,来获取有关案件事实的取证方式,是一种“国王的太平”的保障手段。[304] 因此,陪审团的早期形式与今天相去甚远,理想的陪审员,并不是不认识诉讼当事人的陌生人,而恰恰是他的社区邻居,法庭借助他们的个人事实,来进行审判。经历了长达五、六个世纪的发展,陪审团才从依赖个人知识的社区目击证人,发展成为仅对正式呈交法庭的证据中的事实加以判决的现代意义的“陪审团”。 [305] 作为普通法的正当程序的核心,“陪审团”的发展历史,展现了一个同时结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力量的普通法形成过程。在普通法的发展中,就不仅能够听到国王的声音,同样也能听到所谓“民众的声音”(vos populi)。因此,作为英国的民族法,普通法能够利用地方习惯法,建设整个国家的习惯法。当普通法法官强调“英格兰的普通法…不过是王国的共同习惯” 时,他也同时在强调这种习惯的好处就在于他是来自所谓“民众”,而非国王制定的。[306] 这也是普通法法官和律师为普通法作为一种“非书面法”(leges non scripta)骄傲的原因。[307] 从全欧的角度来看,在13、14世纪,欧陆与英国一样,也在力图发展一套以法律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为核心的“普通法”(ius commune)学说,这种所谓“普通法”一方面,试图运用法律来约束君主的权利,具有宪政的立法理性取向,另一方面又强调借助程序来对诉讼者权利的保护,体现司法理性的特点。[308] 不过,我们已经指出,只有英国通过民族法实现了这一点,而欧陆却要到18世纪以后,借助罗马法的继受来完成这一过程。但是这时,“普通法”的司法理性与宪政意涵已经为绝对主义倾向的民族国家的国家理性和立法理性的结合所压倒。欧洲各民族国家借助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地推行罗马法,也更多是查士丁尼时代的罗马法,正如韦伯所论述的,这种罗马法与科层权威紧密结合,并日益为法学家的法和立法机构的实定法左右,成为立法理性取向的法律,强调逻辑的形式理性,具有浓厚的庇护色彩,而逐渐丧失了宪政意义的取向。而英国的普通法,尽管利用了罗马法和中世纪法律的各种法律技术与自然法的某些观念和技术,但却在法官的“宣示论”之下,成为司法理性取向的法律,强调在经验和传统中逐渐形塑的技艺理性。许多研究普通法的学者发现,这一过程却与罗马法早期的发展具有惊人的类似。 [309] 正如韦伯早已指出的,导致普通法与大陆法这一重大差别的关键因素就是英国与欧陆在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方面的差异。
(2)法律的自主性与治理的超人身化:法律职业的兴起
历史学家早已指出,律师在形塑整个欧洲现代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10] 而这一点对英国来说,尤为适用。正如一位观念史学者所言,普通法的律师,比任何其它职业对英国政治生活的影响都更为巨大。[311] 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普通法治理的发展,是通过超越治理的人身化和地方化实现的。这种发展为法律本身的自主化提供了条件。王室法院制度、令状制度和陪审团制度,在这一过程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发展仍是法律职业的兴起。
最初,主持王室法庭的法官,和后来欧陆的情况一样,也主要来自“公务员”。但从12世纪中期到14世纪末的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伴随着王室法院的发展,法律诉讼程序的技术化与复杂化[312],使普通法法庭日益由专门的法律专家,而不再是政治官僚来充当法官。而法律代表(representation)制度的发展,则促进了律师的发展;而且随着法律程序的复杂化,在13世纪末形成了法官从高级律师中遴选的惯例。这样,法律的集中化(centralization)就与法律的专门化和专业化结合在一起[313],共同推动了独立自主的法律专家群体的形成,这一群体逐渐在英国社会中占据越来越高的地位。
当然,英国普通法的律师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他们发挥作用的方式,与英国法的司法理性形式的治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法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体现在英国的律师职业的构成上。直至16世纪,普通法律师,和绝大多数现代职业的早期先驱一样,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完全“制度化”。一方面,长期以来,普通法律师一直面临来自教会教士和民法律师的竞争。另一方面,在普通法法律职业内部,既有与地方事务有密切联系的半职业人士,也有与王室法院(特别是各种上述法院)联系在一起的具有较高声望和巨大诉讼收益的高级律师的地位群体,整个律师界划分为复杂的层级关系。其核心是一批制度化的律师,构成了法律职业相当稳定的核心,而外围则由许多边缘性的法律从业人士构成。[314] 从法律的发展来看,高级律师的作用当然不可忽视,正是他们的判例,收入了各种法律报告中,成为先例,从而构成了普通法法律原则的核心。而且由于相对集中、封闭与密切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高级律师,尽管人数不多[315],但作为普通法职业的核心,对政治生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普通法法院的法官,也主要是从这些高级律师中产生,而不象大陆国家中从行政官员中招募,这些都保证了普通法无论在内在理性,还是外在的职业角度方面都能维护法律的“封闭性”。
不过,英国法律职业中的边缘人士,各种地方法律从业人士,半职业性的法律专家,在普通法形塑英国社会的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尽管英格兰以王室法院为核心的“法治”早在12世纪就开始得以发展,但直至17世纪清教革命时代,英国的法治仍然是一种低调的“根植性治理”。与法国相比,英国的大量地方性律师,并不是在中央权威的直接命令下行事。法律对英国的渗透,恰恰是通过这些在职业等级制中处于较低地位的律师,通过提供法律咨询,起草合同等日常法律事务,将普通法的理性与整个英国政治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将少数几十位高级律师与法官的工作,加以扩展,从而形成一种与大陆法相区别的独立的法律制度。
从治理的角度看,这种法律职业最初是在延伸国王的人身化权威的过程逐渐发展的。不过,因为法官和律师并不具有国王的人身权威,他们需要借助法律的权威来维持自身的权威,维持法律的稳定性,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和律师慢慢形成了自身的技艺理性。而这种技艺理性,正是法律职业自主性的内在基础。
正是这里,我们触及到了所谓“普通法心智”中最具争议的部分。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波科克指出,普通法律师和英国人,都强调普通法是“超出记忆的”,好象它从古至今都一直统治着英国人民,律师则运用这种观念来对抗强调制定法和国王敕令的绝对主义倾向,这突出体现了伪历史的“普通法心智”的特点,这一观念构成了英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基础。[316] 在某种意义上,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普通法“没有作者”[317],这正是普通法作为司法理性,与信奉实定法的立法理性之间的差别。因此,在普通法法官和律师的眼中,“法律是超出记忆的,而没有立法者”。[318] 不过,从治理的角度看,无论是对“诺曼征服”意义的否定,还是将普通法的历史追溯到罗马统治之前英格兰古王的努力,都并非单纯是神话或意识形态的编造,而不如说就是普通法的技艺理性在治理“过去”上的体现,一种治理历史的技术。因为所谓的“普通法心智”中,历史不是作为历史证据使用的,也就是说,不是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而是一种“法庭历史”(forensic history)。运用这种“法庭历史”,普通法律师能够抗衡国王的所谓“自然理性”和赤裸裸的权力,同时建立了法律自身的中立性,使法庭内外的人们都能相信,法院做出判决的方法是中立的,因为普通法的“起源”超越了人们可以发现的任何政治斗争的范围,因此,普通法“超出记忆”,超越时间的“历史”或者说 “神话”恰恰是捍卫普通法的“完善理性”的“第一原理”。[319] 通过这种所谓历史感的非历史用法[320],实现了对历史的治理,使普通法能够超越政治权威的“有限时间”,建立中立和超越色彩的法律。正如清教革命期间,一位普通法法官所言,“政府沉浮兴替,而普通法则永存”。[321] 从而使普通法能够在政治变革中,保持稳定性和开放性,并利用时间累计的各种诉讼案件,实现普通法的发展。[322] 从前面我们谈及的柯克与詹姆斯一世的对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普通法的这种“法庭历史”,正是普通法法律职业的基础,它使法官和律师从最初延伸和拓展国王的人身化权威的工具,摇身一变,成为约束国王恣意权力的宪政机制。普通法的“法庭历史”成了所谓“自由的法理学”。[323] 这大概正是英国在现代国家治理历史中的重要意义。
(3)普通法理性作为政治的“普通话”:法律教育与“英国自由”
对于普通英国人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律师职业都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声望,并对英国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固然是因为法律职业往往能够使一个人有机会获得高级官职,但更为普遍的是,法律教育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生活的基础教育。不仅用来保障私人权利,而且成为英国政治思想的公共语言。
普通法的法律教育与大陆法的法律教育之间的差异,对于两种法律制度之间的分歧来说,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事实,早已为法律史学家和法律社会学家所熟知。韦伯特别强调了英国法律公会的教育方式对于培养强调技艺的普通法理性的重要性。而相比来说,欧陆则主要借助大学的正规法学教育,来培养法律职业人士,这种正规法学教育,受罗马法传统的深刻影响,特别关注法律在逻辑分析意义上的形式理性。
不过,法律教育不仅对两种不同的法律理性(强调逻辑性的立法理性与强调技艺的司法理性)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英国与欧陆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后者,尽管受到较少的注意,但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早期都铎时代的教育理想,就是除了要学习宫廷礼仪、军事训练以外,士绅与市民阶级的子弟同样要接触人文与法律。[324] 在14、15世纪逐渐形成的律师公会(inns of court)中,这些子弟不仅接受法律教育,而且通过共同生活,培养未来政治活动的礼仪与社会关系。法律史学者估计,大概英格兰三分之一的士绅都曾经参加过律师公会的学习,而且在伦敦的四大律师公会中,绝大多数的学生并不打算日后专门从事法律职业。他们主要希望在这里除了获得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之外,还获得礼仪等方面的知识,从而适应未来的政治生活。因此,这些律师公会的教育,对于英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以及文化和思想方面来说,至少在18世纪前,其影响可能并不亚于牛津与剑桥,甚至可能更大,所以被称为英国的“第三所大学”。[325] 也许正是从这种法律教育的角度来看,我们才能说,普通法的发展形塑了英国社会的性格。[326] 托克维尔当年曾经指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要追溯到法国的“文学政治”,因为法国的文人与英国不同,从来未曾置身日常政治中,这反而使他们形成了运用脱离“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从抽象和普遍的原则出发,来探索政治体制基础的“文学政治”。[327] 正是在这里,我们触及了英国政治思想与制度的关键环节,以及普通法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正如法律职业在英国与欧陆同等重要一样,但却以不同形式发挥了作用一样,法律教育在欧陆也同样重要。社会的一般知识阶层也同样受到正规法律教育的广泛影响。不过,欧陆的法律教育主要是大学以罗马法为核心的教育,而英国普通法的法律教育则不同,这种教育主要是一种实践技艺的教育。如果说在整个欧洲(也包括英国的大学: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法学教育是培养立法者的科学的话,那么英国的律师公会,则是传授作为司法理性核心的技艺理性。在律师公会中,很少学习正规的法学课程,而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令状、法律分析与争辩等复杂的程序技术上。正如我们前面分析普通法的技艺理性时所指出的,这些复杂技术,正是围绕具体实践权利的方式和法律原则来不断演练的。因此,英国的法律教育,不是大学中抽象权利的逻辑学,而是一种具体权利实践的修辞学。所以,对于诸多在律师公会中求学的青年人来说,他们正是通过普通法的法律教育,逐渐掌握了实践权利的技术,使普通法的理性成为整个英国政治生活的“普通话”。对于英国人来说,政治不过是法律的一个分支,法律是谈论政治的主要方式。正如17世纪的一位出版商所言,“通览法律,是一个绅士最大的光彩”。[328] 正是这种英国式的“法治”[329] 培养了托克维尔眼中英国政治生活的特点,对日常政治的复杂性和细节的参与和重视,而不是象立法者一样,迷恋抽象性的话语。在边沁对布莱克斯通尖刻批评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两种“心智”之间的深刻差异。[330] 在16世纪获得巨大发展的普通法,濒临世纪末的时候,面对英国正在兴起的变革观念开始受到了日益严厉的挑战。托克维尔后来描述大革命前法国的情况大概也同样适用这时的英国:“现实社会的结构还是传统的、混乱的、非正规的结构,法律仍是是五花八门,互相矛盾,等级森严,社会地位一成不变,负担不平等”。 [331] 在批评者的眼中,这种混乱的法律,就是一个“耳目闭塞的暴君”。[332] 面临改革的普通法有两种不同的选择。[333] 培根起草了25条法律公理,希望运用“理性的一般命令来贯穿各种不同的法律事务”,赋予法律以一贯性,从而能够“治愈法律中的不确定性,它是当前我国法律面对的最主要的挑战”。[334] 柯克同样认为普通法需要系统化,不过他采用的形式不是培根的法律公理体系,而是通过在法律年鉴中添加新的案例,编纂更完善,案例更“现代”的法律报告来为普通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理性化的基础。在柯克看来,一个普通法的律师,只有通过长期浸淫在这样的案例报告中,才能掌握普通法的技艺理性,而希图借助一般公理来进行的法律理性化,并无助于增加法律的一贯性。
哈勒的一段论述精确地阐发了柯克的观念:“英格兰的普通法(Common-Laws)比其它法律都更具特殊性,而且尽管比起其它法律,它数量繁多,缺乏条理,需要花费更常的时间来研习,但是这些都有巨大的好处作为回报,即英格兰的法律能够防止法官的恣意,这样使法律更具有确定性,对于那些提交给它判决的事务来说,也更适用。一般性的法律(General Laws)确实非常全面,易于掌握,容易消化成为有条理的方法;但当这种法律面对特定的法律适用过程时,它们却没有什么用,给偏见、私利和各种各样错误适用法律的考虑留下了过大的余地;这种法律与道德学家的共享观念没什么两样,即使当彼此争辩的各方都对这些共享观念完全达成一致,但是面临有争议的特殊事例时,从这些共享的观念中,每个人都可以推导出与他们自己的各种欲望和目标相相应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彼此却极度矛盾。因此,英国治理的智慧和幸福一直就不在于一般性的东西,而在于运用与所有特殊情境相吻合的特殊的法律,来防止恣意与不确定性”[335]
(4)清教、圣公会与普通法:如何治理良知?
从全欧洲的角度来看,普通法在16世纪末面对的挑战,不过是宗教改革以后整个社会秩序面对的“17世纪的总危机”的一个预兆。[336] 在这个试图同时追求所谓“总体性”、“绝对性”与个人信仰自由的时代中,普通法面对了来自清教、天主教与圣公会种种不同的秩序观念之间的尖锐冲突的挑战,在迫害、偏见与中立、宽容之间左右摇摆。而发生在清教与圣公会之间的激烈争执,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宗教问题,而涉及了伦理理性化与社会秩序理性化之间的复杂纠葛,直接关系到了我们这里讨论的韦伯社会理论与“英国法”的核心问题,也提供了一个我们最后返回韦伯思想的绝佳路径。
自16世纪中期,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交恶,王权与教会之间的斗争为新教学说在英格兰的传播提供了机会,从而使宗教改革运动能够逐渐在英国赢得了官方的支持,借助国王与议会的立法活动推行开来。到伊丽莎白女王统治后期,新教已经取得了所谓“压倒性的胜利”,成为英国的“国教”。[337] 不过,伊丽莎白时代建立的“宗教和解”,实际上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兼采新教的学说与天主教的教职制度的一个中间路线。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是独特的,就在于它努力在单独一个国家的疆界内创造空间,来容纳保守…和激进”。[338] 比起大陆宗教改革后立场更为“鲜明”(precise)的教会和罗马教会,英国的国教显得态度含糊暧昧,学说与实践自相冲突。不过,正是这种奉行中间路线(Via Media)的宗教“和解”,使教徒自行处理的问题(adiaphora, indifferent things)有远为宽泛的空间。[339] 不过从16世纪末到查理一世即位之后,和平化的“宗教-政治-法律”局面同时面临了来自鲜明立场的“清教”激进分子与罗马天主教廷两种极端路线的潜在威胁和现实压力。圣公会的宗教学说和实践与这些极端路线之间的激烈冲突,直接触及了终极价值、现世政治与法律治理之间的冲突,而争执的焦点就是宗教与国家,良知与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
受加尔文学说影响的英国清教徒认为,现有的政治与法律秩序不仅混乱不堪,而且与基督教徒的自由相冲突,是一种没有内在秩序的强制秩序,而他们倡导建立的新秩序,则是一种与个人良知和意志密不可分的秩序。[340] 因此,在清教徒中的激进分子看来,真正的教会要完全听从“上帝之言”,这意味着要建立一套基于“选民”的自愿服从的共识秩序。而这种“衷心”的、出于个人意志的服从,是建立一种新的共同体的基础。用清教思想家的话说,教会应该成为“良知的受托人”(the depository of the conscience)[341]。因此,上帝的新秩序与传统圣公会或伊丽莎白女王的国家秩序不同,这种新的秩序依赖的不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服从。这种围绕良知建立的秩序,其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成为我们自己的法律;我们必须在没有外在制约的条件下,出于自身意志这样做,自由地产生对上帝意志的服从”。“每个人都足以成为自己的治理者,而所有人都服从上帝”。[342] 共识是这一秩序的主题,《圣经》中的“上帝之言”是他们的法律,而其核心环节则是全面治理一个人的良知。
早在加尔文那里,伴随宗教改革产生的这种新的“良知的治理”就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倾向:政教分离的个体化与政教合一的信条化。[343] 而当清教徒与圣公会进行论争时,“良知治理”的这两种背道而驰的倾向都体现出来了。一方面,新教强调基督教自由与自愿秩序的学说,可能会推动政教分离,使国家与教会构成两种不同的秩序领域,国家继续施行它的强制秩序,而教会则完全摆脱任何具有强制色彩的世俗政治秩序的问题,只关心信徒的内心秩序。但另一方面,在清教的批评家眼中,英国面临着日内瓦化(genevating)的危险,因为清教徒渴望建立的不是一种多元取向的自由社会,而是一种上帝主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自由并不属于此世的罪人,而属于全能的上帝。[344] 新的秩序的基础并非原子式的孤独个体,而是一种有机的共同体。人的内在完善(inner integrity)与选民自愿组成的共识共同体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只有成为这一新的共同体的成员,才有可能获得救赎。因此,当新教的“良知治理”从个体化的层面逐渐社会化,当每个清教徒所听从的内心审判的法律,成为共识共同体的法律,清教徒共同体的政治化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危险:一种总体化的良知治理。在这样的新秩序图景中,国家服从上帝的新秩序,施用严刑峻法,以便“将尽可能多的良知转变过来”。[345] 因此,清教徒眼中的“基督徒自由”最重要的因素,倒是纪律,而新教教会的目的就在于推行这种纪律。[346] 近来许多“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在早期现代,清教徒倡导的这种自由观念,与现代的世俗化的自由观念有很大差别,它的核心意涵并非自主,倒更多是为了听命上帝的意志,通过摆脱较低的世俗权威,来满足个人对更高权威的义务。[347] 不过,正如韦伯当年对清教徒的讨论一样,这种对上帝意志的服从,如果摆脱了潜在的“信条化”的危险,倒同样有可能培育一种尊重个人良知,宽容异端的自由观念。而且恰恰是这种对良知的个体化观念,为所谓现代自由主义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用一位试图矫正“修正主义”偏颇观点的历史学家的话说,“最热诚的清教徒,通过他们原始的热忱,得出了某种非常突出的自由派的结论”。[348] 与清教在教义上针锋相对的天主教,自玛丽执政之后,就一直是英国政府的“眼中钉”。而天主教为了在英国传教,则借助中世纪晚期以来的道德决疑术的技术发展了一套迥异的良知观念,这套观念特别与所谓“内心保留”(mental reservation)的学说连在一起。这一学说认为,当天主教徒,特别是传教士面对英国政府当局提出的各种宗教信仰问题时,可以利用“说半句,留半句”(mixed speech)的方式,以含糊的措辞,隐瞒事实真相,掩饰自己的身份。从而将“内心的声音”与“口舌的声音”区分开来,前者面对上帝,而后者则用来应付世俗权威。[349] 在天主教的决疑术训练中,个人的良知,变成了一种详尽斟酌的技艺,但它与个人的公共事务形成了鲜明的分离。在人的外在的公共面目与其内心深处的良知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世俗的法律,比起内心的良知,同样处于劣等的地位。
而对于圣公会来说,它力图在清教的极端主义与天主教正统似乎逃避道德规范和法律规则的决疑术之间找到一个可能性,既避免良知的内在化、私人化,同时也避免良知的制度化和外在化。[350] 因为,从圣公会的学说来看,清教学说,特别是带有“信条色彩”的清教学说,忘记了“精神的王国”是超验的,因此绝对不能制度化。所以,希望借助共同体自愿达成的共识,将每个人内心审判的法律,变成社会的法律,就根本不能成立。坎特伯雷大主教威特基夫特指出,“法律的理性,就是因为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所有人都达成一致是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一种自然的倾向是彼此意见分歧,不能统一意见,如果每个人都能接受这样的共识,就根本不必有法律或秩序”。[351] 英国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圣公会主教胡克(Richard Hooker)也认为,良知完全属于个人的事务,因为它与超验的世界有关,而与现世的政治政治生活无关。[352] 诉诸圣经来代替世俗法律,“不过是在应该听从公共法律的时候,却听命私人理性的法律”。[353] 因为,在圣公会的观念中,教会涉及两种治理,一种是可见的治理,它是外在的,一种是不可见的治理,它是精神的。人执行的只是可见的治理,由外在的纪律、教会中的各种礼仪构成,只有上帝才有权能治理人的良知。[354] 因此,圣公会与清教之间争论的关键就在于,救赎究竟是一项个人的,彼岸的问题,还是一种集体的,现世的事务?而答案的核心就是如何治理良知。良知与法律的关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触及到了整个现代社会面临的价值多元与程序正义的问题。
“良知”是晚期中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观念,特别是在对普通法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的阿奎那的思想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中世纪的哲学家那里,良知被看作是一种通过自由选择,与特定行为的判断有关的行为,因此是可能犯错的,这与不可能犯错的,与自然法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良心” (synderesis)区别开来。[355] 在这方面,圣公会的学说与普通法的理论传统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
早在15世纪,“良知”的观念就构成了英国法的一些理论家的重要概念。圣日尔曼(St. German)在著名的普通法与神圣法的学者之间的对话中就指出,“良知就是一种将一般性的规则转化为在特定情境下可以遵循的专门的行为规则,是…一种应用知识的方式”。因此,在许多时候,普通法需要运用良知来形塑其结论。[356] 因此,在普通法的法律学说中,良知并非某种主观的道德或不道德(right/wrong)。象圣日尔曼屡次指出的,良知必须以法律为基础。[357]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良知观念与16、17世纪盛行的决疑术中的“良知治理”有着微妙的一致性。尽管它不承认良知是潜伏在内心深处的观念,但两种良知观念,都特别强调良知是一种“或然性的知识”[358],良知并非“良心”,并没有确定性的保障,因而需要通过对各种复杂的良知案例(cases of conscience)的反复斟酌,才能掌握相关的技术。[359]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普通法的司法理性,正是运用并发展了与决疑术中对良知案例的斟酌有关的技术。[360] 不过,普通法尽管使用了与决疑术类似的技术,但它却并不是一种天主教决疑术形态的“良知的治理”,它针对的焦点,是人的行为举止。所以,当年柯克法官在审判天主教耶酥会的烈士索思韦尔(Robert Southwell)时,当后者诉诸天主教的“内心保留”的学说来为自己辩护时,柯克断然反对,“如果接受这样的学说,它就会取代所有的正义,因为我们是人,而非神,只能根据〖人的〗外在行动与言辞来做出判决,而非根据他们隐蔽的内在意图”。[361] 而普通法的这种类型的良知治理,在圣公会的一些学者笔下,同样有所呼应。在被誉为“我们国家,也许是所有国家最优秀的决疑术专家”桑德森(Robert Sanderson)笔下,良知被界定为“一种实践智慧方面的能力或习惯,能够使人的心智借助一种推理过程,将它所拥有的光应用到特殊的道德行为上”。桑德森的定义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在于,首先它强调了良知是一种习惯;其次,良知作为“知识的连接”(con-science),就是将(有关律法的)普遍性知识与(有关实际发生的事实的)特殊性知识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桑德森看来,良知是围绕一套实践知识形成的习惯,而不是一套一般性规则。最后,与天主教的良知决疑术不同,也和激进的清教徒的良知共同体不同,桑德森要求区分三种行动领域,即听凭命令的(commanded),非法的(unlawful)和无关善恶自行决定的(indifferent)[362],基督徒的自由只与第三种行动领域有关,因此,任何与世俗法律相抵触的非法行为,都不是自由,“上帝没有给我们任何非法之事的自由”。[363] 事实上,正是这种良知治理的观念,构成了普通法治理的内在核心,特别是普通法有关“合理”(reason)的观念。在普通法中,所谓“合理”,用柯克爵士的话说,就意味着合乎“衡平与好的良知”(equity and good conscience)。[364] 这一观念直至今天仍是普通法法律推理技术的核心,在普通法的法官看来,法律就是要“防止以违背良知的方式得益”,这也是普通法强调“常识”的基本意涵。 [365] 因此,普通法的治理,针对的焦点是个人的外在行为,尤其是那些有可能冒犯良知的行为,而它将更为根本的“良心”问题留给了上帝和个人自己。也就是说,普通法的司法理性,并非教化式的“皈依”手段,但却更关注于实践习惯的形塑,这与我们在前面发现的普通法内在视角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366] 普通法中的衡平女神,尽管同样又聋又哑,听不见个人内心的声音,但却能看到每个人的行为举止。[367] 所以,在普通法的法庭上触及的“良知”,即使在衡平法院中,也并非清教徒意义上的良知。而仅仅是一种“市民的或政治的”良知。正如一位普通法的法官所说的,“法庭的良知是职业性(professional)的,而非信条性(confessional)”。[368] 而且普通法法官与律师对衡平法院的前身,大法官法庭(the Court of Chancery)之所以充满怀疑,就是因为这一法庭自称是“良知的法庭”,妄图直接触及每个人的良心,但在普通法律师眼中,最终不过变成了恣意的法庭。
普通法的习惯倾向的“良知治理”,是普通法的“法治”与德国法治国的一个重要分歧之处。从法治国的谱系来看,法治国中国家的角色深受德国由王公贵族推动的第二次宗教改革运动中“信条化”倾向的影响。德国历史学家谢林指出,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正是这种信条化,通过在宗教与政治、国家与教会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从而促进了早期现代国家的建设与运用纪律进行控制的主体化技术之间的紧密结合,导致在欧洲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前所未有的一体化。“信条化”与“治安国”结合在一起,使国家既充当日常生活无微不至的守护神,又担负起每个人良知的牧领者(pastor),从而推动了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法治国试图摆脱国家作为日常生活与个人良知的警察形象,但国家自上而下推动自由的形象,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信条化国家的万能色彩。[369] 在这样的国家中,正如一位探讨黑格尔的“伦理国家”学说的德国学者所指出的,“由于国家――作为展开来的国家――从自己那方面来说,代表着自己的客观内容,在其安排和是(被假定为伦理-理性的)法律中是成为现实的理性,因此,不存在与它相对立的偏离良知的权利”。[370] 个人的良知(实际上是“良心”)最终与国家的伦理合为一体,国家成为个人良心的看护者。
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的普通法面临同样的危机,但普通法回应这一危机的方式,却没有采取运用深入个人良心的“总体化-个体化” 的方式来建立秩序,而是沿循了封建法团秩序中的一些程序化、自主化的框架与心态,以被动和自助的方式来治理个人良知与日常生活,其理性化充分借助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而从治理的逻辑与个人的伦理理性化的关系看,正是圣公会与普通法采取的这种有限的、外在的良知治理,才使无论哪一种教派的信徒,都可以依其自身信仰来追求自己的绝对化的,毫不妥协的价值(尽管历史事实并不象我们描述的这么“美好”)。而德英之间的区别也许暗示了理性化所遵循的不同的道路。
当18世纪这个“立法者的世纪”最终取代了17世纪这个“良知的世纪”[371],普通法的理性,和决疑术一样面临了衰败的危险。在这个霍布斯的时代,一种新的“确定性政治”逐渐兴起,来管理这个“诸神之争”的世界。[372] 面对政治治理、政治文化乃至大众心态上的绝对主义,即使在英国,普通法也不免象决疑术一样倍受猜疑,面对实定化日益强大的压力。其司法理性的逻辑,受到立法理性和议会主权的限制和遮蔽,逐渐在英国政治生活的公共话语中销声匿迹,只是以扭曲的方式保留在诸如柏克这样的保守主义的著作中。也许正如这位自诩拥有 “普通法心智”的继承权(但实际上也许不过是一个“私生子”)的辉格党的善辩之士所言,这些批评者“将经验鄙夷为文盲的智慧,至于其他东西,则他们已经在地下埋好了地雷,它将在轰然一声的爆炸中粉碎一切古老的规范、一切先例、宪章和议会的法案”。[373] 强调权利的实践技术的技艺理性,最终沦为“意识形态政治”的纷争格局中一种反话语的话语,倒颇有些“理性的狡黠”的味道。也许,培根的“自信”是有道理的。谁又知道,在柯克迷宫般的案例报告与培根清晰透明的“法律公理”之间,未来会把它的赌注押在哪一方呢?
五、回到韦伯:伦理理性化与社会理性化的法律关联
(1)重提问题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就已经指出,在韦伯有关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的复杂分析中,个性与培养个性的天职,是二者之间关联与紧张的核心环节。不过韦伯认为,现代人所追求的已经不再是一种完美的个性。这正是韦伯与当时德国盛行的浪漫主义的“伦理文化”与“个性崇拜”之间的巨大分野。在韦伯眼中,洪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代人的个性,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天职中去寻找。
不过,尽管韦伯认为人的个性不再梦想完美,但却仍然要努力趋于“绝对化”和“总体化”。清教徒毫无宽佑余地的一丝不苟的伦理,仍是韦伯心目中的“榜样”伦理。[374] 因为,在韦伯眼中,个性意味着人的尊严,它是我们的最终价值。说一个人具有“个性”,就意味着这个人要依照某种价值对他的整个生活进行全面的组织。 [375] 换句话说,只有伦理理性化才能使一个人获得“个性”,在韦伯看来,这也是自由的意涵所在。而对于现代性的社会理论来说,韦伯的这一论述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不仅揭示了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这种自由的伦理理性化,最终推动了社会理性化的发展;而且在理性化的持续发展中,只有自由的伦理理性化,才最终能够担负除魔世界中社会秩序的理性化。
可是一旦我们将韦伯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发现的“新教伦理命题”带入政治与法律的支配社会学领域,我们就会发现,社会理性化与自由或伦理理性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丧失了,问题变成了如何在科层制的例行化这一社会理性化力量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挤压下,维持一点微弱的自由空间,使我们能够探索我们的个性,捍卫我们的尊严。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韦伯社会理论的“英国法”问题的实质正体现了韦伯理论的这一基本困境。
不过,如果把新教伦理命题看作是一个法律社会学或者说支配社会学的问题[376],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困境在现代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些深刻根源。从这个角度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发现的,实际上就是新教的“良知治理”中的个体化倾向,即政教分离的倾向。从这个角度看,新教徒的经济活动,是一种自主乃至孤独的救赎事业。经济活动并不是国家治理的直接对象,而倒象是在普通法中的“自行处理的行动领域”一样,更多留给个人之间的契约来保证。而韦伯对美国新教教派的研究[377],实际上是发现了教派在这方面的重要意义,一种自助式的“法律秩序”,建立信任与“秩序”的自主方式。 [378] 这种“践行的预定派”(experimental predestinarians)尽管试图对生活进行全面的伦理理性化,但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的“自主秩序”,却在政治上具有潜在的危险。几乎同样这些清教徒,在政治上,却梦想从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出发,建立一个真正具有可见的虔诚(godliness)的可见教会,希望运用一套带有侵犯色彩的精神纪律,来在虔诚者与不虔诚者之间建立截然的划分。[379] 因此,入世禁欲主义,在政治上,并不象经济上那样,可以与现有的政治权力结构相妥协,而是往往发生尖锐的冲突。[380] 但一旦个体化的“良知治理”政治化,也就是说将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延伸到政治领域,其危险就是世界的再次着魔,意味着整个社会秩序的“总体化”。这时,某个“共同体”往往开始具有总体化的面目,充当“良知的受托人”,运用例行化的治理手段(尤其是法律),通过管理人们生活,来实现社会正义,引导人们趋于自由,甚至希望塑造“新人”(new man)。个体化与总体化的结合,使教会、国家,或者民族,不仅成了社会福利的管理人,还是个人自由与个性完善的监护人。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与作为信条化国家中的法律精神和科层精神的新教伦理,貌合神离,针锋相对。
韦伯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恰恰基于这一点,他强调了法理权威的形式理性化,并对各种“实质化”的努力深表怀疑。不过,当韦伯笔下 “法律的形式理性化”变成了法学家或立法者手中的逻辑理性运算时,它与普通人生活的伦理理性化之间的关系,变得难以理解。这种对无缺陷的法律规则体系的追求,就象边沁的“万全法”一样,仍然摆脱不了庇护型“国家-法律”的问题域。面对这种“万全法”的“自动售卖机”,普通人注定只是一个法律的消费者,对法律的神秘与强大满怀敬意,只能徘徊在法律的门口,不得而入。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正是德国“法治国”的内在痼疾。
面对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之间的这一僵局,韦伯的选择只剩下社会夷平状态下没有个性和自由的“政治-法律”机器(工具化和例行化的政治)与听任领袖的克里斯玛引导的领袖民主和大众动员的民主(危机化或浪漫化的政治)。无论最终我们选择什么,作为普通人的我们都只能心甘情愿地交出我们的自由活动空间,如果我们曾经有的话。对于普通社会成员来说,自由成了明日黄花,只能在乌托邦的幻想中去憧憬,或者到“黄金时代”的怀旧中去缅怀,而理性化的现实却变成了深不可测的命运,无法逆转。
(2)能动的理性化
韦伯在临终前曾经指出,不同领域可以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图景和目标取向来加以理性化”。[381] 这段话尽管引起了研究者的充分注意[382],但不同的理性化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深刻的关联?不仅韦伯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者同样也没有给出答案。
事实上,理性化的多元性和彼此的张力不仅是理性化的重要特点,还是理性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而这种理性化的“分殊”实际上正是通过依循不同“理性”逻辑的理性化之间的抗衡,形成一种张力关系,推动了整个理性化的发展过程。而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殊性并不在于某一种具体或特殊的理性化,而在于存在这种具有张力的,复杂理性化的发展机制。也就是说,是一种“能动的理性化”。正是这种不同形态的理性化,能够借助或吸纳各种不同发展逻辑的理性化之间的抗衡,建构了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理性化”发展机制,使西方理性主义的历史逐渐变成了全球化的世界历史。[383] 从表面上看,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似乎是英国(或进一步说,“普通法国家”)在经济、政治与法律领域之间在理性化程度上的不协调问题。为什么在英国,具有较低理性化程度的法律并没有阻碍,甚至反而促进了经济理性化的发展(尤其体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和政治理性化的推进(尤其体现在稳定的民主制度中)。许多学者急于在英国的法律中寻找与经济和政治的理性化相吻合的部分,证明其实它们之间的逻辑是一致的,并无矛盾之处。这些做法,恰恰是南辕北辙,对理性化真正的动力机制却视而不见,将韦伯的“亲合力”理论降低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384] 或“工具理性扩张”的理论。
实际上,倒是韦伯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含糊和犹豫,给我们更有价值的线索。在英国,法律的理性化确实没有与经济理性化和政府的科层理性化遵循完全相同的理性化模式。[385] 如果说在德国历史中,“治安国”试图运用统一的“治理术”来塑造经济、政治与法律,“法治国”则试图将政治与法律的理性化置于“立法-行政理性”的一元逻辑上。那么,尽管英国的普通法的形成与延伸国王的行动治理手段联系在一起,但从13世纪到16世纪,伴随着中央权威的“超人身化”和“跨地方化”,普通法日益具有自身的自主性,在16世纪末的所谓“普通法的理性化”过程中,普通法与立法者的自然理性彻底分道扬镳。在16世纪最后十年中,普通法大概比后来边沁的时刻更接近迈向统一理性的可能,如果普通法采用了培根的改革方案,也许普通法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但最终仍是技艺理性压倒了自然理性,为普通法的司法理性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如,哈勒评论霍布斯对柯克的批评时所言,“一个人在医学领域中娴熟的理性,不见得适合政治,而另一个人在数学中驾轻就熟的理性也不见得适合医学”。在哈勒眼中,霍布斯笔下普遍的数学家的理性,比起柯克所说的法律的“完善理性”,倒更象是一种虚构。因为“普遍适用的知识,只不过是一些表面的东西,很少能够深入任何事物的内部”。[386] 无论从内在视角,还是从外在视角看,普通法发展史中通过吸纳特殊性因素,建立普遍主义的动力机制,都是普通法理性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正是普通法的治理,作为一种根植性的,自下而上的治理的特点。而这种理性化,其突出特点就是能动的理性化,而且它的动力机制,是多元的,但又是稳定的(“一贯的”)。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讲,围绕普通法的治理形式,才以最复杂的方式体现了理性化所具有的普遍历史的意涵:即能够吸纳各种复杂、甚至相互冲突的理性力量来推动理性化的发展。[387] 普通法的司法理性,议会后来逐渐形成的立法理性,与以国王为首的科层理性,最终构成了整个英国政治理性化的内在张力。而普通法在复杂的力量格局中的形成历史,使普通法成为运用程序技术容纳多元理性的法律制度,而没有象“法治国”或边沁的“万全法”一样,成为立法数学家手中的尺度。普通法这个“混沌和黑暗的国度”,实际上正反映了普通法中蕴含的理性化与价值、自由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种本质上的可争议性。如果说,不可决定性(indeterminacy)是现代社会法律的真正核心的话[388],普通法对社会多元价值的复杂性、特殊性和相互冲突的尊重及其处理这些问题的技艺理性,正是普通法成为所谓英国式自由的基础和保障的原因。诚如帕斯卡所言,“正义会面临争论,强权却易于识别而又没有争论”。[389] 因此,英国的历史恰恰证明能动的理性化来自彼此之间存在张力的理性化机制。而且正如我们在“论抽象社会”中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同理性之间的颉颃,反而构成了两种系统理性之间的“亲合力”的来源,从而推动整个理性化的发展进程。
(3)伦理理性化与作为斗争的自由
仅靠不同的社会理性化之间的颉颃,并不足以推动理性化的发展。探讨“英国法”问题的诸多学者忽视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作为韦伯社会理论核心的伦理理性化的问题。而恰恰是这种伦理理性化,构成不同系统的社会理性化充满张力的“亲合力”的关联环节。如果说新教伦理提供了伦理理性化的超验动力,那么在“普通法心智”支配下的程序理性的法律制度则作为一个前提和渠道,使这种理性化能够通过程序化的“相互斗争”,“自助”色彩的规则创造、选择与制度化,实现了“价值多元”背景下的个性塑造与社会理性化的二律背反结构。
不过,在一个“除魔的世界”中,这种伦理理性化不是一元性的,而注定是彼此相互冲突的。因此,通过伦理理性化实现的社会理性化之间的张力关系,要比“新教伦理命题”复杂得多。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伦理理性化的“诸神之争”中,政治与法律的社会理性化如何为这种冲突提供秩序的保障,提供足够的空间,同时,在秩序的建构过程中,不仅没有抹煞或取消这种伦理理性化的冲突,而且利用这种伦理理性化的冲突为社会理性化的发展提供动力。
我们对普通法进行的内在视角分析,正是要揭示普通法司法理性在这方面的社会理论价值。因为,普通法司法理性的特点就是通过程序技术来容纳普通人的伦理理性化冲突所提出的权利实践技术的问题。而且,普通法还借助这种普通人的伦理理性化冲突(“疑难案件”),实现了自身(作为社会秩序)的理性化。
不过,面对普通法的这种司法理性的社会理性化,法律行动者的伦理理性化,具有与新教伦理中的一元的伦理理性化相当不同的复杂面貌。普通法的这种司法理性,之所以能够面对社会成员的伦理理性化冲突做出“回应”,正是因为普通法法律职业自身的伦理理性化,在普通法的程序技术中植入了真正的 “天职”要素。而诉讼当事人之所以能够在“诸神之争”的社会中,从自己绝对化的价值立场出发,探索实践自己权利的技术,形塑自身的人格,其前提正在于法官能够借助自身的伦理理性化方式,以一种天职的“有纪律的激情”[390] 来维持法律的“一贯性”,通过法律的程序技术来构建践行自由的技术的空间。因此,法官、律师这些职业人士与诉讼当事人不同形式的伦理理性化,从两个方向为普通法的程序技术提供了内在的动力,使普通法的程序技术,没有沦为工具化或形式化。换句话说,社会成员实践权利的技术是以法律的程序技术为前提,同时又充实和丰富了后者;而社会成员借助这种技术实现的伦理理性化,之所以能够形塑一种绝对化的人格(当然,不一定必然如此),能够发展一种具有超验取向的价值理性的伦理理性化,正在于法律的另一面是法律职业人士围绕法律“天职”进行目标理性的伦理理性化,“一种禁欲主义教导的职业伦理”[391]。这一点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的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的关系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都未能理解,在价值理性和目标理性两种不同取向的伦理理性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依赖和制约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除魔的世界”中理性化与自由的二律背反结构的关键环节。政治的非人格化,社会的抽象化,恰恰需要一种特殊、也许是最强有力的人格来支撑。这就是普遍主义与伦理理性化之间的“亲合力”,韦伯当年面对的各种亢奋的情绪主义、一元性的至善伦理或神秘主义(无论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甚至反政治的),都与政治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未能理解在价值多神论、政治普遍主义和政治-法律的职业人士的禁欲主义天职伦理之间的复杂关系。现代人的个性,正是在破碎与完美之间摇摆,在分裂与整合之间挣扎,同时面对深度自我与表面自我的双重考验,将理性化与自由的二律背反从轰鸣的机器延伸到“机器中的幽灵”。
在这里,哈勒成了一个鲜明的象征形象。作为一个清教徒,哈勒的生平几乎就是英国早期现代史的一个缩影:法律、政治、宗教与科学。 [392] 但面对政府的动荡,革命与复辟,宗教的教派之争,这位韦伯笔下新教伦理的代表——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好友,却始终试图同时捍卫他的宗教生活与他的法律职业。
一方面,哈勒从没有试图让他的法律活动听命于他的宗教信仰。正如我们上面引述过的那些段落所表明的,他的各种法律论述,直接秉承了柯克以降的普通法主流的思想传统。作为一个律师、法官和法学家,哈勒明确申明,“在执行司法活动时,我小心谨慎地将我自己的激情放在一边,不论它们如何令我激动,我都不向他们让步”。[393] 但哈勒的职业生涯并非真的毫无“激情”,相反,正是借助这种纪律与自制,他才将“在实质与自然方面都属于民事的行为,转变为真正在形式上是宗教的行为”。 [394]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要在他受到感召的天职中做好他的工作。“基督徒的能量,应该先消退,再涌回”。[395] 上帝的全能,正体现在能够用类似法律的方式来调控一个人的行动,选择“理性”的方式来确保人的救赎。不过哈勒的理性,却并非空洞的普遍知识,而是能够洞察特殊性的“技艺理性”。上帝与激情,就在这种“特殊性”中。
正是律师和法官的“有纪律的激情”,使普通法能够容纳普通人相互冲突的伦理理性化,并利用这种伦理理性化的冲突,推动普通法这种社会秩序的理性化的发展。如果说法律职业人士真象富勒所言,是社会秩序的建筑师[396],那么普通法律师一定是一个表面上最无能,但实际上却最谦逊的设计师,他的手中并没有画好的图纸,他的天职就是让那些勾划“图纸”的普通人的激情,有能够活动的空间,让彼此冲突的自由的伦理,能够在他的职业活动下享用、创造并再生产这个空间。因此,正是法律职业的责任伦理,才使得普通社会成员彼此冲突的信念伦理可以共享一个无需实质性共识的社会空间,不致于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和利维坦两个极端之间来回跃迁[397],从而使这些多元价值的伦理理性化与个性形塑真正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法的理性,是伦理意义上的,而非道德意义上的;是自助意涵的,而非庇护意涵的。
这样讲,也许不免让人产生精英主义的印象。这正是普通法经常面对的一个批评。从法律管理的角度看,基层法院管理的一般是例行案件,而只有上诉法院才会处理疑难案件(先例原则也体现了这一点)。而将一个案件“变成”疑难案件,需要大量的精力、时间乃至相应的法律知识,而这些条件,在社会上当然不是均匀分配的,也许只有少数人才能直接运用这种自助性的法律,来创造自由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法容纳的“普通人”的伦理理性化冲突,似乎只是那些士绅与市民阶级的,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398] 但由此就简单地认为,普通法较之立法理性支配下的大陆法,更具精英性,也许并不公允。普通法并不是将个人命运交给某个具有主权意志和数学家式的理性的立法者来决定,更不用说一种无名的卡夫卡式的法律机器了,而是一座可容纳个人努力与斗争的司法竞技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法更“民众化”。[399] 从韦伯的思想来看,“为自己而斗争”并不是一种社会普遍性的能力,倒是一种韦伯所赞赏的“市民阶级的品德”,是市民阶级特有的“精神气质”,是自由的伦理理性化动力。耶林曾指出,“法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和平的手段是斗争。…世界上的一切法都是斗争得来的”。[400] 不过在法治国“无缺陷”的万全法中,似乎并没有给这样的斗争留下多少空间。[401] 而如果象在清教徒的“良知治理”的共同体中一样,试图运用“上帝之道”作为一种平等化的力量,同样也不能将这种伦理理性化变成每个人的能力。相反,却可能取代个人自由的可能性。毕竟,只有上帝才是“夷平者”,但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并非上帝。在韦伯看来,个性作为我们最高的价值,正是在与生活展现的困境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402] 正如韦伯所言,我们所希望和承诺的,无论在思想还是行动中,都既非愚人的乐园,也不是轻松富足的安乐之境。[403] 人的尊严提出的要求是,值得生活的生活不仅仅是社会团结条件下的生活,而更是一种与生活本身的斗争,在接近耗竭的边缘上,塑造自己的个性。所以,法律的守护神最终仍然只能是每个人自己的守护神。“就法律而言,成熟的人就是每一个特殊的公民,他将法律看作是自己根深蒂固的特定目的…对于这样的人,法律才是最充分意义上的普通法”。[404] 也只有这样的公民,才有真正的法治和真正的国家。
六、“尾随者”的国度:自由的条件与自由的技术
从普通法国家的当代发展来看,普通法本身也日益实定法化。面对18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复杂性的日益增长,存在大量压力,要求国家进行更多的治理来维持所谓“自然秩序”或“自由秩序”,而这样的治理也日益以立法的形式出现,并交由正式或非正式的司法机构来处理,治理理性、立法理性与司法理性之间相互渗透。所谓“系统理性的引诱”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还是一个现实问题,面对复杂的社会,个人为自由而斗争是否仍然有意义,是否个人的自由命运最终要完全交给国家,法律的这种实质化倾向,以及政治正义,是否最终象韦伯所预言的那样,将我们带入一种新型铁笼,即使其中不是奴役的命运,也不乏冷漠与厌倦,充满了个人的无力,欠缺勇气、创造性与个人负责的精神。
因此,对现代社会的自由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自由的条件的问题,还是一个自由的技术的问题:人们能否承担一个自由的社会对每个人自身提出的挑战?不同理性之间在颉颃与制衡中形成的“亲合力”,与民主、主权联系在一起的立法理性,这些确实都构成了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自由的条件。 [405] 不过,学者们往往忽视了,能够担当这种自由社会的复杂性的自由人,需要具有自由的技术,能够面对冷漠与厌倦的挑战,做一个孤独的陌生人,一个自救的人。韦伯关注的个性形塑与伦理理性化,只有放在这一背景下,才体现了它不可或缺的意义。
自由的技术对于我们的国度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韦伯当年曾经非常关注“尾随者”(epigone)的问题。对于处于“尾随者”的一代人来说,他们可以不费任何代价,享用并非斗争获得的自由。而丧失了争取自由的过程,“尾随者”的一代也不再具有足够的尊严和真正的个性,最终也不再可能有自由可言。[406] 也许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韦伯预言的真正意涵:当自由的制度条件,脱离了个性与自由的技术,变成单纯的工具和形式的时候,这种理性化就从“轻飘飘的斗篷变成了沉重的铁笼”。
发展中国家往往迷信凡伯伦(Thorstein Veblen)所谓“落后的优势”。在这些国家中,制度的引进,程序技术的形式化挪用,往往是通过国家权威进行自上而下的制度移植。由于这种制度移植的力量,往往是一元性的权威,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家长制和“凯撒制”色彩浓厚的“伪法理型”权威,所以不仅不能建立多元的社会秩序,往往还妨碍这种秩序的发展。更为危险的是,这些社会理性化的制度化移植,完全脱离了任何推动伦理理性化的努力[407],没有任何实践权利的技术,作为这种理性化的行动支撑,最终导致理性化与自由的分离,理性化成为一个“仪式化”的“空壳”。我们只能象无所适从的学生一样,听见梅菲斯特在我们的耳边,半带怜悯半带嘲讽地说道, “法律和权利可以遗传,就象永久的疾病一样;它们从一代拖向另一代,从一个地方慢慢移到另一个地方。理性变成了荒谬,善行变成了灾殃;你作为尾随者,真是不幸!”在一个“尾随者的国度”中,幸福论驱动下的富强话语使那些思想或行动中形形色色的“立法者”忘记了,对于普通人来说,一旦那些社会理性化的纪律,没有任何伦理的意涵,更不用说与自由的关联,它就只不过是死板的条文、印在书页上的规章或者象机器一样空空转动的轰鸣,普通人的选择就是要么成为机器中的螺丝钉,要么躲在机器背后,唱一些怀旧的哀歌。理性化仅仅是例行化和事务化,而没有任何自由的意涵。即使有自由,也只是少数制度设计者的“自由”。
当然,在这样的国度中,自上而下的“创造”并未摆脱所有的观念和情绪,成为单纯的就事论事,恰恰相反,诚如韦伯所指出的,正是由于脱离了个人担当责任的伦理理性化,它才往往会在反动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极端之间摇摆。[408] 思想的迟钝与情绪的亢奋,使每个人都相信他们的光荣与梦想最终在彼岸;而披着堂皇外衣的众人的神,就是他们的守护神。
在古希腊,“守护神”是一个人灵魂的看护者,游荡在人与神的世界之间。这位看护者,体现了一个人灵魂中那种贴身的陌生性(familiar strangeness),一种有待发展的陌生性。这种隐秘的内在声音,总是暗含了一种来自外面的感召,一种超越的方向,或许是一种含糊的低语:在此身中学习做一个陌生的人。如果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将不可能是一种稳定的、令人确知、可以把握、甚至占有的东西,也许需要我们耗竭一生的力量,找到并坚守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命运,然后在冰冷的火焰中,燃成灰烬。
而在一个复杂的理性化社会中,正象美国大法官布雷南(Brennan)所说的,“自由是一件脆弱的东西,一件非常脆弱的东西”。它既需要那些看起来琐碎冷漠的程序“技术”来保障。[409] 但这些程序技术,同样也需要每个人艰苦的努力,而且也只能依靠这些努力,才能建立、维持和发展。离开了蕴含在每个人的伦理理性化中的自由技术,法律即使象机器一样,也并不一定靠得住。[410] 毕竟,“一部没有生命力的机器,只是僵死的精神”。[411] 在我们寄身的国度中,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意味着没有参与的人,也将没有自由,因为握着每个人生命之弦的守护神,既不是政治仪式中的口号或者标志,也不是机器中的幽灵,而就出没在每个人自己通向“天国”的路上。“这事情必定成就在一个人身上。你们不可集体行动。你们必须分开。你们必须一个人一个地干。这样才有希望”。
在1906年讨论俄国的处境时,韦伯曾经指出,俄国和美国,作为两个地域辽阔,但又与世界历史缺乏关联的国家,也许是从头开始彻底建设“自由”文化的最后机会。不考虑所谓的“国民性”,也不考虑民族利益方面的冲突,甚至不考虑参与者的“党派”和“阶级”,俄国争取自由的斗争,在韦伯眼中,具有普遍历史的意义。[412] 今天,另一个“大陆性”的国家,也许面临了同样的历史命运,或者象韦伯常说的,“在历史面前的责任”,一种具有普遍主义价值的世界历史努力。事隔八十年后,韦伯的“使命预言”最终会面对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无法预知。也许自由与个性的空间,能从韦伯的文章,延伸到眼前的这页纸上,并经过无数看不见的道路,通向许多无名者艰苦的日常努力,这些正是当年令韦伯深受触动的东西。尽管我们在今天所能守护的希望,和韦伯当年一样,并不比绝望更多。
* 本文的初稿,曾先后请舒炜、郑戈、赵晓力、强世功、林国基、黄春高和林国荣看过,他们都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我在美国的朋友蔡泳和谢桂华费心帮我找到了一些重要的文献,在此谨致谢意。并特别感谢强世功、赵晓力和郑戈在法学方面对我的指导,没有他们的帮助和鼓励,我不可能完成这项研究。当然,文章中的一切问题仍由作者本人承担。
[1] 这一点也体现在7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学界对韦伯的所谓“去帕森斯化”。从今天的角度看,无论是所谓“正统共识”中的韦伯形象,还是激进左派眼中的韦伯,争论双方的观点大概都缺乏对韦伯关心的问题的真正感受。Jere Cohen et al., “De-Parsonalizing Weber: A Critique of Parsons’ Interpretation of Weber’s Sociology”; Talcott Parsons, “Comment on Cohen et al”; Cohen et al, “Reply to Parsons”, reprinted in Peter Hamilton ed., Max Weber: Critical Assessments II (London: Routledge, 1991), Vol. 2: 111-40. [2] 施路赫特也指出,帕森斯与马尔库塞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具有类似的历史视角。参见 Guenther Roth and 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12, n.4. [3] 今天回头来看,比较而言,倒是所谓“正统主流”的解释更多地考虑了韦伯对现代性的复杂理解,尤其是后来饱受非议的帕森斯。卢卡奇等人对韦伯思想的读解背后的理念,我在“论抽象社会”一文中有所讨论,《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1-27。 [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收入《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李小兵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101。 [5]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帕森斯在翻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将这篇“前言”一并译出,置于正文前,在英语和汉语的学界,许多人都误将此文当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论”,这是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错误。正如Benjamin Nelson所言,这篇写于1920年的著作是整个韦伯著作的“关键线索”。参见韦伯,《世界宗教论文集》“前言”(原为“导论”),收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1-19。 [6] 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两项早先的研究一同构成《文集》的主体,是韦伯继《新教伦理》以后宗教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计划,包括已经完成的有关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研究,未最后完成的古代犹太教分析,以及甚至没有来得及成篇的对伊斯兰教和早期基督教等宗教的研究。参见 Wolfgang 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Chap.XII. [7] 均写于1915年,在1920年又经过韦伯的修订。这两篇文章收入中文版的《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导论”,3-40;“中间反思”(王容芬译为“过渡研究”),302-37。 [8] Friedrich Tenbruck, “The Problem of thematic unity in the works of Max Weber”, in Keith Tribe ed. Reading Weber (London: Routledge, 1989), 42-84. [9] 除了下文直接论及的一些争论外,一个争议的焦点是韦伯的著述是否只具有一个核心问题。可能象雅斯贝尔斯所言,韦伯的著作就是一些“分散的片断”,而“片断化”(fragmentation)正鲜明体现了韦伯思想与生活的风格。认定一位学者毕生的研究只是围绕一个中心问题,这本身并非理所当然的假设。尽管本文的分析仍主要是从一个问题域出发,考虑韦伯的思想,但我们并不因此认为这一问题域是贯穿韦伯全部著述的唯一问题域。而且即使在本文考察的这一问题域中,韦伯有关的新教伦理的分析与韦伯有关现代法理权威的论述,尽管涉及同样的主题,但却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触及了这一主题。实际情况显然要比腾布鲁克最初认为的情形复杂得多。参见雅思培(雅斯贝尔斯),《论韦伯》(鲁燕萍译,台北:桂冠图书,1992),9。 [10] 这也许是韦伯思想的真正“精神”,参见 Dirk Käsler, Max Weber: an Introduction to His Life and Wor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Chap. 7. [11] Tenbruck, “The Problem of thematic unity in the works of Max Weber”, 75. [12] Entzauberung 的译法至今仍有一些争论,从字面上来看,应译为“de-magicification”(施路赫特就认为这样更准确)。在英语学界,尽管 “除魔”(disenchantment,中文也有人译为“除魅”)是较为普遍的译法,但也有学者指出(如Hennis),应译为“去神秘化” (demystification),不过从中文的角度看,“去神秘化”并不太准确,似乎仍以“除魔”一词较为理想。 [13] “导论”中一次,“中间反思”中两次,尽管韦伯在成熟阶段(1915年)之前,就已经使用过这一概念。参见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577-8 n.35. [14] 被编入《经济与社会》中的许多文稿属于韦伯为拟议中的《经济、诸社会秩序与及其权力》一书撰写的部分文字。新版韦伯全集将原属《经济与社会》的这些文本按这一书名重新编辑。三联书店的中文版《韦伯选集》也采取了这一做法,只不过译做《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甘阳编,李强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8)。有关该书著述史方面的情况,参见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Chap. XIII. 以下出于引文的方便,我们仍然援用《经济与社会》的名字。 [15] 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Chap. XII- XIII. [16] Wilheim Hennis, Max Weber: Essays in Reconstruction (London: Allen & Unwin, 1988)。当然部分受德国学者的影响,当代美国的年轻学者也力图扬弃以帕森斯和本迪克斯一手树立的韦伯形象,这显然比 “韦伯的去帕森斯化”要有意义得多。特别参见 Lawrence Scaff, Fleeing the Iron Cage: Culture, Politics, and Modernity in the Thought of Max Web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17] Hennis, Max Weber, 64. [18] Karl Loe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2), 19-22. [19] Hennis , Max Weber , 45,38. [20] 韦伯在承认桑巴特对自己思想的影响的同时,明确区分了自己的思路与桑巴特的思路,这一区分散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各处,例如55;157- 161,注12,注14。这一点特别体现在韦伯一直强调的对理性资本主义与其它形式的资本主义(如贱民资本主义或盗贼资本主义)的明确区分上,例如 Max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89-90. [21] 例如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7-8。而正是因为韦伯能将“个性”、“生活方式”与“人”的问题放在具体的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或社会学的研究中,才使他的这些观念与当时盛行的个性的偶像崇拜或所谓“伦理文化”区分开来。韦伯对文人习气的批判,矛头针对的实际上是无视现实的浪漫主义。在韦伯看来,这种“文人的肥皂泡”,有意培养了一种无视现实的习惯,缺乏韦伯一再强调的“现实感和客观性”(Sachlichkeit)。而且打着所谓“生命”或 “体验”的旗号,不仅不能坚守个性,相反却是在瓦解个性。有关韦伯对文人习气的批评,参见韦伯,“以学术为业”,《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5-7;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07。韦伯对所谓“伦理文化”的严厉批评态度,例如 Max Weber, “Anticritical Last Word on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3, No.5 (1978),1125; 尤其参见 Scaff, Fleeing the Iron Cage, 22ff. [22] 这一点在亨尼斯的“解释”方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亨尼斯一再强调韦伯的中心问题是“人的发展”,但由于确实很少能直接在韦伯的文本中找到充分的例证,亨尼斯不得不反复辩解说韦伯并未明确地阐述自己关注的根本问题,但既然韦伯关心的问题是“人的发展”这样一个经典问题(无论是在政治思想史中,还是在德国知识界里),那么,他为什么偏要躲躲闪闪,不肯明言呢?而且亨尼斯也没有告诉我们,仅仅是在阐述传统问题的韦伯,为什么偏要费尽心机构建一套解释社会学的范畴框架,反复思考相关的“科学学说”问题,而在亨尼斯看来,这些思考本身在韦伯的思想中并没有什么核心地位,只不过是以“隐晦”的方式(?)展现了韦伯对 “人的发展”的关注。此外,亨尼斯片面强调韦伯早期作品的重要性,认为韦伯从法学转向国民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而相反却对1908年前后韦伯转向社会学不置一词甚至嗤之以鼻,这些都暴露了亨尼斯思路的缺陷。这样看来,施路赫特讽刺亨尼斯的这种方法是“侦探式的思路”,并非偏见之辞。参见 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413。正如韦伯本人尖锐指出的,在科学领域中“采用‘人’的概念显然不是一种对经验问题的解答。相反,它是一种神秘化的做法”,Max Weber, Critique of Stamml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 168. [23] 这当然与亨尼斯对韦伯早期作品的片面强调有关。不过,限于本文的目的和篇幅,这里不可能处理这样复杂的问题,但下文的论述已足以表明作者在这方面的态度。在我看来,韦伯对于现代社会理论的重要性正在于他是一个“社会”(Geschellschaft)的社会学家,而非“共同体” (Gemeinschaft)的社会学家。参见 R. Holton and B. Turner, Max Weber 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39。韦伯的这一立场突出地表现在他在政治著述中对各种“粗疏的浪漫派”坚持不懈的批判,特别是他对某些人倡导复兴传统的“等级国家”,以建立所谓经济-政治方面的“团结原则”的驳斥。参见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00ff。不过,特纳本人仍然认为韦伯是具有怀旧情绪的悲观社会学家,特别体现在他的“命运”概念上,是十九世纪怀旧社会学的代表。对此,笔者的看法完全相反,下文对此有所论及。不过,对这一问题更全面的考察,也许需要我们尝试阐述一种真正的“命运社会学”。特纳的观点参见 Bryan Turner,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Body: Reflections on Modernity and Discipline”, in Sam Whimster and Scott Lash ed., Max Weber, Rationality and Modernity (London: Allen & Unwin, 1987), 236-8. [24] “可能价值冲突的代言人的意图经常遇到的最严重的误解就是宣称这种立场是‘相对主义’”, Ma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Glec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49), 17. [25] 韦伯, 《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前言”,15。 [26] 韦伯, 《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前言”,4,译文有改动(参考德文版,下同)。 [27] Tenbruck, “The Problem of thematic unity in the works of Max Weber”, 56. [28]我们这里的论述包含了来自争论双方的想法。笔者认为,无论腾布鲁克对韦伯的进化论甚至目的论色彩(类似韦伯所批评过的“流溢论”)的读解,还是蒙森的历史主义色彩的阐述,都与韦伯的整个努力方向相悖。参见Tenbruck, “The Problem of thematic unity in the works of Max Weber”,64; Wolfang Mommse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 chap.10; 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37ff; John Love, “Developmentalism in Max Weber’s Sociology of Religion: a critique of Tenbruck”, Arch. europ. sociol., 34 (1993), 339-63. [29] 尽管亨尼斯强调的“生活秩序”(Lebensordungen)在韦伯的文章中似乎更常见,但韦伯却选择“社会秩序”作为拟议中的著作的书名(《经济、诸社会秩序及其权力》)并非毫无来由。一方面,自腾尼斯以来,“社会”这一概念在德国社会学中就具有重要的意涵(尽管许多时候带有否定的意涵);另一方面,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韦伯在晚期著作中,尤其随着支配社会学研究的开展与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深入,更明确地考虑在社会秩序与个性-生活行为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而非二者之间的吻合,因此我们采用了社会秩序这一用法。有些英文研究著作或翻译,就径直将“生活秩序”一词译为“社会秩序”,这样尽管不妥,但却多少表明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一致性。 [30] 韦伯在“中间反思”中对经济、政治、审美、性爱和知识诸社会领域中的理性秩序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探讨,参见“中间反思”,307-330。 [31] 这并不意味着韦伯没有研究这两个问题。《经济与社会》中较早撰写的部分主要探讨的就是这些问题(原因正如我们下面揭示的,是因为韦伯在有关领域中没有找到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之间的“亲合力”)。《世界经济通史》这一授课记录(以及《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也在许多方面触及了这一问题。但整个《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以及《经济与社会》中较晚撰写的部分,尤其今天作为第一卷出版的部分)则是以第三个问题为核心的,而且,在我看来,这也正是韦伯对现代社会理论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贡献。 [32] 韦伯, 《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前言”,15,译文有改动。 [33] Hennis, Max Weber ,39. [34] 《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导论”,15。 [35] “中间反思”,306-7。 [36] 韦伯,《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导论”,30-1,译文有改动。 [37] 韦伯, 《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前言”,16,译文有改动。值得指出的是,无论英文还是中文的翻译,都忽略了韦伯使用的“惯习”概念。 [38] 韦伯, 《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前言”,7。 [39] Loe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 63,n.45. [40] 在我看来,理解韦伯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恰当地处理韦伯著述中的这些段落。既不能象美国主流社会学界常做的那样,将它们看作无关紧要的,非科学的“价值”感慨,也不能象亨尼斯那样,无视韦伯对“具体现实的科学”的倡导,象侦探一样从韦伯卷秩浩繁的著述中搜寻这样的段落(所以他们最偏爱的韦伯文本不是韦伯的社会分析,而是韦伯的通信和韦伯夫人的传记),把韦伯视为一个“文人”,两种做法都割裂了这些段落与韦伯的社会理论之间有机又充满张力的关联。[41] 这也许正是浪漫派尖锐批评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原因。诺瓦利斯就看出,“在这部作品中,浪漫的东西,还有自然的诗意和神奇的东西全都湮灭了。它写的只是普通人的各种事情,而自然和神秘全都给遗忘了”。参见卢卡契(卢卡奇),“德国文学中的进步与反动”,《卢卡契文学论文选》第一卷,56。 [42] Loe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 59ff;类似的观点参见 Harvey Goldman, Max Weber and Thomas Mann: Calling and the Shaping of the Self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43] Liebersohn 强调韦伯与腾尼斯相比,体现了德国社会学想象力中两种不同的思路(命运或乌托邦),参见 Harry Liebersohn, Fate and Utopia in German Sociology: 1870-1923 (Cambridge: Cambridge, 1988)。Scaff 也认为韦伯力图摆脱乌托邦的观念,Fleeing the Iron Cage,30. [44] 韦伯致Georg Kaiser的一封信,转引自 Mommse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 135. [45] 歌德,“然而什么是你的义务?日常的要求”,《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董问樵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51。“以学术为业”, 49。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同样引用了这句话,196页注64。歌德这句格言中的“日常”,又有“当下”(present)之义,因此,带有浓厚的古代哲学味道。而在韦伯笔下,这种异教色彩的个性观念摇身一变,成为现代新教徒的伦理写照,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观念史与社会史方面的意涵,对于理解现代性的社会理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这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了。 [46] 韦伯,“以学术为业”,49,译文有改动。 [47] 韦伯,“以政治为业”,113,译文有改动。类似的论述,参见“以学术为业”,41。 [48] 一种“全面发展的个人”,马克思讨论在共产主义问题时经常提到类似的说法。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卷46(上),108-9。 [4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42。 [50] Max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68。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铁笼”的译法并不准确,未能传达韦伯笔下Gehāuse兼具“保护”与“禁闭”的意涵,也许“(铁)屋”会更好一些。韦伯在论述农奴制、科层制和福利国家问题时,都曾使用这一比喻。不过,考虑到中文学界已广泛使用这一用法,在没有找到更贴切的译法前,权且保留这一译法。 [51] 1889年,韦伯致鲍姆加登的信。转引自Scaff, Fleeing the Iron Cage,14. [52] Loe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29; Ma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35. [53] Mommse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3ff. [54] 参见 David Beetham, “Max Weber and the Liberal Political Tradition”, in Asher Horowitz and Terry Maley ed., The Barbarism of Reason: Max Weber and the Twilight of Enlightenmen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4), 99-112,不过作者将韦伯与Hobhause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相比,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看到韦伯的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特征。韦伯的现实主义态度并没有使他相信自由主义的“社会化”是解决自由主义困境的出路。 [55]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56. [56] 施路赫特称之为韦伯的“第二次突破”,迈向了理性化的社会学与类型学, 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44ff;蒙森认为韦伯思想突破的关键是克里斯玛概念的变化和纯粹类型方法的发展,Mommse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121ff. [57] 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儒教与道教》的分析格局上,以及同期撰写的 “中间反思”一文。 [58] Mommse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10。洛维特和蒙森都引用过韦伯的一句重要的话,“面对日益盛行的科层化趋势,如何依旧有可能维持某种人的活动自由”。参见 Loe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54; Mommse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35. [59] 在韦伯之后,德国的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如 Otto Hintze,Gehard Oestreich 和 Shilling 等,尤其是 Schilling 对所谓“第二次宗教改革”的研究,强调了加尔文教(及路德宗和天主教)与早期现代国家的兴起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纪律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过在 Schilling 看来,这与经典的韦伯命题是有分歧的。而正如下文逐渐揭示的,这些历史研究的社会理论意涵,对于我们这里有关“英国法”的讨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意义。参见 Herz Schilling, “The Second Reformation”, in Religi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Early Modern Society (Leiden: E. J. Brill, 1992), 271-2. [60]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78-9; 类似的说法参见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 17; “以学术为业”, 39。 [61] 这一点以戏剧性的方式出现在韦伯1920年最后修订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在第二章的结尾,韦伯在原有的“我们可以从根本不同的基本观点并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使生活理性化”一段话之后加上了一段话,以作强调: “所有致力于‘理性化’的研究都应该以这一平实的句子为出发点”,然而,下面紧接着的论述就是,“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由反题构成的一个世界”。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57,译文有改动。 [62]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42. [63] 参见Scaff, Fleeing the Iron Cage,29ff,讨论韦伯从法学转向国民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64] 参见施路赫特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Wolfgang Schluchter, “Convi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in Paradox of Modernity: Culture and Conduct in the Theory of Max Web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8-101.中文译文,见李康译,“信念与责任”,载入本期杂志。 [65] 韦伯,“中间反思”,312。 [66] 韦伯,“以学术为业”,63页以下。 [67]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42,译文略有改动。 [68] 例如,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称罗伯斯庇尔为“对理性的克里斯玛式的崇拜”(charismatic glorification of “Reason”), Economy and Society, 1209. 参见 Mommsen ,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141,对这一变化的讨论。蒙森恰当地指出,这一概念逐渐从特定的历史性的“理想型”发展为一种纯粹的“理想型”,参见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121-32。不过,蒙森有关韦伯“方法论”变化的其他论断,就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他似乎赋予了韦伯本不具有的“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倾向。 [69]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1150. [70] Wolfgang Mommsen, The Age of Bureaucracy (Oxford: Blackwell, 1974), 111ff. [71] Mommse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24ff. [72] Friedrich H. Tenbruck, “Max Weber and Eduard Meyer”, in Wolfgang Mommsen and Jurgen Osterhammel ed. Max Weber and His Contemporaries (London: Unwin Hyman, 1987), 252. [73] 从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来看,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74] Mommse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143. [75] 韦伯,“以政治为业”,98,译文有改动。 [76] 参见 Peter Baehr, “Max Weber as a critic of Bismarck”, Arch europ. Sociol. 29 (1988): 149-64. [77]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Bismarck’s legacy”(“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under a New Political Order”), 135. [78]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40. [79]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编,甘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98以下;以及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35. [80] 在1884年11月8日致鲍姆加登的信中,青年韦伯就指出,“俾斯麦的凯撒制的险恶特征就是普选”,转引自雅思培(雅斯贝尔斯),《论韦伯》,28,译文略有改动。韦伯认为,这种所谓的“普选”实际上是“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就这个词的真正意涵而言)的谋杀者”。转引自Marianne Weber, Max Weber: A Biograph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8), 117-8. [81]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80-81,220ff;并参见 Peter Baehr, “Max Weber as a critic of Bismarck”的讨论。 [82] 当然韦伯也认为,凯撒制这种因素在大众动员的国家(mass state)和议会民主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参见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74. [83]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90-1,译文有改动。 [84]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44, 145. [85]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69. [86] Mommse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29. [87] Loe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55-6. [88]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91以下。 [89] Mommsen, The Age of Bureaucracy, chap.5. [90] 韦伯,“中间反思”,321-35,译文错讹较多,需留意。 [91]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71. [92] 对凯撒制与民粹主义观念的民众动员的讨论,参见韦伯对“普遍公民权”问题的讨论,见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80ff, 220ff [93] 韦伯,《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导论”,18,中文误译为“气度非凡的仪表”。 [94] Talcott Parsons,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92. [95] 参见 Reinhard Bendix,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第三部分的论述安排。 [96] Anthony Kronman, Max Web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 [97]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52ff. [98]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以往对韦伯法律社会学的探讨,主要关注的问题集中在法律理性化与经济理性化(或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的兴起)之间的关系上,并进而认为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主要涉及的问题是与私法相关的问题,如契约自由。这样做似乎直接忽视了韦伯法律社会学与支配社会学之间的紧密关联,不过近来的情况有所改变,参见 Stephen Feldman, “An interpretation of Max Weber’s Theory of law” , in Law and Social Inquiry, Vol.16, No.2, (1991): 105-48; Toby E. Huff, “On Weber, Law, and Universalism” ,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 1989, 21, fall, 47-79. [9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56,译文有改动。 [100]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51. [101]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81. [102]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49ff, 691ff. [103]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54ff。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韦伯以比拟口吻提到的“决疑术”正是英国普通法的一个重要法律推理技术。 [104]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784ff. [105]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56,以及809以下论“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 [106] 例如围绕令状制度形成的各种形式的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技术,参见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56ff. [107]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762. [108] 当然,这里“克里斯玛”的意涵,主要是我们提到的“传统”或“巫术”意义上的“克里斯玛”,与后来韦伯逐渐发展的“克里斯玛”概念的意涵不同。 [109]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89;不过,对于这一问题,韦伯的立场也相当含糊,他同样指出,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主要特征的一些技术,并非起源于罗马法,而是来自中世纪: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49.n.a. [110] 因此,至少从韦伯的分析出发,英国普通法,不仅不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形式化的法律,也同样并非是在原则上具有较高理性的实质法,这一点与Fletcher 颇有影响的论点正好相反,尽管Fletcher是采用多少有些不同的术语来论述的。参见George P. Fletcher, “Two Modes of Legal Thought”, The Yale Law Journal, 90: 970-1003. [111] “卡迪司法”是指判决案件时依据的不是理性的“判决规则”,而是对个别案件的具体价值评判,取决于法官的公正感,或者其它非理性的审判手段。在韦伯看来,陪审团、太平绅士参与地方司法管理,乃至英国法对罗马法继受的抗拒,都是英国法中“卡迪司法”痕迹的体现。参见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976ff, 891-2; Political Writings, 148。值得注意的是,英译者在p.806n.40中对“卡迪司法”所做的界定并不准确。即使从实质理性法的角度看,“卡迪司法”也是理性化程度较低的法律管理形式。 [112] 研究英国法律史的比利时学者 Caenegem 认为,在韦伯的理论中,普通法具有两副面孔(double face),对中上阶层采用形式理性的法律,而对日常生活中下层的小型案件,则采取“卡迪司法”的形式。这一观点似乎没有看到,在韦伯的理论中,英国法的形式理性,并非大陆法系的形式理性,而仅仅是外在的形式主义,而这种理性化程度较低的形式主义,与英国法在“实质”意义上的非理性(即卡迪司法)是有内在关联的,两者都与英国法律思维方式受到普通人的强烈影响有关,与大陆法系的“教授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参见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90-2;R. C. Van Caenegem, “Max Weber: Historian and Sociologist”, in Legal History: A European Perspective (London: Hambledon, 1991), 212. [113] 正如Trubek所指出的,在这个问题上,韦伯同样也语焉不详,有诸多相互矛盾的说法。但总的来说,韦伯的观点仍是强调英国法尽管不是逻辑形式理性的法律,但却是可以计算的。这一论断在较晚写峻的《儒教与道教》在比较中国与英国的法律结构的段落中特别明显,参见韦伯,《儒教与道教》,156-57; David Trubek,“Max Weber on Law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Wisconsin Law Review, 1972, 721-53. [114] 两位学者进行的比较政治研究指出,在发展中世界的民主国家中,52%的国家要么采纳普通法的传统,要么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而具有比较持久民主经验的国家往往是前英国的殖民地。见 Huff, “On Weber, Law, and Universalism” , 70. [115] Zweckrationalitāt 在英语文献中一直被交错译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或“合目的的理性”(purposive rationality)。从涵义看,前者显然有严重的问题,而后者则更准确,但中文的表达则不免累赘,本文尝试译为“目标理性”,而且从中文的一般用法来看,“目标”也比“目的”更好地表达了韦伯这一概念与“价值理性”相对的意涵。 [116] 例如 Ann Swindler,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ty in the work of Max Weber”,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 43, No.1(1973):35-42. [117] 例如 Arnold Eisen, “The Meanings and confusions of Weberian ‘rational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9, No.1 (1978), 57-70. [118] Eisen 认为构成“理性”概念的意项包括6种,而Brubaker则认为韦伯笔下的“理性” 至少可以发现有16种意涵,Kronman 则仅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部分就找到了“理性”的4种意涵,分别见Eisen, “The Meanings and confusions of Weberian ‘rationality’,58-61;Rogers Brubaker,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London: Routledge, 1984), 2; Kronman, Max Weber, 73-5。而韦伯本人清楚地认识到“理性”概念的这一特点。在回应布伦塔诺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批评时,他就特别强调了理性的复杂性,指出“如果说本篇文章还有一点真知灼见,但愿这点真知灼见能用来说明看似简单的‘理性’这一概念的复杂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56-7页注9。但有必要强调的是,韦伯始终仍认为,可以而且有必要使用“理性”这一个概念来表述这些复杂性。这一点同样在《新教伦理》中有所论及。韦伯指出,“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是一个由各种反题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世界”(第57页,译文有改动)。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强调的那样,理解韦伯的“理性”概念(以及韦伯的整个社会理论),就必须认识到,韦伯一方面考虑了“理性”概念是复杂多元的,并打上了具有偶然性和独特性的历史进程的烙印,但另一方面“理性”恰恰是通过将这种理念与历史两个方面的复杂性结合为一个富有张力与冲突的“理想类型”,揭示了其中“普遍历史” 的意义与有效性,这正是西方“理性”的特殊分析价值,也就是韦伯为什么说,对宗教的比较历史分析的尝试,“最终和首先都必须和愿意有朝一日同时成为对理性主义本身的类型学和社会学的一种贡献”(“中间反思”,303)。这一点是理解韦伯思想的活力和创见的关键线索,而许多学者却有意无意地无视了这一点。 [119] Gret Mueller, “The Notion of rationality in the work of Max Weber”, Arch.europ.sociol., Vol.20 (1979), 149. [120] 有关这两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参见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40ff。在英文版中,分别将这两个概念译为“communal”和“associative”。这里的中文译法只是为了保留原文中与腾尼斯概念的关联,不过韦伯明确指出他的用法与腾尼斯有所不同。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41. [121] 需要指出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讲,韦伯心目中的伦理理性化,本身恰恰是在分化社会中才有可能。这与许多从浪漫主义和保守主义出发理解伦理问题的学者,在社会观念上有巨大的差异,不过本文不可能讨论这一复杂的问题,也许要留待另一篇有关“陌生人”问题的文章来讨论了。 [122] Mueller, “The Notion of rationality in the work of Max Weber”,150ff. [123]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往往仅注意到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以及价值理性与目标理性之间的冲突。前者是韦伯针对现代社会的文化与政治的重要诊断,在当代受到了相关领域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后者在经济领域中有关效率与分配正义及“社会主义”的争论中一再被提及。但不同目标理性之间的冲突则受到了广泛的忽视,在“论抽象社会”中,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论及了这一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在韦伯的政治论文中是一个常见的主题,特别是科层制与其它理性地调控生活行为的方式(如私人资本主义)之间始终存在的紧张关系,例如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90, 156ff. [124] 这是将这对范畴与目标理性/价值理性对立混淆起来的一个表现,例如Brubaker,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36. [125]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5-6。经济社会学中与法律社会学中的形式理性/实质理性区分之间的关联在韦伯有关法律对契约自由的保障和限制的讨论中,有比较清楚的论述,参见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68-81. [126] 当然还涉及了所谓“世袭司法制度”(the patriarchal system of justice),参见 Kronman, Max Weber, 77ff. [127]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16. [128]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28. [129] 韦伯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大概是因为他在此处主要关注的是神圣法与世俗法(尤其是私法)之间的关系。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28-31. [130]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第一部第二章。 [131] 同上书,第34页。 [132] Shilling, “The Second Reformation”. [133] Brian Tierney, Religion, Law and the Growth of Constitutional Thought:1150-1650 (London: Cambridge, 1982),引文见107-8。 [134] 伯尔曼一再强调,在“教会革命”推动下形成的教会法是第一个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实现了教会法内部的系统化,并将理性应用于各种习惯法,废除大量不合理的习惯,将合理的习惯纳入法律体系中,同时还创用了大量至今仍在使用的法律概念、法律推理等诸多技术。《法律与革命》,629-34。这与韦伯对教会法发达的形式技术程度的论述是一致的。尽管伯尔曼自己批评了韦伯的观点,但似乎他的批评主要是建立在对韦伯著作常见的误解之上的,正确的箭并没有射到正确的靶子上。例如,他就将韦伯笔下两套不同的理性范畴划分混淆起来,《法律与革命》,653-4。Treiber 曾撰写长篇论文,证明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与法律社会学之间存在“亲合力”,但可惜只是满足于分析结构上的对照,而没有更深地从核心问题的角度来着眼。参见 Hubert Treiber, ” ‘Elective Affinities’ between Weber’s Sociology of Religion and Sociology of Law”, Theory and Society, Vol.14 (1985), 809-61. [135] 荷兰法学家罗斯认为,韦伯的法律实证主义明显地以概念法学为基础。有关德国法学思想的发展,特别是概念法学对韦伯的影响,参见林端,“德国历史法学派:兼论其与法律信实论、法律史和法律社会学的关系”,《台大法律论丛》,第22卷,第2期,特别是29页。 [136] 加藤一郎,“民法的解释与利益的衡量”,梁彗星译,收入梁彗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75。 [137]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73. [138]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67. [139]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37. [140] 有关韦伯法律分析中的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理论之间的关系,参见J.M. Finnis, “On Positivism and ‘Legal Rational Rationality’”,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5, No.1 (1985), 74-90. [141] Kronman, Max Weber, 30. [142] 例如Roger Cotterell, “Legality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the Sociology of Max Weber”, in David Sugarman ed. Legality, Ideology and the State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3), 88. [143] 二者之间的这一联系在韦伯晚年有关世界经济通史的讲课记录中体现得十分清楚,参见维贝尔(韦伯),《世界经济通史》,姚曾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287-91。 [144] Leonard Krieger, 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 253. [145] 参见 Neumann, The Rule of Law (Leamington Spa: Berg, 1986), 200ff.对德国宪政史的论述。 [146] Krieger, 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 253-5. [147] Leonard Krieger, 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 257。从表面上看,这种观念颇具康德色彩。而且“法治国”的许多观念也似乎与德国经典自由主义者的观念有共通之处,强调国家基于一般法律来进行支配,并不甘于此,希望在否定的功能之外,国家还是一个文化国家,肩负教养的职责。但即使如此,二者仍然有许多关键性的差异。在康德和洪堡时代,国家与个人伦理(及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制约关系,自黑格尔的“伦理国家”之后,经过浪漫主义的洗礼,就逐渐为一种总体化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的关系所取代了。参见 Gerald Izenberg, Impossible Individuality: Romanticism,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Selfhood, 1787-180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5-6讨论了从洪堡到浪漫主义的“国家-个人”关系的观念的变化。 [148] 这一观念证明,“法治国”归根结底属于霍布斯时代的产物,有关实定法实现自然法的论述,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207-8。 哈贝马斯甚至批评韦伯没有更充分地考虑二者之间的关联,参见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1 (London: Polity, 1986), 260ff. [149] F. K.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114,转引自Cotterell, “Legality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the Sociology of Max Weber”, 89 n.4。在这一过程中,德国浪漫派的思想无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通过“绝对总体”生产“特殊化个体”的观念,对“法治国”中国家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参见 Ernst Troeltsch, “The ideas of Natural Law and Humanity in World Politics”, in Otto Gierke, 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 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4), “Appendices”, 201-22; Izenberg, Impossible Individuality。有关自然法与法治国观念的内在联系,参见 Otto Gierke, 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 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4), 137-8. [150] Otto Kirchheimer, “The Rechtsstaat as Magic Wall”, in Kurt H. Wolff and Barrington Moore.ed. The Critical spirit: Essays in honor of Herbert Marcus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7). 288。德国法学思想中国家的重要性,在对韦伯影响很大的耶林的一句话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无疑现代法哲学与早先的自然法相比的巨大进步,就在于他承认和强烈地强调法律依赖于国家”, 转引自Charles Haines, The Revival of Natural Law Concep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247. [151]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00. [152] Reinhart Koselleck 语,参见 Jonathan Sperber,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Prussia: Thoughts on a New Edtion of Reinhard Kossellck’s Preussen Zwishcen Reform und Revolu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57, No.2 (1985), 279 的讨论。 [153]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80-1。许多近来的韦伯研究著作都讨论了韦伯对“市民个性的衰微”这一问题的关注,例如 Goldman, Max Weber and Thomas Mann, 15. [154] 转引自 Neumann, The Rule of Law, 180. [155] 自由派法学教授 Karl Theodor Welcker 语,转引自 Krieger, 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 255, 256. [156] Neumann, The Rule of Law, 182. [157] 在魏玛德国,对这一问题的反省,成为左派与右派知识分子的一个争论的焦点,参见 David Dyzenhaus, Legality and Legitimacy: Carl Schmidt, Hans Kelsen, and Herman Heller in Weimar (London: Clarendon, 1997)。哈贝马斯则认为,韦伯的实证主义法律观,使他完全将合法性与法理性等同起来。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的批评似乎没有注意实证主义的观念与程序的观念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显然在他90年代的著作中,这一观点已经有所改变。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1 , 264-7. [158] Otto Kirchheimer, “Legality and Legitimacy”, in William E. Scheuerman ed. The Rule of Law Under Siege: Selected Essays of Franz Neumann and Otto Kirchheim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44-63;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65ff. [159] Krieger 和 Neumann 都提及这一点。不过,Krieger 只是简单地提及了这一问题,而尽管纽曼将之视为英德法治原则差异的关键,但在我看来,他的论述存在严重的问题,所以下面的论述并没有遵循他们的思路。试对比Krieger, 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 256;Neumann, “The Change in the function of Law in Modern Society”, in The Democratic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Legal Theory ,ed. by Herbert Marcus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7), 43ff。从下文第四部分有关英国“普通法心智”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转化具有内在的基础,即绝对主义国家与自然法哲学家在理性逻辑上的同构,柯施莱克对此有非常精辟的分析。参见Reinhart Koselleck, Critique and Crisis: Enlightenment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Modern Society (Leamington Spa: Berg, 1985). [160] 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第37页以下。 [161] 茨威格特和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奠等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254-5。 [162] Krieger, 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 258. [163] Robert Von Mohl 语,参见 Neumann, The Rule of Law, 181-2. [164] 对韦伯早期思想形成产生相当大影响的 Rudolf Von Gneist 语,转引自Krieger, 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 358. [165] Neumann, The Rule of Law, 181. [166]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82-95;参见 Neumann, “The Change in the function of Law in Modern Society”. [167]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82ff. [168] Max Weber, Critique of Stammler, 124ff; 及 Economy and Society, 326-7. [169] Kirchheimer, “The Rechtsstaat as Magic Wall”, 290. [170] 参见 Kirchheimer, “The Rechtsstaat as Magic Wall”, 294. [171]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47; Political Writings, 77-8, 334. [172] “法治国”的整个观念,在19世纪末就逐渐成为法学中的重要观念,影响了一代德国法学家,包括韦伯的许多老师和同时代的重要学者,参见 Haines, The Revival of Natural Law Concepts, 246ff。有关韦伯的法学教育对他社会理论的影响,参见 Stephen Turner and Regis Factor, Max Weber: The Lawyer as Social Thinker (London: Routledge, 1994);郑戈,《迈向一种法律的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法律思想研究》(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博士论文,1998),23-35。 [173] 1794年的《普鲁士国家普通邦法》,转引自茨威格特和克茨,《比较法总论》,256。 [174] 1766年的巴登王室法令,转引自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第37页。 [175] 格伦顿、戈登和奥萨魁,《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18。 [176] 韦伯,“中间反思”,312, 译文有改动。 [177] 参见 Otto Kirchheimer, “State structure and Law in the Third Reich”, in Scheuerman ed. The Rule of Law Under Siege, 142ff. [178] Franz Neuman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Freedom”, in Scheuerman ed. The Rule of Law Under Siege, 202. [179]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90。括号中的文字为引者加。 [180] 法的社会学往往倾向于排斥采用“内在视角”(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作为“分支社会学”,如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都如此),这样往往难以把握分化的社会领域中独特的理性。对于普通法来说,更重要的是,这种内在视角正是普通法的司法理性的重要特点,参见Andrew Lewis, “Legal Positivism: some lessons from legal history”, in Stephen Guest ed. Positivism Today (Aldershot: Dartmouth, 1996), 65-76. [181] H.L.A. Hart, Essays on Bentha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26. [182] Thomas Hobbes, “A Dialogue between a Philosopher and a student of the Common Laws of England,” in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London: John Bohn, 1966), Vol.VI:3-8。 [183] 从观念史的角度看,边沁的思想,通过耶林,直接影响了韦伯的法律观念,参见Turner and Factor, Max Weber: The Lawyer as Social Thinker, 11. [184] David Sugarman, “Legal Theory, the Common Law mind and the making of the Textbook tradition”, in William Twinning ed. Legal Theory and Common Law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39. [185] Hart, Essays on Bentham, 4. [186] 这是边沁对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的说法,大概同样可以看作他对整个普通法的看法。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3页。 [187]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我们忽略了霍布斯思想中在自然法学说与法律实证主义之间的潜在张力。从霍布斯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英国的法律实证主义学说同样经历了德国“法治国”观念的某些转化,通过吸收自然法中的一些关键性的理念,为实定法提供了潜在的支撑。而其中关键性的过渡环节就是霍布斯的理论。霍布斯的“理性”概念,更是成为未来社会工程的理性计算依据的基本尺度。参见 Nobert Bobbio, Thomas Hobbes and the Natural Law Tra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44-6. [188] Hobbes, A Dialogue between a Philosopher and a student of the Common Laws of England, 5. [189] Hart, Essays on Bentham, chap.1。值得注意的是,自柯克之后,普通法的主流观念传统很少称普通法的“理性”为“自然理性”,更多称之为“技艺理性”(人为理性)。 [190] 正如法律史学者密尔松指出,普通法中的这种“理性”观念保留了最初来自法语的意涵。S. F. C. Milsom,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Judge-made Law”,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London: the Hambledon Press, 1985),216。此外,普通法实践者的“理性”观念,还带有程序上的意涵,参见 Norman Doe, Fundamental Authority in Late Medieval English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8-13,讨论普通法“理性”的语言学背景。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柯克大力倡导普通法理性的时代,“理性”的这一用法具有非常具体的政治意涵,是当时政治-法律-宗教纷争的一个焦点。有关这一时代的“理性”与“合理性”(reasonableness)的讨论,参见 Christopher Hil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17th Century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3-23。在当代法学界中,也有一些对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观念都不太满意的欧洲学者倡导这样的观念,特别是Perelman倡导的所谓“新修辞学”,这一理论与我们下面论述的普通法的司法理性之间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参见Chaim Perelman, “The Rational and the Reasonable”, in The New Rhetoric and the Humanistic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Press), 117ff。有关“理性”概念的历史说明,参见本文第四部分的论述。 [191] 参见Nobert Bobbio, “Reason in Law”, Ratio Juris, (1988) vol.1, No.2:97-108。不过在某个重要的方面与Bobbio的观点有所不同,我与韦伯的看法倒更近似,自然法与实定法都同样属于立法理性。这一点就突出体现在霍布斯的立场中。Bobbio 本人强调了霍布斯思想中自然法因素与实定法因素之间的二律背反。事实上,这种二律背反并不仅限于霍布斯一个人,在17 -18世纪具有自然法倾向的学者中颇为常见,自然法的立法理性不是作为对抗绝对主义君主恣意意志的武器,倒成了后者立法的某种“导师”或“顾问”的形象(例如德国的Thomasius),这正是我们上面讨论过的实定法吸收自然法过程的一部分。因此,所谓“霍布斯”的时代,并非自然法的“霍布斯”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调门实际上却是借助自然法中的“理性法律”观念建构起来的实定法的立法理性,并希望最终能够以此建设一种绝对主义的国家。这一“利维坦”的时代,大概在许多方式,远不是霍布斯当初能够设想到的。参见 David Saunders, Anti-Lawyers: Religion and the critics of law and State (London: Routledge, 1997), chap.4;Bobbio, Thomas Hobbes and the Natural Law Tradition, 149-71;关于Thomasius,参见 Peter Stein, Legal Evolution: The 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51-2。相反,正如本文所论述的,倒是普通法的“法律理性”是“司法理性”(Bobbio 称之为 judging reason)的代表,而不属于“理性法律”的传统。这一点也与Bobbio对柯克的论述有所不同,参见下文有关普通法与自然法关系的讨论。 [192] Postema 在他出色的著作中,将边沁看作是一个普通法的修正主义者,似乎忽视了边沁倡导的法律观念的“哲学激进主义”色彩,其中的自然理性尽管带有普通法强调的“常识”色彩,但从法律治理的角度来看,却貌合神离。Gerald Postema, Bentham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Chap. 6. [193] W. T. Murphy, “The Oldest Social Sciences? The Epistemic Properties of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The Modern Law Review 54:2 (1991), 182-215. [194] Lon Full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21ff. [195] 克洛斯指出,布莱克斯通的这种“不知道”,“是任何想要成为普通法的伟大诠释者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布莱克斯通是这样的人,而边沁不是”。Rupert Cross, “Blackstone v.s. Bentham”, The Law Quarterly Review (1976) 92: 527. [196] Frederick Schauer, “Is the Common law law?”, California Law Review, (1989) 77:455. [197] 转引自 Sugarman, “Legal Theory, the Common Law mind and the making of the Textbook tradition”, 34. [198] Hobbes, A Dialogue between a Philosopher and a student of the Common Laws of England,7. [199] W. S. Holdsworth, Sources and Literature of English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5), 145. [200] 杰弗逊语,见 James Stoner, 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 (Lawrenc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2), 13. [201] 这样说,有两个方面的意涵:既指柯克通过将普通法“现代化”,也指柯克将中世纪中法律至高无上的观念带入了现代法律思想中。参见 John Undenwood Lewis, “Sir Edward Coke(1552-1633): His Theory of ‘Artificial Reason’ as a Context for Modern basic Legal Theory”, Law Quarterly Review 84 (1968), 333. [202] Sir Edward Coke, 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 I,97b,转引自 Stoner, 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 23. [203] A. W. Simpson, “The Common Law and Legal Theory”, in A. W. Simpson ed. Oxford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Second Series, Oxford: Clarendon, 1973), 79. [204] Lewis, “Sir Edward Coke: His Theory of ‘Artificial Reason’ as a Context for Modern basic Legal Theory”, 338. [205] 转引自 Alan Cromartie, Sir Matthew Hale (Cambridge: Cambridge, 1995), 32。从某种意义上讲,哈勒的观点并非比喻。英国的普通法在许多方面与自然法的早期意涵有近似之处,参见 D’entieve,《自然法》。而富勒有关“程序性自然法”的提法,正是继承光大了普通法的这一司法理性传统。参见Lon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206] 从普通法的这种法律理性的思路出发,现代分析法学中有关一阶规则(primary rules)与二阶规则(secondary rules)的区分完全是没有必要的,这一区分本身就是立法理性的产物。并再次证明了普通法与基于法律实证主义的现代分析法学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对哈特这一著名区分的批评,参见 M.J. Detmold,“Law as Practical Reas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4(3), Nov. 1989, 442ff;富勒也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了类似的批评,参见 Lon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141ff 。哈特本人对这一区分的论述,参见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第五章。该书将这两个概念译为,“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 [207] Cromartie, Sir Matthew Hale,20-1。饶有趣味的是,Cromartie 将柯克的这种思想与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阐述的思想相比。从我们下面的论述可以看到,这一共通之处远不止Cromartie所强调的方面。不过,我认为,柯克大概很难接受德沃金那么强的“实质”立场,认为这种法律的完善理性是由“原则”支配的。参见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特别是第9章。 [208] Gray在探讨哈勒的普通法学说时,讨论了三种不同的法律变迁模式,参见Charles Gray,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Sir Matthew Hale, Th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of Engla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xxvi. [209] J. A.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A Study in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17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2. [210] Hale, Th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of England, 40. [211] Sir Matthew Hale, “Sir Matthew Hale’s Criticism on Hobbes’s Dialogue of the Common Laws”, In Sir William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London : Methuen, 1956-1972), Vol.V, 504. [212] Lewis, “Sir Edward Coke: His Theory of ‘Artificial Reason’ as a Context for Modern basic Legal Theory”, 337. [213] 转引自 Stoner, 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 25. [214] Hale, ” Sir Matthew Hale’s Criticism on Hobbes’s Dialogue of the Common Laws”, 504. [215] 不过,边沁的理由是这样做的好处低于代价,因为个别案例的效用与整个规则系统稳定性的效用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这也成了边沁反对运用司法手段改善法律的一个重要理由。参见 Postema, Bentham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chap6. [216] Hale, ” Sir Matthew Hale’s Criticism on Hobbes’s Dialogue of the Common Laws”, 501. [217] R. Stone 语,参见 Postema, Bentham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31。Hale 有类似的说法,见” Sir Matthew Hale’s Criticism on Hobbes’s Dialogue of the Common Laws”, 501. [218] Peter Goodrich, “Antirrhesis: Polemecal Structure of Common Law Thought”, in Austin Sarat and Thomas Kearns ed. The Rhetoric of Law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57-102. [219] 在这段引文之后就是在宪政史上著名的段落,柯克引用布莱克顿(Bracton)的说法,“国王不在任何人之下,但在上帝与法律之下”(sub Deo et sub Lege)。Coke, 12 Report 63,转引自Stoner, 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30。但值得强调的是,普通法的这种宪政色彩,其基础是以“技艺理性”为核心的实践技术,以及以法律职业的封闭性和自主性为前提的制度保障,与法团观念背景的“混合政体”(mixed government)或民粹主义背景的“一致政体”(government by consent)的立法理性观念,在观念史和制度史的源流上,都有所不同(尽管与封建法律的法团观念有相当深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英国,直至清教革命,依靠“司法一致”的司法理性观念对绝对主义君主制进行的制约,仍然是主要的“宪政”保障,这正是所谓“古代宪章传统”(ancient constitution tradition)的重要意涵。参见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有关“司法一致”(judicial consent)与“民众一致”(popular consent)的对比讨论,参见Doe, Fundamental Authority in Late Medieval English Law, 22ff;有关“一致政体”与“古代宪章传统”作为两种主要的反绝对主义力量,参见J. P. Sommerville,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England, 1603-1640 (London: Longman, 1986), Chap. 2-3. [220] Hale, ” Sir Matthew Hale’s Criticism on Hobbes’s Dialogue of the Common Laws”, 501. [221] 与疑难案件相对的,有各种不同的说法,easy cases(德沃金)、plain cases(哈特)或clear case(麦考密克)等,但这里之所以采用“例行案件”的说法,并不仅仅是为了与韦伯的社会理论相关联,而更多是因为“例行案件”的提法更好地反映了这类案件判决过程的性质。 [222] Aulis Aarnio, The Rational as Reasonable: A Treatise on Legal Justification (Dordrecht: 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 1. [223] 也许正如 Aarnio 所言,对于法学理论来说,例行案件的意义并不太大(对此,我也多少有些怀疑)。不过至少,对于法律管理或法律理性的社会学分析来说,例行案件和疑难案件同样重要。Aarnio, The Rational as Reasonable, 1. [224] 所以,麦考密克才称之为“清楚的案件”(clear cases),与“不清楚的案件”相对。Neil MacCormick, “The artificial reason and judgement of law”, Rechtstheorie, Beiheft 2, 112-3。尽管麦考密克的文章采用了柯克的著名说法为题,但似乎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与经典的普通法学说中的司法理性有相当的距离,具有浓厚的“实定化”色彩。 [225] Detmold 称之为“准立法”(sub-legislation)的方式,“Law as Practical Reason”, 458. [226] 当然,由于运用有限数目的“初始令状”(original writs)开启诉讼程序,普通法确实需要考虑一些“外在”的事实,而非“逻辑分类”意义上的事实,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普通法程序历史发展的特殊过程有关。另外,陪审团的情况也类似,参见下文第四部分的讨论。不过,从法律推理的角度看,韦伯在普通法和大陆的“形式理性法”之间建立的区别,似乎并不恰当。 [227] Aarnio, The Rational as Reasonable, 103-5. [228] Niklas Luhmann,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aw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5), 174ff. [229] M.J. Detmold,The Unity of Law and Morality: A Refutation of Legal Positiv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175. [230] 绝对性与一般性的区别,参见 Detmold 对先例的讨论, 同上引文。 [231] Ray D. Perelman, “Analogy and Metaphor in Science, Poetry, and Philosophy”, in The New Rhetoric and the Humanistic. [232] 参见Arthur L. Goodhart,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the Common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31), chap.1. [233] Jack Beatson, “Has the Common Law a Future?”, Cambridge Law Journal (1997) 56(2), 312. [234] 转引自 Rupert Cross and J. W. Harris, Precedent in English Law (Oxford: Clarenden Press, 1991), 43. [235] 正如我们下面讨论所逐渐揭示的,案件涉及的“特殊性”一面,正是法律行动者借助稳定的法律程序,在价值自由的前提下实践权利的独特方式。普通法法律推理中对“特殊性”的重视,与浪漫主义背景下的保守主义观念对“特定个体中蕴含的精神总体”的强调相去甚远,后面这种观念对德国“法治国”观念的实质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也是诸如“活法”、“自由法”观念的重要背景,参见Troeltsch, “The Ideas of Natural Law and Humanity in World Politics”, 210-1。尽管(通过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间接受到德意志神秘主义观念的影响,Detmold的论述仍然比较深刻地探讨普通法理性这一特点的重要法理学意涵,并特别揭示了其中的司法理性的意涵(不过,他本人没有使用这样的说法),The Unity of Law and Morality; 特别是 “Law as practical reason”中对“特殊性虚空”(particularity void)的讨论。 [236]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双方(或至少一方认为),案件中的重要事实,与任何先例都没有建立起类推关系。但是,一般来说,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将先例与案件之间建立“弱”的类推,即以“劝导性”的方式使用先例。因此,可以忽略这种情况,将它看作上述两种情况的特例或变体。而在实证主义的“自由裁量权”的学说中,却把这种情况看作是“疑难案件”的主要形式。这实际上违背了普通法通常的情况。 [237] Summers 概括了这几种可能的情形。Robert Summers, “Two Types of Substantive Reasons: the Core of a Theory of Common Law Justification”, Cornell Law Review (1978) 63. 5: 733ff. [238]而在实定法的体系中,疑难案件的产生,意味着法律的缺陷,要么是“若”不清楚,难以认定事实;要么是“若-即”的条件程式不完备,无法找到适用法律,需要立法机构来制定或修订法律。而如果象在普通法中理解的那样,控辩双方都提出了有理由的“若-即”,在实定法的立法理性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即使现实中出现了这种情况,也只不过证明法律缺乏更高阶的“若-即”的条件程式来解决疑难。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韦伯“偏爱”的形式理性法事实上与“诸神之争”下的“价值自由”之间有内在的紧张关系。 [239] Goodrich, “Antirrhesis: Polemecal Structure of Common Law Thought”, 59. [240]德沃金本人在《认真对待权利》中的论述,以及此后许多评论者(无论是赞成者、批评者,还是发展德沃金思想的学者),都似乎没有找到区别法律原则与法律外的各种价值(这些学者主要关注的是道德价值)的办法。正如我们下面所指出的:首先,法律内部并不包含各种价值;其次,法律本身确实包含与这些价值有关联的“法律原则”,这些“法律原则”就实现这些价值的技术空间做出了相关的“规定”。法律原则,实质上是将法律“规定”与法律之外的各种价值联系起来的程序技术的“内核”。从这个角度来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坏的“法律原则”,或者法官不认同的法律原则,因为正如德沃金认识到的(但并没有恰当地予以解释),法官可以采用某些法律原则将法律规则与他不认同的非法律价值联系起来。这样的世界,显然并非Alexander和 Kress所谓“所有世界中最糟的世界”(worst of all worlds),因为它既没有破坏“原则”潜在的道德意涵,也没有损害法律的规则意涵(或更准确说,程序意涵)。同样,这种程序色彩和技术意涵的法律原则观,也没有危及Detmold所谓“原则”(在我看来,他指的是“价值”)对认同(commitment)的要求。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分别参见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168以下;Larry Alexander and Ken Kress, “Against Legal Principles”,in Andrei Marmor ed. Law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Clarendon, 1995), 279-327;Detmold, The Unity of Law and Morality, chap. 4。在我看来,Alexander 和 Kress 的批评,主要是因为德沃金的法律原则概念的“实质化”色彩过重,“倡导了一种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具实质取向的法律理论”。而从本文的角度看,这种过度的“实质取向”恰恰损害了“实质”价值本身的“价值自由”特点,这一问题在其权利理论与法律解释理论的缺陷中都有所体现。有关德沃金思想的实质性,参见 P. S. Atiyah and R. S. Summers, Form and Substance in Anglo-American Law (Oxford: Clarendon, 1987), 263。关于“价值”背后的“自由”色彩,正如我们已经隐约指出的,在韦伯的理论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参见 Stephen Turner and Regis Factor, Max Weber and the Dispute over Reason and Valu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35-8. [241] 参见德沃金《法律帝国》,14-9。用必要指出的是,该案涉及的遗嘱法是一种制定法,不过这并不影响实质性的论述。我们可以假定,在所谓“普通法国度”的法律制度中,制定法的适用过程也广泛采用了普通法的“方法论”(法律推理技术),或者说一般的法律理性原则。参见 P. S. Atiyah, “Common law and Statute”, The Modern Law Review (1985), Vol.48, No.1, 3. [242]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一种带有立法理性色彩的实证主义的权利观。而德沃金的一些论述(尽管并非全部)确实容易引发这样的意涵。尤其他关于存在一个“正确答案” 的论述。参见D. MacCormick, “Dworkin as Pre-Bentamit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78) LXXXVII, No.4: 585-607. [243] 这里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将法官的行为与诉讼当事人的行为混淆起来了。Detmold 对原则、权衡与特殊化的分析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尽管他的论述在别的方面非常具有启发性。参见 Detmold, The Unity of Law and Morality, 特别是第4章。 [244] 如果原则具有绝对的权重,原则就转变为规则了。参见 Detmold, The Unity of Law and Morality, 83。从这个角度看,考虑到任何具体案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所有案件都涉及到不可妥协的冲突原则,但在例行案件中,往往一种原则具有压倒性的权重。因此,从司法理性的描述社会学观点出发,我们也可以把例行案件看作是疑难案件的一种极端情况。不过,从司法管理的角度来看,理性案件的判决往往转变为法律规则的运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实定法的“若-即”的条件程式。在现在这个所谓的“制定法的时代”中,就更是如此了。 [245] 参见阿蒂亚,《法律与近代社会》(范悦等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14。 [246]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7-8. [247] 参见Martha Nussbaum,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art 3. [248] 季卫东,“程序比较论”,《比较法研究》(1993)第7卷第1期,26-39。 [249] 这正是普通法理性的特点。关于普通法是基于原则的这一“深层结构”,参见A.W. B. Simpson, Legal Theory and Legal History (London: The Hambledon, 1987), 282ff. [250] 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136。 [251] 大陆法系的国家往往对由法官承担这一角色充满怀疑态度。无论就观念史,还是社会史而言,这种怀疑,都与立法理性与共和理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这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只能留待将来讨论。 [252]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历史悠久的“自助”(self-help)原则的“司法化”,这与本文第四部分讨论的普通法的历史形成有关。从普通法的法律理性看,直接管理的实践权利的技术,远远少于那些没有直接管理的技术。但普通法先例中体现的精神仍然能够渗透到后者那些没有直接管理的部分。 [253] Sally Ewing, “Formal Justice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Max Weber’s Sociology of Law”,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987) Vol.21, No.3: 251-76。确实可以在《经济与社会》中找到一些支持埃文观点的论述,例如,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13。但同样也能找到不少相反的论述,例如977等处。在这方面,显然象Trubek所言,韦伯的观点是比较模糊的,参见Trubek, “Max Weber on Law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254] 叶士朋:《欧洲法学史导论》(吕平义、苏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36。 [255] Stephen Perry, “Judicial Obligation, Precedent and the Common Law”,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87) Vol.7, No.2, 2. [256] 这里强调的英国法治的特点,与纽曼的论述有很大距离。有些大陆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指出英国的“法治”与司法程序有更密切的关系,参见R. C. Van Caenegem, “The ‘Rechtsstaa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Legal History, 185. [257] 有关普通法与中世纪法律,特别是封建法之间的关系,法律史学者论述甚丰,例如Murphy, “The Oldest Social Sciences?”强调,普通法诞生于中世纪的程序,在17世纪奠定了其传统的核心。 [258] 哈勒指出,普通法充斥着程序方面的各种形式或仪式。Hale, Th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of England, 17,并参见本文第四部分的相关论述。 [cclix][259] “从法律发展的出发点来看,仪式主义的功能在于实现抽象,在于法律形式的详细规定和角色中立化。这种法律形式逐渐独立于情境,可以从一个情境转移到另一个情境,并且作为形式,可以脱离冲突”,Luhmann,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aw, 125. [260] Gunther Teubner, “Substantive and Reflexive Elements in Modern Law”, Law & Society Review, Vol.17, No.2 (1983), 246ff. [261] 程序化与形式化的区别,就在于其中涉及的“反身”意涵,参见Teubner, “Substantive and Reflexive Elements in Modern Law”, 250-1,以及全文各处。 [262]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柯克判决理由的核心,既没有明确倡导司法审查的学说,也并非一种当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参见Stoner, 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 29. [263] 这与自然法哲学家所谓的“不可变的自然法”相对,Cromartie, Sir Matthew Hale, 31. [264] 在以往的一些分析中,学者要么撇开这种理性来寻求某种“高级法”的痕迹,关注英国法中的各种不同的价值,用一种受到立法理性强烈影响的思路来看待普通法的司法理性;要么无视这种理性在心智和制度上的重要作用,直接分析英国法背后的意识形态效果。套用哈特的说法,我们倒可以说这种对普通法的解释,要么是把普通法看作是一种“高贵的梦想”(noble dream),要么是戳穿这种“高贵的谎言”(noble lie),将普通法看作是一场“恶梦”(nightmare)。实际上,与其说柯克的论述反映了普通法中的“高级法”因素,倒不如用富勒的话说,是某种 “低级法”,参见 Lon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96;并参见99ff对柯克学说的程序意涵的讨论。 [265] 与Neumann的观点不同,参见Neumann, The Rule of Law, 183. [266]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166. [267] 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144。 [268] 参见Simpson的讨论,尽管他将普通法等同于习惯法,也同样流于简单化, “The Common Law and Legal Theory”, 84ff. [269] 转引自 Cross and Harris, Precedent in English Law, 32-3. [270] 从普通法的法律发展史来看,这一点与英国早期的多元法律制度、封建法律背景以及具体的令状制度的发展有关。 [271] 转引自 Postema, Bentham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71-4. [272] Luhmann,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aw, 48. [273] Luhmann, “The Self-Reproduction of Law and Its Limits”, in Essays on Self-refer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229ff. [274] Lon Fuller, Anatomy of the Law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68), 106. [275]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88。 [276] Van Caenegem认为,普通法特殊性来自其形成阶段独特的历史时机,即普通法的形成时期较大陆法律的“现代化”要稍早,而这时罗马法的复兴运动刚刚开始,尚不能提供成熟的“教授”法模式以供利用。因此,英国不得不利用自身的力量来塑造一种“普通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论述是我们这里描述的英国国家面对的治理问题与治理技术之间的“差距”的一个方面。参见Caenegem, The Birth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chap.4;与本文的看法不同,Caenegem认为这一特殊性,不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解释,而本文认为,这恰恰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参见 Caenegem, “Max Weber: Historian and Sociologist”, 212-4. [277] 叶士朋,《欧洲法学史导论》,83-90。 [278] R. C. Van Caenegem, The Birth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23ff。德、法都是在18-19世纪,通过罗马法的继受过程,借助所谓教授法,编纂了民族法意义上的法典。这与韦伯的论述是一致的: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65ff. [279]Caenegem, The Birth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88. [280] 有关英国法律发展的“特殊性”(正是这种历史特殊性缔造了韦伯眼中英国法的“理论”特殊性),参见John Hudson, The 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London: Longman, 1996), 233ff. [281] S. F. C. Milsom,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the Common Law (London: Butterworths, 1981), 11-23. [282] 有关国王的两个身体的论述,参见E.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283] 以下有关“金雀花改革”的论述,主要参考了 Hudson 的研究,参见Hudson, The 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chap.5. [284] 巡回法庭对地方行政事务进行的“司法”审查活动,突出表现了普通法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特点,尤其是在普通法的早期形成阶段,行政与司法活动的结合。参见 Murphy, “The Oldest Social Sciences?”, 199; J. H. Baker,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London: Butterworths, 1990), 19. [285] Baker,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15. [286] Caenegem, The Birth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33。事实上,从封建治理的逻辑来看,国王并没有能力,也无意取消其它法院的司法管辖权。而且从治理与宪政的斗争来看,随着推行“普通法”的王室法院逐渐演变为国立法院(national court),并具有越来越强的自主性,国王反而可能会借助教会法庭等力量来与之抗衡(例如大法官法院与星室法院)。这种在复杂的司法管辖权划分的情况下形成的多元法律格局,具有突出的中世纪法团秩序的特点,是英国法受中世纪诸多制度持久影响的又一例证,这一点直到清教革命,甚至18世纪才有了较大的变化。参见 Burgess, Absolute Monarchy and The Stuart Constitution, chap.5. [287] C. W. Brooks, “The Common Lawyers in England: c.1558-1642”, in Wilfred Prest ed. Lawyer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America (London: Croom Helm, 1981) 42. [288] 当然,在这方面,英国法与大陆法的差异,除了英国法早期发展的历史特点外,也与与英国法偏重“私法”的倾向有关。早期王室法院处理的法律案件主要是围绕土地占有权方面的大量纠纷,因此,整个普通法的法律理性受到了私法的法律技术与理性的强烈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来看,英格兰这种围绕私法问题进行的司法治理的方式,使英格兰的“法治”与欧陆强调公法体系的“法治”有很大差别。也许正是出于这一点,英国法的史学家才强调“土地法”作为所谓英国自由的基础的重要性。有关普通法作为一种“私法”为核心的治理。参见 Stephen Perry, “Judicial Obligation, Precedent and the Common Law”,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87, Vol.7, No.2: 218;马克尧,《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24,及第8章。 [289] S. F. C. Milsom, “Reas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law”,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London: the Hambledon Press, 1985), 150. [290] Caenegem, The Birth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17-9; Paul Brand,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Legal Profession (Oxford: Blackwell, 1992), 23. [291] Caenegem, The Birth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34. [292] Baker,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21ff. [293] 马克尧,《英国封建社会研究》,12;Caenegem, The Birth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11;Milsom, “Reas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Law”, 154ff. [294] Sugarman, “Law, Economy and the State in England, 1750-1914: Some Major Issues”, 216. [295] 韦伯也隐约地提到了这一差别对两种法律制度的影响,参见 Treiber, “‘Elective Affinities’ between Weber’s Sociology of Religion and Sociology of Law”, 835-8. [296] Hudson, The 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142. [297] 参见 Baker,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chap.4; Caenegem, The Birth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chap.2. [298] Caenegem, The Birth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39, 41. [299] Baker,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63. [300] Milsom,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the Common Law, 60. [301] Baker,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67. [302] Baker,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84ff. [303] Milsom, “Law and Fact in Legal Development”,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171ff. [304] Baker,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86ff. [305] John M. Mitnick, “From Neighbor-Witness to Judge of Proof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Civil Jurors”,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Vol. 32, No.3 (1981), 201-35. [306] Sir John Davies 语,转引自 Sommerville,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England, 1603-1640, 89-90. [307] 当然另一个重要的意涵是普通法是程序中心的法律,参见 Hale, Th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of England, 16ff. [308] 参见 Kenneth Pennington, The Prince and the Law, 1200-1600: Sovereignty and Rights i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不过,作者并未考虑立法理性与司法理性两种不同的倾向之间的张力的关系,而这一“有意的”忽视使他运用了当代普通法的司法理性来理解欧陆诸多带有突出立法理性倾向的学说,如博丹(Jean Bodin)。而这一区别,对于我们理解普通法的程序技术的社会理论意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09] Milsom, “The Nature of Blackstone’s Achievement”, 207;叶士朋指出,所谓“罗马法”与民法的“德国式的系统化”的法律文化有很大差异,前者是强调“公正乃是一个具体案例的适当解决”,认为法律是一种实践知识;“法其实仅是而已,其内容与诉讼法为中心”。这些“罗马法”的法律文化特征,与我们这里概括的普通法的司法理性,毫无二致。参见叶士朋,《欧洲法学史导论》,68-70。 [310] William Bouwsma, “Lawyers and Early Modern Cul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73)78: 303-27. [311] 例如 Sommerville,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England.1603-1640, 86. [312] 例如,王室法院诉讼必不可少的令状,从12世纪末到14世纪初,数目就翻了三番以上。 [313] Caenegem, The Birth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19ff. [314] Wilfrid Prest, “lawyer”, in Wilfrid Prest ed. The Profess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ondon: Croom Helm, 1982), 69. [315] Prest 编的两本书中都包含了对英国律师界规模的估计,参见 Lawyer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America;The Profess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316] J. A.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chap.2. [317] Simpson, “The Common Law and Legal Theory”, [318]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41. [319] John Reid, “ The Jurisprudence of Liberty”, in Ellis Sandoz ed. The Roots of Liberty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3), 147-231. [320] Gray, “Editor’s Introduction”, xx. [321] Gray, “Editor’s Introduction”, xiv. [322] Sommerville,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England, 1603-1640, 90. [323] Reid, “ The Jurisprudence of Liberty”. 在其中,Reid 提及,“律师不是政治理论家,但政治理论也不是法律,至少不是普通法”, 227. [324] Brooks, “The Common Lawyers in England: c.1558-1642”,54. [325] Sommerville,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England, 1603-1640, 86-7. [326] J. H. Baker, “The English Legal Profession: 1450-1550”, in Prest ed. Lawyer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America, 34-5. [327] 有关“文学政治” 这一“托克维尔命题”的论述,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74-183。以及笔者在“抽象社会”中对“意识形态政治”的讨论。 [328] 转引自Hil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17th Century England, 152. [329] 参见 Cromartie 的简明讨论,Alan Cromartie, “The Rule Of Law”, in John Morrill ed. Revolution and Restoration: England in the 1650s (London: Collins and Brown, 1992), 55-69. [330] 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之所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是因为它针对的是普通人,而相应来说,边沁的理论却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立法者的科学”。边沁,《政府片论》,并参见Milsom, “The Nature of Blackstone’s Achievement”. [33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81。 [332] Christopher Hill, Intellectual Origin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Revisted (Oxford: Clarendon, 1997), 204. [333] 以下的历史事实,参见 Hill, Intellectual Origin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205ff. [334]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培根的方案,也不是象后来的边沁一样,希望通过“公理化”实现“法典化”,建构一种象大陆的“教授法”一样的“书本法律”(text- law),他的这些公理,更多是为法律教育服务。参见 Simpson, Legal Theory and Legal History, 285-6. [335] Matthew Hale, “Preface”in Henry Rolle, Un Abridgement des Plusieurs Cases et Resolutions del Common Ley (London: 1688), 转引自Glenn Burgess, Absolute Monarchy and The Stuart Constit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7. [336] 有关欧洲“17世纪总危机”,参见“论抽象社会”中的讨论,7页以下。 [337] Patrick Collinson, The Elizabathan Puritan Movement (London: Methuen, 1967);有关英国宗教改革运动,修正史学“写”出了更为复杂的历史图景,参见Tyacke的综述:Nicholas Tyacke, “Introduction” to England’s Long Revolution 1500-1800 (London: OCL Press, 1998), 1-32. [338] Peter White, “The Via Media in the Early Stuart Church”, in Margot Todd ed. Reformation to Revolution: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ondon: Routledge, 1995), 80. [339] White, “The Via Media in the Early Stuart Church”, 79-94. [340] Daniel Little, Religion, Order, and Law: A Study in Pre-Revolutionary Engl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0), chap. 4. [341] Walter Travers 语,参见 Little, Religion, Order, and Law, 114. [342] William Perkins 语,Little, Religion, Order, and Law, 115, 117. [343] Little, Religion, Order, and Law, chap.3. [344] J. C. Davis, “Relig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5, 2(1992), 507-30. [345] Little, Religion, Order, and Law, 101. [346] 近来修正史学家开展的许多地方史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例如 W. J. Sheils, “Erecting the Discipline in Provincial England”, in James Kirk ed. Humanism and Reform: The Church in Europe, England and Scotland 1400-1643 (Oxford: Blackwell, 1991), 331-45. [347] Davis, “Relig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348] John Coffey, “Puritanism and Liberal Revisite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1, 4(1998), 985. [349] 参见 Zagorin 非常精彩的研究: Perez Zagorin, Ways of Lying: Dissimulation, Persecution, and Conform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9. [350] Ned Lukacher, Daemonic Figures: Shakespear and the Question of Consc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13. 不过,Lukacher 在此处,没有充分考虑在英国的天主教“良知”学说的复杂性。 [351] Little, Religion, Order, and Law, 143. [352] Little, Religion, Order, and Law, 153. [353] Alexander D’Entreves, The Medieval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The Humanities Press, 1959), 111. [354] Saunders, Anti-Lawyers, chap.2。这一观念显然与我们前面提到的中世纪的法团治理模式有关,参见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355] 在本文中,不可能深入讨论经院哲学中 conscientia 与 synderesis 两个概念之间的微妙区分,尽管这一区别对于我们这里探讨的“良知的治理”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参见 Timothy Potts, Conscience in Mediev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2ff, 45ff. [356] Doe, Fundamental Authority in Late Medieval English Law, chap.6讨论普通法传统中的“良知”观念。 [357] R. J. Schoeck, “Strageties of Rhetoric in St.German’s Doctor and Students”, in Richard Eales and David Sullivan ed.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Law (London: Hambledon, 1987), 82. [358]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纳尔逊在70年代早期就注意到“良知”制度的变化,对于西方文明史与比较文明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一篇不太为人注意的文章中,纳尔逊指出,决疑术这种“或然性的知识”对早期现代心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只是在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之后,对确定性的追求才改变了这一点,他还将这一洞见与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联系在一起讨论。参见 Benjamin Nelson, “Conscience and the Making of Early Modern Culture: the Protestant Ethics beyond Max Weber”, Sociological Review (1969) Vol.36: 4-21. [359] 参见 Thomas 对近来相当盛行的“决疑术”研究的总结性的论述,Keith Thomas, “Cases of Conscience in 17th Century”, in John Morrill et al ed. Public Duty and Private Conscience in 17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 Clarendon, 1994), 29-56。不过从韦伯的视角来看,“或然性”与“确定性”之区分,实为天主教,甚至路德宗与严格的加尔文宗及清教徒在生活风格方面最根本的差异。面对伦理,前者采用计算加总与多少平衡的做法,而后者却采用了要么是,要么不是的毫无弹性的态度。参见 Weber, “Anticritical Last Word on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115. [360] 可以说,普通法是现代社会中真正保留“决疑术”色彩的唯一重要制度。非常遗憾,我们不能在这里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参见 Costas Douzinas, Justice Miscarried: Ethics and Aesthetics in Law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Chap. 3. [361] 转引自 Zagorin, Ways of Lying, 191. [362] “indifferent”作为16、17世纪良知与法律观念中的重要概念,有非常复杂的涵义, [363] 上述有关桑德森良知思想的论述,参见Kevin T. Kelly, Conscience: Dictator or Guide? (London: Geoffrey Chapman, 1967), Chap.2. [364] 转引自Lewis, “Sir Edward Coke: His Theory of ‘Artificial Reason’ as a Context for Modern basic Legal Theory”, 337. [365] Lewis, “Sir Edward Coke: His Theory of ‘Artificial Reason’ as a Context for Modern basic Legal Theory”, 340ff。这一思想就是我们前面所探讨的普通法权衡各种权利实践技术时的主要考虑依据(例如里格斯诉帕尔默案)。 [366] 这里对普通法“习惯治理”的论述,参考了Tully对洛克的精彩研究。如果说洛克式的“司法治理”确实与宗教改革诸教派的“良知治理”不同,那恰恰是因为其中渗透了普通法的司法理性。只不过,洛克的这种“习惯治理”添加了边沁式的福利算术和18世纪以后的性格形塑的问题,这方面的复杂问题只能留给以后处理。参见 James Tully, “Governing Conduct”, in Edmund Leites ed. Conscience and Casuist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2-71. [367] 对比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5。 [368] 转引自 Saunders, Anti-Lawyers: Religion and the critics of law and State, 27. [369] Hans Shilling, “Confessionalization in the Empire: Religions and Societal Change in Germany Between 1555-1620”, in Religi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Early Modern Society, 205-45,特别是245对比德国与英荷的情况。 [370] E.W.Bockenforde,转引自 H. Kleger/A. Muller,“多数共识即公民宗教?论自由-保守主义国家理论中的政治宗教哲学”,《道风:汉语神学学刊》,第7期(1997),53-4。 [371] Thomas,“Cases of Conscience in 17th Century”, 30. [372] Stephen Toulmin, 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373] 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76。 [374] Weber, “Anticritical Last Word on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124. [375]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55. [376]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意回避了“纪律”的问题和相应的清教伦理在政治上的意涵:“我们特意不以历史较长的新教教会这样的客观社会制度作为我们的出发点,也没有将出发点放在其伦理道德影响上,更没有放在极其重要的教会纪律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18,译文略有改动。 Little指出了这一点,但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Little, Religion, Order, and Law: A Study in Pre-Revolutionary England, 26。韦伯在1910年与Rachfahl围绕《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展开的激烈争论中,他简单地提及了这一点,指出“教派”对于美国民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一战后,面对德国重建的问题,他甚至赋予了这种自愿、排他的美国“教派”模式以更为重要的意涵。从某种意义上讲,韦伯这里倡导的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自主的共同体,既不同于“信条化的国家”,也不同于孤立的个人。对这方面问题的理解,仍有待更深入的探讨。参见Weber, “Anticritical Last Word on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1118; Roth and Schluchter, 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116. [377]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Sect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n H.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 From Max Weber (London: Routledge, 1991), 302-22. [378] 普通法在契约(合同)与“侵权行为”(tort)方面的历史发展,法律史学者论述甚多,例如 Milsom, “Reas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Law”, 154ff; Baker,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27, 73-5, Chap. 19. [379] 有关“践行的预定派”与“教义的预定派”(credal predestinarians)的区分,参见 Peter Lake, “Calvinism and the English Church 1570-1635”, in Todd ed. Reformation to Revolution,183-5. [380]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593;以及“中间反思”,311以下。不过韦伯并未象后来德国的历史学家那样深入研究这些入世禁欲主义的现世政治影响。 [381] 韦伯,《宗教社会学文集》“前言”,15,译文有改动。 [382] 许多学者仅将这段话看作是韦伯晚年“价值多元论”的反映,这样固然不能说错,但未免稍嫌简单化。事实上,有关韦伯的“多元理性化”观念与他的“普遍历史” 概念和“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殊性”的理论之间的冲突,学者们(以施路赫特为一方,蒙森为另一方)尽管争论不休却至今也未能给出满意的答案。而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是理解韦伯理性化理论的关键环节。所以,我们对普通法理性化的分析,并非要从多元主义或相对主义的立场出发,来批评韦伯陷入了大陆法系的“欧陆中心观”(这样的批评,往往充斥了韦伯当年嗤之以鼻的“怨恨”情绪),而是尝试在普通法的理性和理性化中,发现更具张力和复杂性,从而也是更具能动性的力量,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普通法才具有普遍历史的意涵。Huff 受 Benjamin Nelson 的影响,也注意到这一点,”On Weber, Law, and Universalism”. [383] 这就是为什么韦伯在运用比较宗教社会学分析对具有各种不同的终极通经和目标取向的理性化进行研究后,仍强调最终还是要建立一种理性主义本身的类型学和社会学。韦伯,“中间反思”,303;并参见本文第二部分有关韦伯“理性”思想的论述。 [384] 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正是纽曼对英国“法治”的论述,它突出地体现了传统观点的问题。尽管纽曼清楚地意识到,英国资本主义的亚当·斯密系统,其“自然秩序”学说的理性深受自然法的影响。但从纽曼多少有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思路来看,完全不考虑英格兰的普通法理性与亚当·斯密的自然法社会理论之间的分歧与张力。这个事实,尽管非常普通,但却经常受到忽视。所谓“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观念阐述,最初恰恰来自苏格兰,属于所谓“立法者的科学”的一部分,正如苏格兰是一个深受自然法与教会法影响的“国度”(不属于普通法国家,与英格兰的法律有着很大的不同)一样,这一“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同样有浓厚的自然法与神圣法的背景。“经济自由主义”,“法律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并非同一种“自由主义”。倒不如说,正是它们之间在相容下的张力,而非总体性的汇合,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重要条件。 [385] 韦伯指出,现代早期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产生于 科层理性最发达的国度,而只是在今天〔这一段落写于1918年――引者按〕,科层制与资本主义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49n.a. [386] Hale, “Sir Matthew Hale’s Criticism on Hobbes’s Dialogue of the Common Laws”, 501. [387] 因此,德国“法治国”的困境已经昭示了诸多所谓“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的内在痼疾,即也许容易自上而下地建立某种貌似“现代”的制度,推行某种最 “现代”的观念形态,但却难以深入地建立真正多元、能动的理性化机制。而且这些国家推动所谓“现代”制度建设的一元化权威,往往对“无序”或“失范”抱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对普通人自身的努力与尝试满怀狐疑。因此,正如德国历史展现的一样,官僚科层体制几乎往往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内,就会从所谓的“自由”或 “现代”的守卫者与推动者,转变为理性化的障碍或者赘疣。在这方面,前面论及的韦伯针对“凯撒制”的批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涵。 [388] 德沃金认为,这种“不可决定性”并非缺省状态,需要正面的理由(positive reason)支撑,而不仅仅靠否定,否则就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混为一谈了。不过,现代社会的法律面对的“不可决定性”要远比德沃金的分析复杂。法律,尤其司法理性,既面对德沃金式的“不可决定性”,还需要面对他所谓的“不确定性”(托伊布讷式的“不可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后者给立法活动和司法解释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同时司法理性还要求法官能够跨越所谓的“特殊性虚空”。这三者,正是现代社会的“偶变”法律的内在张力,它对法律的程序化与法律行动者的伦理理性化提出的要求,比德沃金、托伊布讷和卢曼所设想得更为艰巨。不过,也许德沃金许诺的一个更大规模的研究计划会比他的短文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当然,我多少有些怀疑)。分别参见 Ronald Dworkin, “Indeterminacy and Law”, in Guest ed. Positivism Today, 1-9; Gunther Teubner, “And God Laughed…: Indeterminacy, self-reference and paradox in law”, in Christian Joerges and David Trubek ed. Critical Legal Thought: An American-German Debate (Baden Bad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1989), 399-434; Detmold,”Law as Practical Reason”. [389] 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40,译文略有改动。 [390] 韦伯针对“科学”(wissenschaft)这一“天职”的论述,以及他有关“价值自由”,科学中的“客观性”等问题的分析,可以在许多方面帮助我们理解法律职业人士的伦理理性化和个性形塑与普通社会成员伦理理性化和个性形塑之间的复杂关系。 [391]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01. [392] Cromartie, Sir Matthew Hale. [393] 转引自 Saunders, Anti-Lawyers: Religion and the critics of law and State, 59. [394] Cromartie, Sir Matthew Hale, 235. [395] Charles Gray, “Editor’s Introduction”, xvi. [396] Full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397] 德国“法治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这种社会秩序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信念与责任之间的二律背反结构,利维坦也许在不经意之间就变成了Behemoth这样的庞然怪兽。 [398] 从普通法的历史来看,把案件提交给设置在伦敦的王室法院来处置,无论从时间还是收费来说,本身都是一个成本高昂的选择,更不用说在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各种 “腐败”现象(这一情况直到17世纪初期柯克推动的司法改革才有所改善),所以往往只有士绅和城市中的市民“新贵”能够负担这样的成本。不过如果就此认为,普通法封闭化的法律职业,事务律师与出庭律师之间的区分,复杂、甚至烦琐的法律技术,导致了司法诉讼费用的增加,从而使法律为少数有钱人服务,这固然不错,但却难免偏颇。在大陆法系中,例如德国,比起地方习惯法解决纠纷的办法,罗马法也一样被看作是代价高昂的“精英”法律。这也是德国学术界和政治界 “罗马派”与“日尔曼派”争执的一个焦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许这里涉及的只不过是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建构过程这一问题。在法律自主性、普遍性与精英主义式的参与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比起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通常的观点要复杂得多。当然这个问题需要联系现代社会所谓“公民权” (citizenship)的发展来进一步加以探讨,这只能留待将来了。 [399] 当然,这样的“普通法”能否真正实现大众化,则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从司法管理的社会学角度来看,例行案件的审理往往与基层法院面对的数量巨大的案件与时间、人力等方面的边界约束之间的冲突有关,这种冲突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普通法中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程序规则(如上诉法院不再接受新的事实),这些都与先例原则一样,使普通法始终面对“一贯性”、稳定性与实质正义,整个法律制度的正义与个别案例的正义之间的紧张,不过这种紧张,是否能够通过“立法理性”的措施来加以缓解,尚难下定论。 [400] 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二卷,12。有关耶林的这一思想与韦伯的价值理论的关系,参见 Turner and Factor, Max Weber: The Lawyer as Social Thinker, 55ff. [401] 赵晓力在他那篇简单但却颇有启发性的文章中探讨了民法传统中“通过法的治理”与自我技术之间的关联,参见“民法传统经典文本中‘人’的观念”,《北大法律评论》(1998),第1卷,第1辑,130-42。 [402]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55. [403] 韦伯写于1909年的一段文字,Roth 和 Schluchter 作为他们著作的题记。参见 Roth and Schluchter, 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 扉页。 [404] Detmold,“Law as Practical Reason”, 470. [405] 我们在“论抽象社会”中,着重探讨了“能动的理性化”问题。不过,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特别对于上一节提及的“平等化”的问题来说,立法理性的发展,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民主和法治结合起来的立法理性,试图解决“腐败”(corruption)这样的共和理论的经典难题,以及宗教战争带来的“内乱”和 “迫害”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只能留给另一篇文章来处理了。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不希望读者认为这篇文章是一篇攻击“立法理性”的檄文。只不过在现代社会中,立法理性正试图通过与科层理性的结合,成为“惟我独尊”的一元理性,在这种理性下形成的庇护型的法理权威,往往在缺乏自主秩序基础的发展中国家,试图自上而下地建立各种所谓“现代”或“理性”的制度,象德国当年的“法治国”一样,难以摆脱实质化与形式化的二元困局,使理性化与自由成为难以兼顾的二难抉择。而这一倾向的危险性,在社会理论方面,却没有引起充分的警惕,也缺乏足够的应对策略。毕竟,在现代社会理论中,立法理性一直发挥了压倒性的影响,而普通法式的司法理性,却受到广泛的忽视,因此,有必要将普通法的理性重新带入现代社会理论的“想象力”中。立法理性的危险,在经验方面,非常清楚地体现在拉美的“法律与发展”规划的失败事例中,参见Huff, “On Weber, Law, and Universalism”. [406] 例如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69. [407] 曾在西方发挥伦理理性化作用的力量,并不能直接在另一个国度发挥作用,这一点已经在诸如德国伦理文化协会的历史上看得很清楚,英美的这种道德协会,在德国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徒增一些空洞,乃至危险的浪漫主义式的乌托邦信念。 [408]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55-6. [409] Nat Hentoff, “Search and Seizure: Fragile Liberty”, in Joshua Rosenkranz and Bernard Schwartz ed., Reason and Passion: Justice Brennan’s Enduring Influence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97). [410] 对比韦伯,《世界经济通史》,291;类似的说法,参见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48. [411]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58. [412]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