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杰·科特雷尔:法律文化的概念
沈明 译
对于比较法律社会学来说,为法律文化寻求一个严格的概念显然是一件具有吸引力的事情;而这里所说的比较法律社会学就是一种对于不同的特定法律体系的特征进行一般性比较的法律社会学。实际上,可以把对于法律文化的关注看作是将法律社会学和比较法学这两种学术雄心加以融合的一种方式。
比较法学——对于世界上不同法律体系的比较[1]——提供了一种学术事业的范例,它为不同国家法律体系之间的比较发展出了一种明晰的概念性框架。例如,不论有怎样的困难,“法系”的思想还是认为,可以把不同国家法律体系或者其中的法律原则(doctrine)所包含的核心要素(包括发展中的和正在显露出来的法律原则的类型,以及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的风格)看作具有充分的相似性,因此可以进行一种富有成果的比较。与此同时,“法系”的思想还表明,为了某些特定的分析目的,这些具有可比性的法律体系或者法律体系的要素,作为一个群体,与其他性质上相差悬殊的法律体系或者法律体系的要素是能够相互区分的。[2]
然而,比较法学的主要概念性构架看来并不足以达到法律社会学的目的,因为后者所需要的概念性框架须可以用于比较那些与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不可分离的法律观念与实践,而不是上述法律原则。长久以来,比较法学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脱离了对法律原则和法律程序赖以存在的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我们可以称之为语境化的)基体(matrix)的比较分析,从而未能令人信服地展示出学说比较的理论价值。[3]比较法学似乎未能提供一种可行的框架,用以对于作为政治社会的样态(aspects)或者要素的法律或者法律体系进行比较。[4] 实际上,已经有学者指出,就解决种种有关比较的问题而言,比较法学的命运就是,它将在事实上变成法律社会学,[5] 或者至少是作为构建人文主义(humanistic)法律社会学一部分的“一种关于实在法的社会知识的混合物”。[6]
对于寻求一种适合于比较法律社会学的法律文化概念的人来说,如果对于法律体系及其特征要素的比较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话,他们就要保证这一概念将会包含或者确认那些不得不加以考虑的语境化基体中的全部要素。但是,就像文化概念本身一样,任何这类概念都存在不严密性和模糊性的困难,而这种不严密性和模糊性又正是人们加之于概念的需求以及通常要求概念在分析中发挥的作用所造成的结果。
本文关注于一般性地考察法律文化概念的理论功用。自1960年代后期以来,出于一种对于探求各种可能性的关注,美国法律社会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一直致力于详尽阐释并且应用这一概念。本文的第一部分考察了弗里德曼在过去这段四分之一世纪还多的时间里关于法律文化概念的种种不同的系统表述及其应用,并且评估了他对这一概念所具有的解释力的主张得到了多大程度的认可。这里强调了弗里德曼的工作,因为到目前为止,在晚近的比较法律社会学研究中,正是他,为获得一个清晰的法律文化概念做出了最为持久的努力,并为这一概念的效用做出了理论上的辩护和阐释。
我的观点是,在弗里德曼的著作中发展和运用的这一概念缺乏严密性,而且在某些关键方面表现出终极性的理论上的不连贯。然而,与其将这一结果归因于弗里德曼对于法律文化概念特别的苦心经营的一个缺陷,还不如说它是在法律理论分析中把“文化”用作一种解释性概念所带来的种种一般性问题的一个反映。实际上,也许不可能发展出一种在分析上具有充分严密性的法律文化的概念,使其具有作为法律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应具有的实在功用,尤其是,它还要能够在法律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标示出一种重要的解释性变量。
本文的其余部分致力于追问:尽管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然而在怎样一种情境中,法律文化的概念可能对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以及,某些通过发展法律文化的概念所探求的比较法律社会学的理论目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其他手段得以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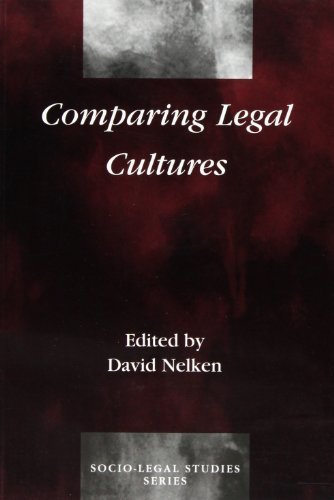 本章所关注的与法律文化的概念相关的主要问题,正如弗里德曼的著作所表述的那样,与下列内容相关:(1)概念的界定;(2)法律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各种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3)法律文化中原因的意义(causal significance)以及种种机制;(4)概念解释的重要性。尽管这是一些根本性问题,但对于它们的审视也建设性地强调了支配比较法律社会学的分析框架的准则。
本章所关注的与法律文化的概念相关的主要问题,正如弗里德曼的著作所表述的那样,与下列内容相关:(1)概念的界定;(2)法律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各种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3)法律文化中原因的意义(causal significance)以及种种机制;(4)概念解释的重要性。尽管这是一些根本性问题,但对于它们的审视也建设性地强调了支配比较法律社会学的分析框架的准则。
概念的界定
弗里德曼对于法律文化进行了广博的理论探讨,其中大多数呈现出了一种多样化特征:法律文化“指针对于法律体系的公共知识(public knowledge)、态度和行为模式”[7]。法律文化也可以是“与作为整体的文化有机相关的习俗本身”[8]。法律文化一般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些普通文化的组成部分——习俗、观念、行为与思维模式——它们以特定的方式改变社会力量,使其服从或者背离法律”[9]。因此,重点在于彼此密切相关的观念与行为模式二者各自的群集(clusters)。然而,在后来的表述中,法律文化又仅仅表现为观念性的:行为因素好像已经被抛弃了。法律文化包括“社会中人们保有的对于法律、法律体系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态度、评价和意见”[10],“人们对于法律体系的观念、态度、评价和信仰”[11]或者“在某些既定的社会中人们对于法律所持有的观念、态度、期待和意见”[12]。
以上这些表述的不精确性使人们很难弄清楚这一概念的精确所指,以及它所涵盖的种种因素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只要解释的重要意义尚未加之于法律文化的概念,只要这一概念仅仅被作为一个未加说明的(residual)范畴,并用于指称思维、信仰、实践和制度的一般情境——可以认为,法律正存乎其中——就不会有任何严肃的问题产生。弗里德曼在对一般文化的概念的某些讨论里似乎也暗示了这一进路。于是他提出了一种对于文化的“常理看法”(common sense view)的主张;文化仅仅指在特定环境中一系列个别的变化(the range of individual variations);[13] 民族文化是“一种集合体(aggregate),而且它难以和其他集合体进行比较”[14]。因此,文化表现为一种残余物(residue);由许多具体的、多样的以及可能是无关的因素所形成的偶然的、任意的型式。*
然而,对于弗里德曼的目标来说,这样的见解显然是不够的。像影子反映了未被看到的物体一样,希望凭借这种模式也能反映出一些问题;[15] 因此法律文化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个集合体。正如下文将要说明的那样,对弗里德曼来说,法律文化自身被理解为法律发展中的一个原因性因素(causal factor)[“至少在某些终极的意义上”,它(法律文化)“创制了法律”[16]],并因此成为法律社会学的理论阐释中的一个精髓性组成部分。由于这个原因,这一概念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更加严密的界定。然而,这里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含义使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在人类学家著作中常见的“文化”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含义。[17]
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及其相互关系
弗里德曼曾说,“人们可以在许多抽象的层面上谈论法律文化”[18]。每个国家/民族(nation)都有一种法律文化;[19] 法律文化能够描述“某一整体法律体系的潜在特征——其主流观念、品味与风格”[20];每一个国家或者社会都有它自己的法律文化,而且没有任何两个是完全相似的。[21] 另一方面,弗里德曼写作了大量有关他称之为现代性的法律文化(legal culture of modernity)或者现代法律文化(modern legal culture)的著作,这种现代性的法律文化或者现代法律文化正是许多当代社会的特征性表现;[22] 此外,他还撰写了若干有关西方法律文化[23]甚至正在兴起的世界法律文化[24]的著作。
然而,特别是在弗里德曼较晚近的著作中,他再一次着重强调了国家间或者民族间法律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阵列”(a dizzying array of cultures)——的多元观念。[25] 例如,在美国,法律文化就可以区分为:富人与穷人的,黑人、白人或亚裔人的,蓝领工人或白领职员(steelworkers or accountants)的,男人、女人与儿童的,等等;[26] “要为我们所选择的任何一个特定群体界定出一种区分的模式都应该是可能的”[27]。一个复杂的社会具有一种复杂的法律文化。[28] 美国法律文化并不是一种而是多种文化:“有法律保守主义者、法律自由主义者,以及它们的各种各样的变种和亚种。在各个具体群体的内部,法律文化包含了特定的态度,无论如何,这种态度都倾向于前后一致,彼此照应,形成种种具有相关态度的集合。”[29]
法律文化的概念由此向两个方向延伸。一方面,它指向那些对于极其广阔的历史趋势或历史运动的宽泛的比较和认同,而这种历史趋势和运动显然超出了民族或者国家法律体系的边界。另一方面,正如在社会科学层面上对法律文化概念的理解那样,人们援引它来认识法律多元主义的各种常见论题。[30] 这种广泛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它是一个相当微妙的概念。法律文化并非显示为一个单一的概念,它标示了对于文化层次和文化畛域的一种巨大的、多层面的概括,而且文化层次和畛域在内容、范围、影响以及它们与国家法律体系的制度、实践与知识的相互关系上是不断变化的。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问及有关法律文化与国家法律体系特定方面关系的某些具体问题时,法律文化这种高度不确定的观念就会给它在理论上的应用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如果法律文化涉及如此之多的文化层次和文化畛域(因为法律文化本身观念范围的不确定性,这些文化层次和文化畛域的范围最终是不确定的),那么就仍然存在着如何确定将此概念作为比较法律社会学中的一个理论构件加以运用的问题。
弗里德曼常常描述法律文化的某种基本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某些方面可能贯穿了上述不同的文化层次或文化畛域。他以一种粗略的方式——在这方面使人联想起萨维尼[31]——区分“完成特定法律任务的社会成员”[32]的法律文化和其他公民的法律文化。被弗里德曼视为“特别重要的”[33]法律职业者(professionals)的法律文化是“内部的”法律文化。在与之相对应的意义上,弗里德曼使用了“外部的”[34]、“通俗的”[35]或“外行的”[36]法律文化这几种不同的说法。可是,“内部的”与“外部的”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仍然很不清晰。为什么内部法律文化在社会学意义上一定要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呢?为什么恰恰是法律职业者的行为与态度对法律体系中所要求的模式具有重大的影响呢?[37] 看不出有什么显而易见原因。正如下文将要论述的,考虑到法律文化的概念倾向于解释许多对于法律体系的运作有着重大社会意义的东西,这些问题是颇为关键的。
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法律家(lawyers)的法律思维必然由其文化所决定,而且文化决定了法律思维变化的限度。[38] 内部法律文化反映出了外行(或外部)法律文化的主要特征。[39] 尽管如此,在他看来,不同种类的职业法律推理——如果它指的是对于法律裁决理由的正式、权威陈述的话——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法律推理可能倾向于封闭或者开放,创立新的原则或者抵制创新。不同类型的法律体系可以按照对其起支配作用的推理的不同类型来加以划分。诸如法条主义(legalism)、对于法律拟制的依赖、类比推理的运用,以及司法语言与风格的具体表现之类的问题,都能够与这些分类联系起来。
尽管弗里德曼明确认定上述各种问题都是内部法律文化的表达或产物,然而,通过他的论述,我们仍然难以清晰地看出它们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同样地,内部法律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如何与比较法学者所认为的法律体系或法系的“风格”[40]相区别,也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然而弗里德曼暗示,法系的思想对于法律社会学来说并无用处,因为法系之间在风格上的差异并不必然与法律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相关联。因此,与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同,法系之间差异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可能相对而言是微不足道的。[41] 但是,如果说这是由于法系仅仅是建立在对于某些特征的专断统合的基础上的话,那么这似乎也可以是法律文化的一个特征,至少在它的某些形态上是如此,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法律文化也能被视为仅仅是一系列个别的变化(a range of individual variations),文化自身就是“一种集合体”。
下文将会谈到,对于内部与外部法律文化之间的社会学关系的解释并不明晰,而这种模糊性给法律文化的解释性功用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产生这种模糊性的原因似乎是明了的,然而,如上文所述,弗里德曼强调法律文化层次与文化畛域的多样性和多重性,但他又暗示了观念、实践、价值和传统中的极为多样化的因素所具有的统一性,而且在这一层面上,他始终坚持使用法律文化的概念。这样一来,法律文化的概念的运用就支持了“内部”法律文化的观点,而“内部”法律文化作为一个统一体是与“外部”法律文化相对应的。
相比较而言,例如,在韦伯对于法律思想的风格及其所赖以发展的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充分而又精湛的分析中,他追溯了种种特定的影响因素。然而,无论是任何文化上的统一性概念的假定,还是将标明观念、信仰和价值的演进的极其复杂的历史模式——实际上不过是浩繁史料中共在(co-present)因素之间种种短暂而又偶然的遭遇而已——概念化,对于他来说都是不必要的。毫无疑问,韦伯涉及到了那些由智识、道德与社会条件构成的独特而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集合体——例如,像资本主义精神、西方的合理性或者与某种宗教的统治地位相联系的社会倾向(orientations)这样复杂的现象[42]——但是他似乎从来没有像这样地要引进文化这个关键的变量来加以解释。为了使研究更有条理,将文化“集合体”加以概念化也许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探究本身总是关涉一些相互区分的具体因素,例如,主体间的行为中所存在的特定宗教、经济、法律或政治倾向,人们能够识别出这些因素,并且在它们和集合体之间建立起关联。
法律文化的原因意义与原因机制
法律文化的概念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对于弗里德曼来说,正是这一概念,在确定法律体系运作的社会环境时,对一种至关重要的因素做出了具体界定。法律文化“决定了人们何时、何地、为什么诉诸法律、法律制度或法律程序,以及他们在什么时候会选择其他制度或者什么都不做”;它“使一切都运作起来”,而且是解释法律运作的关键性变量;将法律文化纳入法律的图景中“就好像给钟上紧发条或者给机器接通电源一样”[43]。这就是对于法律文化的原因意义的毫不含糊的断言。
特别是在1975年出版的《法律制度》一书中,弗里德曼对于像他那样理解法律文化影响法律体系运作的理由给出了一个相对详尽的说明。社会力量产生了一种变革的推动力,但并非直接作用于法律制度。[44] 利益不得不被转变为需求,而需求必须被成功地加之于法律制度,以便产生出“法令律例”(legal acts)(例如新的法律)来。法律文化的运作塑造了需求,而它又通过自身表达出的态度实现或者允许这种从利益到需求的转化;[45] 法律文化还决定了法律制度回应这些需求的方式。然而,在后一种能力中,法律文化(推想应该是既包括内部的又包括外部的)的运作塑造了一些“结构”[46]。这是法律制度本身的结构,例如直接和间接作用于法律制度的规则、权力和影响力的体系。[47] 但是,当这些结构性因素运作以抵制或者适应需求时,弗里德曼却急于否认这样一种观点: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法律体系本身作为一种体系,做出了回应。“真正的力量,真正的人民”(real forces, real people)在起作用,“对利益集团具体的反对在法律制度内部或者通过法律体系表现出来”[48]。尽管如此,法律制度——程序上的和学说上的结构——“确实有一些影响;但确切地说,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程度,我们并不知道”[49]。(弗里德曼)运用了拔河中的绳子的类比。法律制度就是这根绳子,它可以被拉伸到某一程度,或许它本身的重量和体积也增加了一些惯性因素;但是绳子却几乎不能决定谁会赢得这场比赛。
这里谈到的法律文化的原因机制确实还有很多含混之处,但弗里德曼观点的基本轮廓已经是足够清晰了。某些问题需要得到个别的法律解决方案,或者,某些利益需要加以保护,这些需求都摆在了法律体系的面前,而法律文化则控制着这些需求的产生步伐。而且,法律文化似乎也以更加模糊和复杂的方式决定了法律体系的回应。看起来,这种决定似乎是部分地通过内部法律文化塑造法律结构的运作,部分地通过反映权力和影响力的社会配置的种种“外部的”压力,才得以实现的。二者对于法律体系的种种回应都有影响。
因此,问题还是法律文化的相对无差异特征——或者,至少存在着这样一种困难,即难于将弗里德曼对于作用于法律体系的塑造因素不得不给出的说明,与上文所讨论过的多样性的法律文化之间极其复杂的相互影响的意象联系起来。法律文化的概念解释的东西太多了。实际上,它似乎解释了法律体系中的一切,不论是发生的还是没有发生的。然而,与此同时,它又几乎没有解释什么,法律文化承载的内涵太多,因为当法律文化本身承载着这样一个由各种因素构成的不确定的集合,并且运用于这样一套不确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标准时,归入法律文化的如此丰富的内涵就无法认定任何特定的要素——而出于法律社会学上的探究的目的,我们应该能够看出,这些要素对社会中的法律的情境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个概念的解释意义
为了消除怀疑,弗里德曼不时地承认法律文化概念的模糊性;它是“一个抽象而且含糊的概念”[50]。关于法律文化的论断“至多是建立在不牢靠的论据基础上”[51]。“针对于这种状况,我只能估计、解释以及推断”[52]。一种阐释,“与其说是对数据的解说,倒不如说它更可能是对于数据所可能显示的东西的一种猜测”[53]。那么为什么还要维系这样一个难以驾驭的概念呢?弗里德曼著作中隐含的答案似乎是,这个概念所具有的艺术功能大于科学功能;它使人们得以勾勒出对于一般趋势的印象。好讼可能成为某些国家法律文化的一个方面:“无论如何,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4]。此外,由于在过去的数年中,弗里德曼的著述重又着眼于不同国家——特别是美国——公民诉诸法律的问题,将此事件认同为一种法律文化的想法,使他调整了自己对于相关文化的解释,以能适应对于下述社会学现实的变化中的阐释: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中,公民参与国家法律制度的程度与性质存在着变化。
就这样,法律文化的思想已经能够包括下述观念:法律正在设法向生活中更广阔的领域渗透;在某些国家中,自觉主张权利的意识正在增长;[55] 对于正义和补偿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普遍期待;[56] 作为社会生活一个组成部分的法律确实多起来了;[57] 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一种选择的文化已经变得普遍了,在这种文化中,人们期待能够形构(formulate)、表达并实现个人选择,而且,如果必要的话,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追求这些选择的目标。[58]
弗里德曼并不掩饰他对于这些论题的讨论常常是仅凭印象的:更像是画家对于景物的描绘,而非测量员对于地形的度量。法律文化概念的魅力在于它似乎暗示了一些重要但却不确定的事物的某种变化方式——这些事物尤其与社会信仰、观点、价值和前景展望中的普遍变化所具有的意义相关联,不能简单地把它囊括在一种关于社会行为的可验证假说之中,而这种社会行为又是美国的法律与社会(law and society)研究通常所探究的对象。对于法律文化的阐述(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运用行为的语词进行推断、暗示——却不解释;以及,在那些不能轻易得到系统经验分析支持的地方,它则(仅仅是)描述一般性的印象(而已)。
弗里德曼对法律文化概念的解释中所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反映了文化概念本身的普遍困难。对于以系统经验阐释为目的的比较法律社会学来说,这些困难严重限制了这一概念的功用;而且,它们还限制了那些能够廓清社会现象之间一般因果关系或功能关系的理论的发展。
另一方面,某些社会环境中共存着由众多社会现象组成的若干集合,在这些群集的构成因素之间存在的精确关系并不明晰或者并不确定的情况下,文化——法律文化或许也是同样——的概念作为指称这些社会现象(思维与信仰的模式,行为与互动的模式,典型制度)的集合的一种方式,仍旧是有用的。文化是一个便利的概念,用它可以临时性地指称一种由社会实践、传统、理解与价值构成的、法律赖以存在的一般性环境。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文化之于法律社会学的重要性不亚于法系的观念之于比较法学的重要性:它是刻画由众多独特因素组成的大型集合体特征的一种手段,尽管它所运用的术语极其宽泛,而且也许或多或少是印象性的。
在其他方面,法律文化的概念在大多数分析语境中都能够被其他概念恰当地取代。法律文化所能涵盖的大多数内容都可以依据意识形态来加以考虑。正像弗里德曼对于法律文化的表述一样,法律意识形态与其说是一个统一体,毋宁说是对实践所包含、表达以及塑造的流行的观念、信仰、价值和态度的一种概括。然而,它与弗里德曼法律文化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律意识形态可以被认为是以一种相对具体的方式“系于”法律原则(doctrine)。法律意识形态不是法律原则,但它可以看作是由某些价值要素和认知观念所组成的,而这些价值因素和认知观念是由在法律制度中发展、阐释和适用法律原则的实践所预设、表达和塑造的。法律意识形态概念优于法律文化概念的一个长处在于,与法律文化相比,法律意识形态的本源及其创造和效果的机制能够提供一种更为具体的理念。
法律意识形态可以被看作是有意义地产生并维系于职业法律实践,并且通过有关公民意识的、制度化、职业化发展与应用的法律原则所带来的某种影响得到传播。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源于这些原则的实践与形式;法律原则本身必然会反映出意识形态的潮流,而它又不能控制这种思潮,而且,出于想要理解原则如何发展的愿望,意识形态思潮本身也值得加以分析。但是,强调智识与制度的机制似乎也很重要;通过这些机制,法律原则就有能力在职业法律实践的领域之外对“常识性”认识——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知识和信仰的形式——加以塑造。因此,尽管法律意识形态包括一个非常广泛而且有些不确定的植根于实践的观念领域,意识形态与原则之间的特定联系在理论上也是能够具体阐明的。
在当今社会,法律原则通常是破碎、错综复杂而且短暂的;它永远处在重构、增补以及修正的过程中,在政府政策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它常常将基于特殊情况的(particularistic)规定与对于官方裁量权的广泛授权高度结合到了一起。相比较而言,法律意识形态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当代法律原则所不可能实现的全部热切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其技术特征的“对立面”。法律意识形态体现了这样一些观念,例如:法律原则(doctrine)是永恒的或不证自明的有效原则(principle);自足的法律逻辑能够用于解决所有的法律争端;法律是一部由系统的规定构成的“无空白的”法规总集;或者,法律理念(ideas)成为圆通精致的价值的和谐体现。
在意识形态观念中发生了变化的法律原则,是以怎样的方式助益于构建或塑造社会认识以及信仰、态度和价值的结构的;以及作为原则的法律如何提供了一个渠道,以使思想与信仰的宽阔洪流能够被转变为循规蹈矩的实践——法律意识形态的概念为这些重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焦点。[59] 使用法律意识形态概念的另一个好处在于,要依据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倾向思考问题,以及要认识到意识形态的种种倾向可能彼此互有抵牾而且反映出了各式各样的社会经验,这些似乎都变得容易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倾向于落入那个——我们认为对于法律文化来说是真实的——陷阱:一个自负的(assuming)统一体的陷阱,其中至多是一些有可能专断地加以认同的集合体。但是,在较少约束的分析中,意识形态的概念基本适合于用以认定相当具体的价值系统和认知观念。
尽管价值和观念内部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然而以一种在事实上认可价值和观念为体系的方式进行的分析,仍为法律意识形态的概念所容许;而且,这一概念还促进了对于固守这些思想和信仰体系的认同,以及对于这些体系拒绝依经验加以修正的认可。它激发了对于意识形态体系结构及其修辞和象征作用的考察,并且容纳了对于种种意识形态思潮之间普遍存在着的冲突的认同。法律意识形态的概念也许比法律文化概念更加明确地强调了社会权力与思想信仰倾向之间的联系。例如,它关注于,对于法律体系的职业化的理论生产(doctrinal production)是怎样通过塑造这些思潮而作用于社会权力的。
法律文化的概念,至少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似乎最直接地关注因素的多样性,这些因素对于法律制度内部 “法令律例”的产生施加影响,而且被用来解释这些制度的特征和倾向中存在的差异,以及它们对于利益和需求的不同回应。关于职业化法律实践和原则的权力对于它们所存在的更加广阔的语境产生的影响,弗里德曼倾向于保持一种暧昧或者不可知论的态度;他宽泛地着眼于作为法律决定因素的总体文化环境的各个方面。
法律,通常在国家法律体系职业化实践的意义上,通过某些机制影响或者改变并因此有助于强化价值、信仰与认识的更为宽广的结构,就对于这些机制的探索而言,比较来说,法律意识形态分析所带给我们的可能是更易于驾驭的理论任务。尤其是,制度化、专业化操作的法律原则被当作是这个理论任务所特别关注的焦点,而不是影响法律体系的潜在无限多样性的文化渊源,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理论任务似乎就更加容易了。
然而,如上所概述,法律意识形态的概念也许不会特别地指向比较法律社会学的那些具体的工作,而正是这些工作,似乎激发了某些学者对于法律文化概念的运用。这里所说的比较法律社会学的工作就是,考虑国家法律制度中特定制度性差异的社会决定因素,或者公民参与职业化的法律及其运作机构的实践、型式(style)、组织机构或模式中所存在的差异。由于关注的焦点在于法律体系的多元化,这种探究似乎又回到了比较法学和法律社会学的交界处。然而,在此背景下,例如像莫简·达马斯卡的进路,[60]——在解释法律程序模式差异时,着眼于与政治结构和政治意识形态相关的特定变化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似乎比那些采纳法律文化的概念作为解释工具的研究具有更好的前景。
达马斯卡提出了一些变化因素并说明了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由此提供了一些分析“模式”[61]。因此,这种分析一方面是基于政府结构与程序性权威的理想类型,另一方面是基于政治权威取向的理想类型。它们被用来解释那些会被弗里德曼称为内部法律文化的因素,特别是法律机构与法律发展前景(outlook)中的种种差异,而人们又常常把这些差异与比较法学领域中公认的普通法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的差异联系起来。但是,达马斯卡否认自己有对于因果关系做出一般性判断的意图。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环境中,具有接近于解释模型特征的特殊法律制度的存在被认为通常不是决定,而是“证明(justify)或者支持了程序形态的某些特定群集”[62]。
达马斯卡的努力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似乎部分地“消解了”那些在普通法和大陆法两种不同程序体制的法律文化中可能会被看作是非常一般性的差异。[63]他暗示,比较法学中的法系概念不足以表征不同程序体制的独特形态,这首先是由于不同体制中(甚至在同一法系之内)实践的多样性,其次是由于在那些被聚积起来作为此一法系或者彼一法系特征的程序性要素之间明显地缺乏联系。
依照韦伯的方式,达马斯卡似乎认识到,除了追寻某些特定法律体系特有的、或多或少可以说是惟一的历史发展的群集之外,要描述文化复杂性的特征是不可能的。这些发展可以依据某些潜在的基础观念来理解,这些观念可以考虑被表述为:“能够将正义的种种形态塑造成可以识别的模式”[64]。这些(关于包括司法机构在内的政府机构,以及关于合法权威的基础的)设定的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产生出了程序体制的理想类型,这些理想类型便利了在实际的程序体制之间进行的比较。
对于纯粹或者理想类型(即那些依逻辑构造的概念,这些经过深思熟虑设计出来的概念并非为了描述经验事实,而只是为了把对于经验事实的阐释有机地组织起来)的运用似乎是将比较法律社会学中的两个至关重要的研究要件结合起来的一个重要途径。首先,它使得人们既有可能承认那些可能被当作法律文化的因素是无穷无尽的;又不至于落入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集合体”的陷阱。与此同时,它也便利了种种比较。
这种进路在韦伯对于广泛的文化集合体的研究中拥有其堪称经典的渊源。实际上,韦伯的全部著作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被视为聚焦于西方文化作为某种独一无二的集合体的特征。但是,理想类型的方法依其本性假定了:首先,决不能把它所指称的对象——作为纯粹为了智识省思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逻辑上统一的、自足的观念——相当于逻辑上构造出来的自足的经验事实;其次,它还假定,通过理想类型组织起来的经验现象,至多不过是依研究的特定目的从无限的历史经历中选择出来的一组资料。
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们承认文化(以及,特别是这里所说的法律文化)依其本性并没有可以测度、观察或者体验的经验性存在;相反,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反而倒是可以产生出测度、观察或者体验特定社会现象——包括法律的现象——的方法来。然而,仅当“文化”的思想被彻底转变为若干套逻辑上精心构造的理想类型的时候,这似乎才是可能的。
然而,也可能存在某些限制性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法律文化的概念,在类似于弗里德曼的描述与经验的意义上,获得了更为精确的效用。换句话说,可能存在这样一些情境,使我们可以恰当地把法律文化作为一个经验性的范畴,而不仅仅是把它作为一套理想类型的建构。
在某些条件下,不仅通过表达文化特征的理想类型从大量资料中进行抽象可能行得通,而且,试图按照描述性人类学的方式(ethnographically)描述并且记录由——例如可能构成弗里德曼所说的外部法律文化的——态度、价值、习俗和社会行为方式构成的丰富而且复杂的群集(cluster)或者集合(aggregate)也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仅当相关文化集合体规模较小而且封闭、使文化的区分和辨认不太成问题的时候,它们才可能实现。
例如,布朗内斯劳·马林诺夫斯基丰富而又经典的描述性人类学(ethnography)展示出了那种他当然可以视之为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法律文化的东西。[65] 马林诺斯基人种学研究的范围(scope)并非主要取决于追踪特定变化因素的努力,而是取决于它的这样一种关注:在对复杂而且无差异的文化整体的解说中揭示社会的结构、变化、连续性,以及功能关系。对于文化集合体的刻画由此得到了界定,而且,由于美拉尼西亚人的(Melanesian)社会规模相对较小并由此形成了地理上的隔绝,就描述性人类学研究的目的而言,文化集合体的描述也变得易于处理和驾驭了。
然而,应当强调的是,由于牵涉到作为总体(totality)的文化集合体以及交织于其中的多种多样极其复杂的因素,“法律”(the legal)必定未与文化的其他方面发生分化,或者分化仅仅是暂时性的、不确定的。因此,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未分化的集合体,仅仅是文化的某一方面(即对于文化的一种见解)。严格说来,并不存在法律文化,它只不过是观察者出于一种法律现实作用的立场所见的文化而已。文化的领域内仍然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马林诺夫斯基的相当模糊的文化概念”[66],就其仅指在地理上(因此,从社会学观点看来,是带有任意性的)有限空间范围内由人种学记录所描绘的社会生活的总体而言,避免了这些问题。仅当人们把这个总体作为某种完整而又独特的统一体,而努力将其理论化的时候,[67] 这一概念就变得大有问题了。[68]
在对当代大型社会——例如欧洲或者北美——的研究中,这些观念也并非毫不相关。在这些当代社会的语境中,如果相关文化集合体的广度能够被限定在与诸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所达到的范围相仿的程度之内,法律文化概念的模糊性以及评估——弗里德曼指出与法律制度内部变化相关的——法律文化的无数层面和领域之间的原因意义这两个问题似乎并不太突出。在当代社会中,当关注的焦点从统一的、集中的国家法律体系转移到多元规则体系时,就先前讨论的弗里德曼的著作而言,这些多元体系的范围有时可能会反映出各种各样的法律文化的范围。显然,运用法律文化概念进行分析的可能性增加了,但这并非因为该概念在此种情境中取得了较为一致的内涵,而是因为,就像特罗布里恩德“法律文化”那样,文化集合体中多样化的因素作为一种纯粹实践性的存在(matter)变得更具地方性色彩,规模上受到严格约束或者限制,也似乎更加易于驾驭:例如,这些多样化的因素看起来更符合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的“浓描”(thick description)所指称的对象了。[69]
在人类学研究以及一些早期的法律社会学著作——例如尤金·埃利希的书[70]——中,与对于法律多元主义的关注相伴随的是一种对于文化变化的相对而言的高度敏感。在埃利希的书中,对于超越国家法律体系的多元法律管理(ordering)体系的强调意在精确地反映出这种变化,并且表明这样一种复杂性:伴随着它,态度、价值、信仰与习俗上的差异可能会在多种多样的管理(regulatory diversity)中被直接记录(register)下来。事实上,文化的概念可能尤其适合于这样一种描述性人类学研究,这种研究旨在把认知结构、价值和信仰体系、社会行为与管理结构的模式之间的相互交织描绘成一个存在于有限的社会场域(locality)中的相对未分化的复合物(complex)、一个复杂集合体——作为一个集合体,它自有其重要性(of interest),描绘成一幅整个社会生活错综复杂之网的图画(尽最大的实践可能性和实际可行性)。
但是,如上所述,这一进路使得人们对于“法律的”或者制度的因素难以保有一种独立的理论关注,这些制度因素可能被视为相当于,或者被置于社会组织的某些方面——在复杂社会中,这些方面或许会被看作具有法律的特性(distinctively legal)。要区分出“法律的”要素,就需要对文化的若干组成部分加以分析,并对要素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做出具体说明。但这恰恰正是在运用作为集合体的文化的观念时所寻求回避的东西,或者,至少看起来这种回避具有正当理由。似乎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类学开始注重于研究社会组织的具体管理、维护秩序或者关注纠纷的方面,而且通过分析,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将这些问题与社会生活的其他因素区分开来了,因此,与文献所运用的其他一系列同类概念相比,文化概念的显赫地位已经显示出一种失落的倾向了。[71]
有可能将弗里德曼所说的内部法律文化——即法律职业者的价值、态度,或许还有实践(前文已经提到了弗里德曼著作的含混之处)——看作是小规模文化集合体吗?依上文所述,答案似乎通常是否定的。根据人类学对于文化的描述性人类学表现(presentation)所作的研究,内部和外部法律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互区分,以及内部法律文化所独有的社会意义可能是什么,弗里德曼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不确定似乎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只要还把内部法律文化当作是文化,似乎就没有显然令人满意的办法把它从较大的文化集合体中分离出来,二者之间肯定会有千丝万缕的牵连。
尽管如此,就当代国家法律体系某些方面的分析而言,运用文化集合体的概念的前景也并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有限。运用文化的概念,对于小规模社会语境中的全部复杂因素加以综合,以及近来在对于美国民众法律意识的复杂的描述性人类学阐释上的若干重要努力,这两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一工作,特别是与阿默斯特法律意识形态与法律程序研究会(Amherst Seminar on Legal Ideology and Legal Processes)成员相关的工作,明确采纳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不是任何文化的观念,用以指出它所关注的焦点。与本文前述对于意识形态分析的取向相一致,这一关注焦点很显然主要在于国家法律制度在生成普通公民的社会认识、态度和价值的结构过程中的影响力;而较少关注散乱的认识、态度与价值塑造国家法律制度的运作的各种方式。另一方面,此类著述中的一些既从文化方面又从意识形态方面加以阐述。“法律语词和法律实践是文化的建构,这种建构的承载着很有影响的意义,不仅对那些训练有素的业内人士或者从事日常商业交易的人们来说是如此,对于普通人也是一样。”[72] 有很多文献都强调指出,在国家法律制度或者相对一体化的民众法律意识内部,普通人或者外行人的法律认识与律师以及其他法律职业者的法律认识之间存在着冲突、紧张和交涉。
一般来说,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当这种研究对于相对有限的社会语境的众多方面进行详细考察时,它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如,被视为社区(communities)的具体的城镇(towns);[73] 或者以律师事务所为背景的社会互动,[74] 法庭调解听证会[75]或者社会福利机构[76],对于法律含义的协商与谈判发生于这些场合之中。这些研究的解释力大部分来自于它们在社会互动的整个复杂语境中的详细描述性人类学记录。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法律体系及其运作、程序被看作是社会互动得以发生的背景,各式各样的民众意识在此背景中得以发展或者塑造,一种关于法律的特定关系因此得以维系。
在这一限度上,或许可以说这些研究是与法律文化直接相关的——特别是弗里德曼所说的内部和外部法律文化的互动。它们(这些研究)似乎使法律文化是许多偶然因素的集合体这一特征变成了一个优点。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概念的运用,使相关社会权力与确立或者商定法律含义的可能性(possibilities)之间的关系问题持续成为一个显明的焦点。有关民众法律意识的文献通常依赖于有效的描述性人类学:尤其是关注于特定社会语境的限制。它暗示了法律文化的概念在那些语境中所可能具有的效用。
然而,相对而言,这种文献似乎同样与追寻社会因果关系或者建构解释理论没有多少关系;它通常也没有寻求进行那种比较性的研究项目——而本文正是将它视为一种尤其突出比较的比较法律社会学的核心。描述性人类学对于民众法律意识的解释以及它对社会行为的表述似乎旨在阐释对于法律特定社会背景的复杂“浓描”。然而,这种文献一般也声言自己从属于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律社会学。[77]
综上所述,对于法律文化得出的一个总体结论是,法律文化这个概念的最大用处在于,它强调了包容当代国家法律制度的社会本体所具有的极度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曾经指出,法律文化可以被理解为由种种重叠交错的文化构成的具有广泛多样性的文化样态:有一些相对而言是地方性的(local),还有一些则更具普遍性(universal)。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对于“文化”这样一个笼统概念的依赖也会使对于特定的法律文化的理论认同变得成问题了。
目前对于法律的社会研究倾向于放弃或者拒绝许多来自于某种特定社会科学观念的传统认识,并且适当地、必不可少地采纳了一些解释方法,这些方法摒弃了实证主义者在此语境中对于 “科学”一词的运用的许多论断,因此,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可能就更易于倚重相对模糊的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概念。本文认为,除了在有限的而且是精心界定的情境中以外,这种倚赖似乎是一个错误,而且,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弗里德曼长期以来对于法律文化概念意蕴的苦心经营,就会发现在它的运用中存在的种种或许是特有的(endemic)问题。
不过,在社会研究的某些语境中,关于共在于某一时空中的种种社会要素构成的未分化集合体的思想可能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思想通过文化的概念得到了便利的表达。在对相对特定的社会语境的研究中,要临时性地囊括那个包容国家法律运作的整个语境化本体,法律文化的概念可能也是有用的。
更一般来说,文化一词可能适于而且有必要用作指称这样一些社会现象的群集:人们并不清楚它们相互之间的精确关系,但是它们作为集合整体的重要性却是清楚的,而且是需要加以强调的。通过这种方式,就或许可能对信仰、价值、认识与实践的复杂网络的特征加以刻画。而借用了描述性人类学方法的社会学研究同样可以恰当地寻求对它加以描述,这也许是一些更加具体的研究的开端,这些研究旨在探究法律原则和使法律原则得以制度化的实践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意义。
Roger Cotterrell, “The Concept of Legal Culture,” in David Nelken, ed., Comparing Legal Cultures, Dartmouth, 1997.
原载《比较法律文化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
[1] K. Zweigert and H. Kötz, 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aw, vol. 1, 2nd edn, trans. T. Wei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 [2] 参见,例如:K. Zweigert and H. Kötz, supra note 1, ch. 5; R. David, and J. E. C. Brierley, Major Legal Systems in the World Today, 3rd edn, London: Stevens, 1985, pp. 17~22. [3] 参见L. M. Friedman, The Legal System: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5, p. 201. [4] 参见M. R. Damaska, 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he Legal Proces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6~7. [5] 参见J. Hall, Comparative Law and Social The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10~15; R. David, and J. E. C. Brierley, supra note 2, p. 13. [6] J. Hall, supra note 5, ch. 2. [7]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3, p. 193. [8] Id. p. 194. [9] Id. p. 15. [10] L. M. Friedman, Law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7, p. 76. [11] L. M. Friedman, “Legal Culture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G. Teubner, ed., Dilemmas of Law in the Welfare State, Berlin: de Gruyter, 1986, pp. 13~27, at 17. [12] L. M. Friedman, The Republic of Choice: Law, Authority and Cul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13; 又见L. M. Friedman, Total Justice, Boston, Mass.: Beacon Press, 1985, p. 31; L. M. Friedman, “Is There a Modern Legal Culture?” Ratio Juris, vol. 7, 1994, pp. 117~131, at 118. [13]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2, pp. 212, 213. [14]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3, p. 209.* 原文为:“the contingent, even arbitrary, patterning produced by many specific, diverse and possibly unrelated factors.”疑有误。——译者注
[15]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2, p. 196. [16] Id. p. 197. [17] C.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4~5. [18]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3, p. 204; 参见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2, p. 120. [19]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3, p. 209. [20] Id. p. 15. [21] Id. p. 199. [22] Id. p. 204ff;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2. [23]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2, pp. 198~199; [24]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3, p. 220. [25]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2, p. 213. [26] Id. p. 213. [27] Id. p. 120. [28] Id. p. 96. [29]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2, p. 98; 又见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1, p. 17. [30] 参见S. E. Merry, “Legal Pluralism”, Law and Society Review, vol. 22, 1998, pp. 869~896. [31] F. K. von Savigny, Of the Vocation of Our Age for Legislation and Jurisprudence, trans. A. Hayward, original 1831, reprinted New York: Arno Press, 1975, pp. 28~29. [32]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3, p. 223. [33] Id. p. 194. [34] Id. p. 223;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1, p. 17. [35]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2, p. 4. [36]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0, p. 76. [37] 参见L. M. Friedman, supra note 3, p. 194. [38] Id. p. 206. [39]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0, p. 79. [40] K. Zweigert and H. Kötz, supra note 1, p. 68ff. [41]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3, p. 202;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0, pp.75~76. [42] 参见,例如H. H. Girth and C.W.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48, ch. 11. [43]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0, p. 76. [44]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3, pp. 15, 153; 又见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2, p. 118. [45]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3, pp. 150, 193. [46] Id. p. 209. [47] Id. p. 150. [48] Id. p. 155. [49] Id. p. 156. [50]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2, p. 95. [51]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3, p. 209. [52]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2, p. 198. [53]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2, p. 119. [54]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3, p. 212. [55] Id. pp. 210~211. [56]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2, pp. 43, 144;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1, p. 22;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2, p. 60. [57]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1, p. 20. [58] L. M. Friedman, supra note 12, p. 74. [59] R. Cotterrell, Law’s Community: Legal Theory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7~14. [60] M. R. Damaska, supra note 4. [61] Id. p. 14. [62] Id. [63] 详尽的讨论参见S. Goldstein, “On Comparing and Unifying Civil Procedural Systems”, in R. Cotterrell, ed., Process and Substance: Butterworth Lectures on Comparative Law, London: Butterworth, 1995, pp. 1~43. [64] M. R. Damaska, supra note 4, p. 5. [65] B. Malinowski, 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26. [66] R. Firth, “Malinowski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Anthropology”, in Ellen, et al., eds., Malinowski Between Two Worlds, 1988, pp. 12~42, at 16. [67] 参见B. Malinowski, 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4. [68] A. K. Paluch, “Malinowski’s Theory of Culture”, in Ellen, et al., eds., Malinowski Between Two Worlds, 1988, pp. 65~87. [69] C. Geertz, supra note 17, ch. 1. [70] E. Ehrlich,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trans. W. L. Moll, original 1936, reprinted New York: Arno Press, 1975. [71] 参见,例如F. G. Snyder, “Anthropology, Dispute Processes and Law: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vol. 8, 1981, pp. 141~180. [72] S. E. Merry, 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 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p. 8~9. [73] 例如,参见C. J. Greenhouse, Praying for Justice: Faith, Order and Community in an American Tow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74] 例如,参见A. Sarat and W. L. F. Felstiner, “Lawyers and Legal Consciousness: Law Talk in the Divorce Lawyer’s Office”, Yale Law Journal, vol. 98, 1989, pp. 1663~1688. [75] S. E. Merry, supra note 72. [76] A. Sarat, “‘The Law is All Over’: Power, Resistance and the Legal Consciousness of the Welfare Poor”, Yale Journal of Law and the Humanities, vol. 2, 1990, pp. 343~379. [77] A. Sarat, “Off to Meet the Wizard: Beyond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in the Search for a Post-Empiricist Sociology of Law”, Law and Social Inquiry, vol. 15, 1990, pp. 155~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