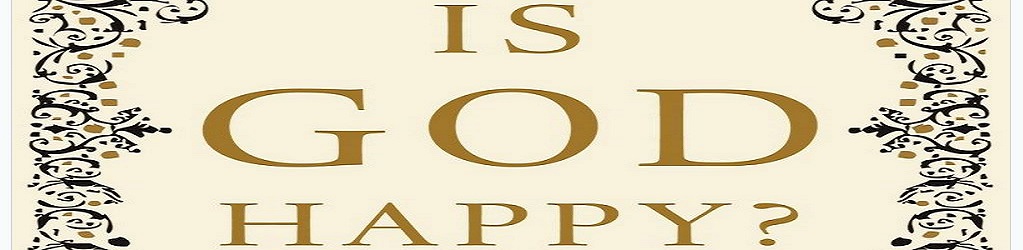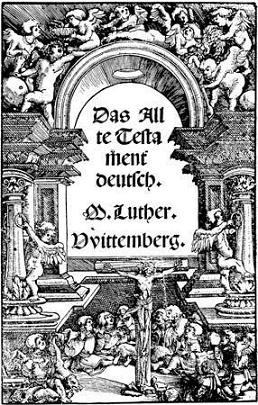A君惠览:
香港已经大热了吧,这儿还留着早春的寒意,海滩上刚出现溜狗的人。昨天散步,望见一条吃水挺深的渔舟,就想起上次你们姊妹俩来吃龙虾的情景。今年的会,恐怕还是来不了,真是抱歉,一拖再拖。这几年因为译经,连欧洲也不去了。而你知道,那些大教堂、寺院、城堡和羊皮纸抄本,是我多少年的朋友!
谢谢发来《时代论坛》的《摩西五经》书评。那是教会的刊物,文章写得蛮认真,但错了几处,待会儿再谈。先说你给神学院老师出的那道有趣的难题:“上帝造人,取的是他自己的形象,男人女人,都依照他的模样”(《创世记》1:27)。那么,上帝该是什么性别,是男是女?
传统的解释,造物主至大,超乎我们这个世界的时空,以至于不能用人类和自然界即“受造之物”的任何区别特征或分类法,例如眼耳口鼻和性别,来指认或定义。正统的犹太拉比连上帝的品性(神性)也很少讨论,因为那“奥秘之奥秘”不是人的理智和想象力可以把握的。耶和华至圣,为了和“异教邪神”划清界限,摩西十诫禁止塑造上帝的形象(《出埃及记》20:4)。根据这一诫命,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严禁塑造和叩拜偶像。但基督教在传布过程中对罗马帝国各民族的多神崇拜“陋习”有所妥协和利用,如把圣诞节定在罗马人祭祀的“太阳生日”,这项禁忌便松弛了。
所以你的难题,就经文而言,实际是问:人们通常对上帝的想象——画家笔下那位长髯飘拂、威严而仁慈的老者——是从何而来的?我想,这跟一些修辞性的称谓有关,例如称上帝为宇宙之“王”、子民之“父”、以色列的“丈夫”和“战士”。此外,以色列是古代近东的小民族,比起她的邻居,埃及、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的大帝国,文学发达得晚些。叙事元素和诗歌语汇,就有大量的借用,包括神话传说,特别是人格化的(anthropomorphic)神的形象与比喻。例如,用“右手”象征力量、胜利、拯救,便是古代近东文学的套喻。摩西举牧杖分芦海(七十士本:红海),以色列子民摆脱了法老追兵,这样歌唱耶和华:“你以右手降示荣耀,以大能之手,摧毁你的仇家……以你胸中怒火,焚敌如烧秕糠;以你微微鼻息,使急流垒起高墙”(《出埃及记》15:6)。这跟迦南(古巴勒斯坦)文献中雷神巴力(ba`al,本义主)的形象,实在相去不远。巴力是耶和华的死敌,这层对立关系,也容易让人产生上帝像是男性神的联想。
不过,《圣经》原文对上帝的“性别暗示”并没有一边倒。这是因为希伯来语名词分阴阳两性,“上帝”(’elohim)虽然是阳性复数,耶和华的其他许多名号和委婉称呼,却是阴性,要用“她”来指示(人称代词,名词、动词和介词的后缀等)。诸如造物主的圣灵(ruah),降世时祥云落处或“神在”(shekinah)、摩西领受的圣法(torah)、义人寻求的大智慧(hokmah),都是阴性名词。故而经文里上帝的神迹和训谕,是常在“她”的语境里论说的。《诗篇》反复咏唱的耶和华对子民始终不渝的慈爱(hesed)与信实(’emunah),就一阳一阴,恰好彰显那永世救恩之和谐。因此从原文研习《圣经》,和阅读缺乏语法性别(即人称只表示自然性别)的语言的译本,如英文和中文《圣经》,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性别指称要细腻、丰富得多。
那位老师的解释忽略了语言和阅读经验分析,是不奇怪的。他站在“牧灵”的角度,关注的第一是信仰即宗派信条而非知识。然而,信不等于知,更不及义;这本是耶稣的教导(见《宽宽信箱·天国的讽喻》),但教会的神学家往往混淆。那篇书评即是一例。
拙译介绍了《摩西五经》文本的“片断汇编假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书评的作者表示不可信,我完全理解。他是旧神学的立场,犹如美国南方某些原教旨主义教派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态度。但是接着断言,那假说只是“个别学者”的看法,就踏出“牧灵”的园圃,撞了学术的硬墙。因为在西方,那假说是大学本科教材、圣经学参考书必定介绍的,学者著述更是汗牛充栋。学界公认的标准词典,《铁锚圣经大词典》的“Torah”(摩西五经)词条(卷六,页605-622),即明确支持“片断汇编假说”,并给出详细的证据。该词条的作者是《圣经》文本研究的权威傅利门(Richard Friedman)先生。可知假说决非过时的旧说,而是现代圣经学文本研究的起点。所以我说“迄今尚无更加合理而有说服力的替代理论”(译序《谁写了摩西五经》),这话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学界的通说(参阅傅利门《圣经是谁写的》)。
 而且,这假说不仅跨教派的学术译本介绍,如《新牛津注释版圣经》(2001),西方主流教会主持的学术译本也是认可的。例如罗马教会官方审定“学说无谬”(nihil obstat)的法语圣城本(La Bible de Jerusalem),在《摩西五经》的序言里就有公允的长篇讨论,并在经文注释中标出各个片断的起止衔接。圣城本一九五四年问世,经过两次全面修订,至一九九八年新版,已经译为英、西、意等多种西方语言,其学术地位之高、影响之巨,在现代西语译本中首屈一指。因此,书评作者对“文本片断假说”的不屑一顾,和西方教会译经的主流也是相悖的。
而且,这假说不仅跨教派的学术译本介绍,如《新牛津注释版圣经》(2001),西方主流教会主持的学术译本也是认可的。例如罗马教会官方审定“学说无谬”(nihil obstat)的法语圣城本(La Bible de Jerusalem),在《摩西五经》的序言里就有公允的长篇讨论,并在经文注释中标出各个片断的起止衔接。圣城本一九五四年问世,经过两次全面修订,至一九九八年新版,已经译为英、西、意等多种西方语言,其学术地位之高、影响之巨,在现代西语译本中首屈一指。因此,书评作者对“文本片断假说”的不屑一顾,和西方教会译经的主流也是相悖的。
至于书评认为,拙译的插注列出希腊语七十士本的异文异读,而“遗忘”了死海古卷,有损“译本在校勘上的价值”,则是说外行话。
死海古卷出土于上世纪中叶,是圣经学领域开辟新纪元的考古发现。出土残卷的解读,对于我们了解公元前二世纪至耶稣时代(第一次犹太起义失败前)的犹太宗教思想和宗派组织,拉比犹太教与基督教兴起的历史背景,以及研究希伯来语《圣经》、伪经和异端文献,都有极高的价值。但是,残卷中《圣经》的篇章完整的不多,有些是亚兰语译本。因此对原文善本(传统本)的校勘,少数篇章除外(如《以赛亚书》、《诗篇》等),就远不如七十士本重要。这可以从拙译的底本,权威的斯图加特版希伯来语《圣经》(BHS)的校注中两者的悬殊比例看出。
译本做注,跟善本校勘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善本校勘的伟业,早有几代德国学者和以色列学者在做。有兴趣的读者,若想考察原文传世抄本和古译本中异文异读的全貌,应当研读他们的成果(BHS和希伯来大学《圣经》,HUB)。拙译的插注简短,通常不满一行。其涉及校勘处,只限于个别疑难语词的释义、笔误脱文的校补,并举出若干重要的异文异读,以使中文读者稍稍了解原文复杂的文本传统和各种可能的译法。《摩西五经》的古译本当中,七十士本不仅完整而且年代最早(公元前三世纪,出自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学者之手),在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中间曾广泛流传。更重要的是,希腊语《新约》的作者凡引用希伯来语《圣经》,皆用这个译本。七十士本因而成为基督教“旧约”的直接渊源,对教会教义产生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是希腊东正教的正典。换言之,西文译经的伟大传统,乃是从七十士本发端的。故我以为,《圣经》汉译,为使读者明了《新约》语言和教义与希伯来语《圣经》的承继发展关系,七十士本中重要的异文异读,是首先需要指出并研究的。
因此,仅就译经而论,死海古卷的校注价值不能和七十士本相比。倒是残卷中不少异文与七十士本相近,颇可支持各国注家、译家对七十士本的重视。书评提到《出埃及记》1:5,“雅各膝下,子裔合计七十”,BHS的校注,便只列出七十士本的“七十五”,不提死海古卷的相同说法。我的插注也只引七十士本,因为,雅各“七十五”子裔,亦是《新约·使徒行传》7:14的说法。这层《新约》与七十士本的密切关系(见拙译《创世记》46:27注),我以为正是包括教友在内的中文读者需要知道的关于《圣经》文本的基础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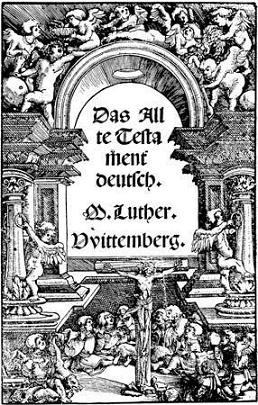
最后,谈谈书评结尾那个令你觉得“刺耳”的问题:译经(或解读《圣经》)可否是“教会的专利”。
其实,这问题我在彭伦先生的采访里已大致说清楚了(见《宽宽信箱·神的灵与言》)。历史地看,回答只能是“不”。马丁.路德译经,新教崛起,宗旨之一就是要把《圣经》从罗马教会的垄断(即拉丁语通行本)下解放出来。这个所谓的“专利”,早在近五百年前就被新教运动宣告无效了。之后,藉着启蒙运动的理性之光,现代圣经学诞生于德国,便不是历史的偶然。
但是,今天我们讲《圣经》不能等同于基督教,基督徒是“圣书之民”中的一支,并不仅仅是承认历史、尊重学术。二战以来,鉴于纳粹屠犹的惨痛记忆和世界各地愈演愈烈的宗教与种族冲突,西方主流教会都致力于促进宗教和解、消弭种族歧视。故而都尊重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对《圣经》的不同解读。犹太学者的《圣经》研究不必说了,在欧美大学早已是学术的中坚。伊斯兰教四部天经,穆圣传世的《古兰经》之外,还有《讨拉特》(tawrat,摩西五经)、《则逋尔》(zabur,大卫诗篇)、《引支勒》(injiil,耶稣福音或新约)。历代伊斯兰学者对天经的阐述,他们的学说,自然也是现代圣经学不可排斥的一个重要领域。
我给你讲一段逸闻。我在哈佛念书时,给两位导师当本科生“核心课”的助教,班生先生教乔叟,皮尔索先生讲“理查二世时代”。皮先生是英国人,自学成材,没拿过博士,口才超群,本科生里一大堆他的“粉丝”。理查二世朝(1377~1399)是英国中古文学的高峰,然而他第一堂课第一句话是这个:那时候,英国只是欧洲身边的“一池滞水”(backwater,喻闭塞);而欧洲,又是那从阿富汗到西班牙,横跨三洲的伊斯兰文明身边的“一池滞水”。教室里静得能听见迟到的同学喘气。接着他一转身,黑板上唰唰几个大字“宗教改革”“威克利夫”,便领我们一步步去了那个时代。威克利夫(John Wyclif,约1330~1384)是持唯实论的经院哲人,后世美称“宗教改革之启明星”,他反对的就是教会的《圣经》“专利”,他的战斗便是译经。“威克利夫本”(1380)是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英译《圣经》。为此他屡遭迫害,译本成为禁书,死后,遗体被挖出烧掉。就这样,开始了一场针对他的追随者的宗教迫害,连同以生命为代价(如廷代尔)的译经运动。面对如此血腥的历史教训,《圣经》在西方,当然不会是任何教会的“专利”了。因为如果是“专利”,即有哪一个教会,谁为正宗、谁是异端的严重问题,而一些地区的基督教教派之间有几百年的流血冲突,势如水火不能相容。理智的选择,便是拒绝并谴责这项只有中世纪教会才配享受的“专利”。
译经无关信仰。我这句话在中国听来仿佛激进,记者拿去做了采访记的标题;其实是西方学界和主流教会对译经的基本态度,是言论自由、宗教宽容、政教分离和公民教育世俗化等,现代社会奉行的宪法原则和民主价值的具体展现。
你觉得“教会的专利”刺耳,我想根本的原因在此。
解放后,中文译经的班子从上海、北京退居香港,原是不得已的安排。香港虽然宗教环境相对宽松,毕竟缺乏良好的西学训练与研究条件,师资、生源、图书、出版、学术传统和思想交锋,比起内地和台湾都差一截,跟西方的学术前沿更是隔膜。和合本修订至今,拿出来的“新译本”(1993),尚不及一百年前传教士的水平。随着内地逐步开放、富裕而人才竞争加剧,这落差还会越来越大。我有个未必实际的想法:拙译在香港出版,或可小小地刺激一下香港的圣经学及相关研究。现在教会的专家也不否认,和合本等旧译“舛误太多,无文学地位”,便是进步的开端。将来的目标,应是加入全国学界的争鸣,即以整个中文世界为读者做学问,把香港变为中国学术的重镇之一。
也许,你刚从北京交流回来,有些切身的感受,会说:可是内地的大学那么腐败!是的,反过来看,这正是香港的求学者的幸运。但是,学术进步通常只在少数人的努力,学术前沿总是由少数优秀分子代表。决不能因为内地大学和学界现时的腐败,就掉以轻心,失去这历史的机遇。
[下略]
二〇〇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