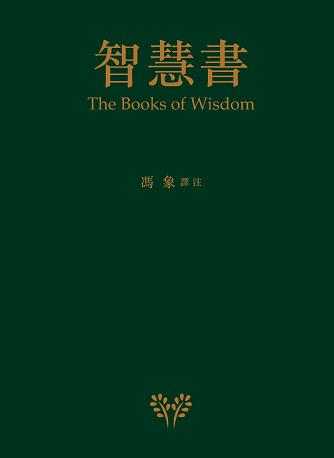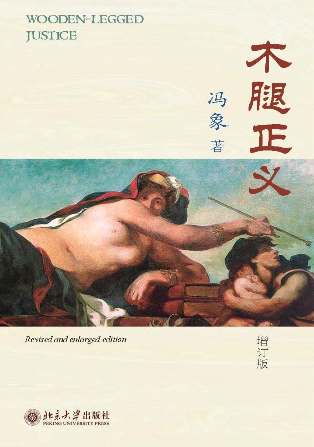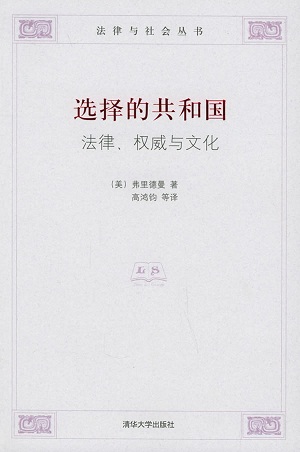前言其实是后记,依我的习惯。一本书写好,修改完毕,连同附录献辞参考书目,大功告成,可以交稿了;再回头想想,有什么需要向读者和友人交代、感谢的?一二三四,便是前言。今晚,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回顾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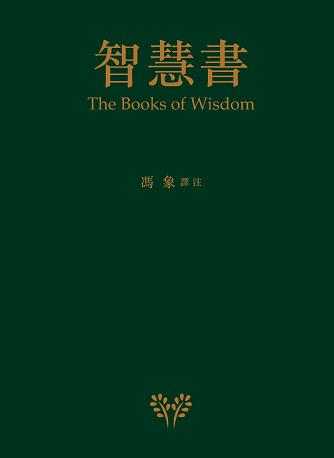 按常规,仿佛还缺一长文,讨论《智慧书》的历史背景同结构内容。然而,这五篇经文的渊源旨趣、思想关怀差异极大:《诗篇》是圣殿祭祀,子民礼拜,忏悔感恩的颂诗哀歌等等的总集,约有一半归在大卫王名下。《雅歌》虽然题为“属所罗门”,却更像民间情歌或婚礼上的唱和之曲,也有人认为取材于初民春祭的颂神诗。《约伯记》(传统上归摩西)、《箴言》与《传道书》(均托名所罗门),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慧文学”,承接的是古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和迦南的悠长的智慧传统。但它们的风格、哲理与教义又各不相同,难以放一块儿讨论。倘若分别作文章探赜索隐,似乎又超出了本书的体例和目的。毕竟,译本不是论著,译者的主要任务并非立一家之言。相反,正因为译文不可避免是一番“再创作”,译者就要十分注意为读者留余地,而不应越俎代庖,替他读书下论断,尤其像《圣经》这样蕴含了无穷教导和启示的经典。这也是拙译的插注一般不涉及神学诠解,不追求微言大义的理由之一。
按常规,仿佛还缺一长文,讨论《智慧书》的历史背景同结构内容。然而,这五篇经文的渊源旨趣、思想关怀差异极大:《诗篇》是圣殿祭祀,子民礼拜,忏悔感恩的颂诗哀歌等等的总集,约有一半归在大卫王名下。《雅歌》虽然题为“属所罗门”,却更像民间情歌或婚礼上的唱和之曲,也有人认为取材于初民春祭的颂神诗。《约伯记》(传统上归摩西)、《箴言》与《传道书》(均托名所罗门),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慧文学”,承接的是古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和迦南的悠长的智慧传统。但它们的风格、哲理与教义又各不相同,难以放一块儿讨论。倘若分别作文章探赜索隐,似乎又超出了本书的体例和目的。毕竟,译本不是论著,译者的主要任务并非立一家之言。相反,正因为译文不可避免是一番“再创作”,译者就要十分注意为读者留余地,而不应越俎代庖,替他读书下论断,尤其像《圣经》这样蕴含了无穷教导和启示的经典。这也是拙译的插注一般不涉及神学诠解,不追求微言大义的理由之一。
于是,想到一个化整为零的办法,原先用过(见拙著《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北京三联,2003)。就是作一份“释名”,为五篇经文和其中重要的人物神明、部族城镇、动物植物,以及相关圣经学术语,做一扼要的介绍。置于附录,供读者随时查阅,“链接”浏览。如此,“译序”即可聚焦一个题目,而不必面面俱到了。题目我选的是希伯来诗律,因为智慧书乃是《圣经》诗歌艺术的明珠,对西方文学影响至巨。原文格律修辞等语言手段作为思想的载体,对于译家,正是他的译文力图再现、转换而“再创作”的一个个文体元素;对于译本的读者,则是为完整准确地理解经文所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而《圣经》的中文旧译,无论文言白话,错漏最多、笔力最弱的部分,恰在诗体的章节。这里面,是有好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的。
智慧书五篇,传世抄本讹误较多,远不如摩西五经整齐。部分段落顺序衔接紊乱(如《约伯记》二十四至二十七章),断句训读,历代注家歧见纷纭。故拙译在底本德国斯图加特版传统本(BHS,1997)之外,参照引用的原文抄本(如死海古卷)和古译本(如希腊语七十士本、亚兰语译本、古叙利亚语译本、拉丁语通行本)的异文异读,也大大增加,详见各篇插注与释名。插注中,“原文”指BHS编者校订的经文善本,即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藏列宁格勒抄本(codex leningradensis);“另读”则指该抄本页边所录经师附注(masorah),或编者脚注列出的传统读法。
译文的体例,包括插注、原文的拉丁字母转写,一如《摩西五经》(牛津大学/香港,2006),此处不赘。仅说明三点,因为常有读者电邮问起。第一,经文原本不分章节(亦无现代标点),至欧洲文艺复兴,十六世纪中叶才开始划分,渐成定例。但这一套章节设计与经文的叙事、诗句的起止,往往并不吻合;不乏一句话断为二节,一首短诗横跨两章的情况。所以章节只是方便检索引证的一个系统,跟如何诵读或理解经文未必相关。这是读者须了解的。此外,传统本的分章与拉丁语通行本略有出入。因为英语钦定本的章节跟从通行本,而中文旧译如和合本又以钦定本为底本,故而凡通行本与传统本分章不一致处,插注中都标明了,俾便熟悉和合本章节的读者对照。
第二,同样,译本里散文的段落,诗歌分行划阕,加标题,也是现代译经的惯例,非原文即古代抄本的原样。为的是便利阅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译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判断而做的文体选择(详见译序)。
第三、希伯来经文中以色列子民的唯一神(‘elohim),汉译有“天主”“上帝”之分野。原是十九世纪传教士不智而搭的藩篱,不仅加剧了教派对立,还阻碍经文合一运动,实为历史的遗憾。而在他们自己的拉丁语和母语译本里,却只有一个诸派共尊的大写的名:Deus-Dio-Dieu-Gott-God。我是“非教徒”、“无党派”的“统战对象”,对于这译名的分歧并无任何偏向。可是译经只能采取其一,没法兼顾;若自创新名,又不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徒增混乱,委屈读者。而简单直译作“神”也不好,易与异教神或泛指的神祇混淆。所以就随汉语学界的大流,用了“上帝”。读者若愿意,读作“天主”也行,音节相当,应无大碍。
《摩西五经》问世以来,蒙读者包括许多教友的厚爱,来信鼓励或提出意见建议,还有专家学者著文评论,在此一并深表谢忱。现在《智慧书》将要付梓,最大的希望,便是继续领受读者诸君的指教——网络时代的写作,有个前人想象不到的好处:能够几乎是即时地获得反馈,隔着十二三个时区。
译经,在智慧的“传道人”(qoheleth)看来,恐怕也是太阳下无休止的一种“辛劳”,或上帝派给人子的“苦活”(《传道书》1:13)。然而人生幸福,却在那份“苦活”日积月累的所得,可以同无数人分享。这一点,我常得益于内子的提醒。我在西文典籍和学术话语里沉浸久了,容易忘记中文世界的读者的知识需求、阅读心理或可能有的困难。她的批阅、提问,总是站在普通读者的立场上,要求修改或解答,让我对学院派的玄谈和上不了口的“文绉绉”辞藻,时刻保持着警惕。
我以这本书纪念卢兄,我的哈尼阿哥。“伐木丁丁,鸟鸣嘤嘤”:每当我乘着经文诗句的翅膀,飞入希伯来智慧的明光,我就离他的大森林近了一程;就又一次回返往日,坐于他的火塘,端起新米的纯酿,聆听一颗超越民族疆界和宗教信仰的宽仁之心的吟咏。而且我知道,从他祖宗的圣山,他能望见,四面八方汇拢到我笔下,这一片漫漫黑地里“渴求天光”的众灵。
二〇〇八年一月于麻省新伯利港铁盆斋
《智慧书》,冯象译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