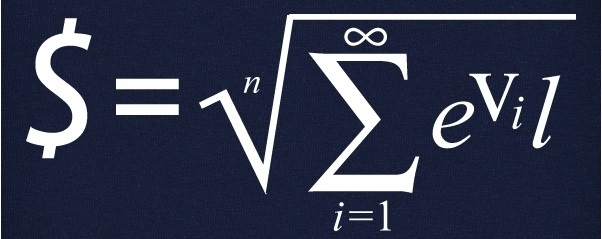沈明:自我殖民与批评伦理——简评《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
“燕京学堂”事件,自高峰枫发表《谁的“燕京学堂”?》一文(《上海书评》2014年5月25日)开始,受到传媒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日渐发酵,讨论逐步升温,加上北大部分教师学生两个月来网上网下的抗议活动,它已然成为高等教育界今年的一大热点事件。“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今天,文科学界两位重量级学者甘阳、刘小枫发表文章《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7月24日,以下简称“《北》文”),进一步以猛烈的火力批判了北大燕京学堂计划,以及由它所代表的英文至上乃至“去中国化”对中国“文明定位”的损害。料想此文必将进一步助推反对意见,使相关讨论走向深入。
《北》文批评力道十足,说了不少不客气(甚至意气用事)的话,读来颇有畅快之感。文章重申了作者多年来对中国大学改革的意见和批评,其中很多观点笔者都非常赞同。然而,掩卷反思,我想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进一步辨析商榷,求教于甘刘二位学长与读者诸君。
首先是树靶子问题,表现在《北》文提出的“英文北大”与“中文北大”的二元对立。这一对概念(以及相关的“法定语言”)大概是二位作者的发明。不消说,在这样一篇时评文章中,读者不应咬文嚼字,追究此种概念的精确性,只要明白作者意在通过简捷直观的符号性表达批判中国大学教育和学术的自我殖民化,也就够了。但问题是,《北》文将“英文北大”与“中文北大”描述成几乎势不两立的状态,以过于简化的处理方式粗暴打发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作者称拟建的燕京学堂为“租界英文学堂”,大加鞭挞,提出中文必须取代英文成为北大的“法定语言”。与此同时,《北》文也意识到不能搞一刀切,因此爽快地赋予了理工科 “治外法权”,甚至慷慨到称理工科“全盘英文化”也“没有什么关系”的程度。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必须由中文作为大一统的“法定语言”吗?《北》文对燕京学堂 “英文中国学”的批判笔者基本上都赞同——“英文中国学”的荒谬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文章试图“以小见大”,将其论说对象从燕京学堂本身提升到中国文化与学术主体性及文明定位之高度的时候,就有以偏概全、大而化之的嫌疑了,因为它在强调中文之为“法定语言”的正当性的时候,似乎有意无意地将“中国学”等同于全部人文社会科学,这显然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