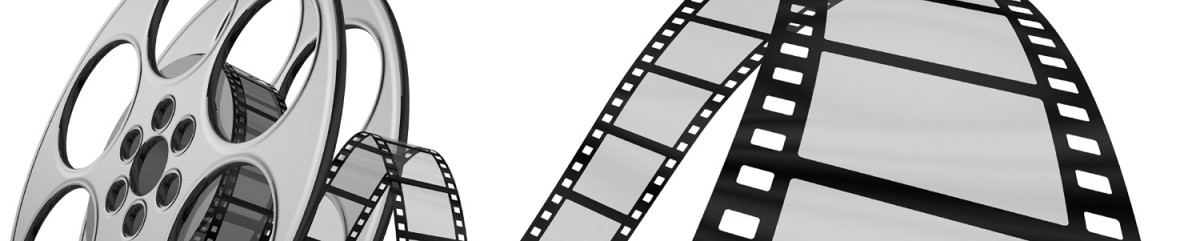刘皓明:狼人病史:《阳光灿烂的日子》
Ce qui se réalise dans mon histoire, n’est pas le passé défini de ce qui fut puisqu’il n’est plus, ni même le parfait de ce qui a été dans ce que je suis, mais le futur antérieur de ce que j’aurai été pour ce que je suis en train de devenir.
我的故事中所实现的,不是那个为已经不再了的东西所定义的过去,甚至不是现在的我所包含的曾一度存在的东西的完成状态,而是那个我将会已经成为的样子之前的未来,当下的我正在走向它。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弗洛伊德在著名的《摘自一例幼儿精神病史》(Aus der Geschichte einer infantilen Neurose)中讲述了这样一个病例[1]:一个总是梦到窗外的树杈上坐着长着狐狸一样尾巴的白狼的成年病人,在弗洛伊德的诱导下把这个梦境还原为婴儿时目击的事件的回忆。而那个婴儿时目击的事件,依据弗洛伊德的分析,是尚在襁褓中的病人目睹了其父母交媾的场景。这个场景被称为“原初场景”(Urszene),而那个懵懂无知的婴儿因此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毁坏性的震撼,被称作“创伤”(Trauma)。婴儿把他当时看到的却完全不能理解的原初场景保留在了无意识的深处,并且同童年时听到的关于狼的格林童话《小红帽》(Rotkäppchen)混合起来。这一创伤的经验在日后以种种掩饰了的、扭曲了的形态出现在意识的表层,扰乱着成年的病人的精神状态,引发了诸如虐待、恐兽症、焦虑、耽迷等种种精神病症状。而狼的形象作为那一创伤经验的象征不断出现在病人的梦里,既指向了同时也掩盖了造成创伤的原初经验。在心理分析的疗程中,成年的病人对孩提时代的往事的追忆,由于身体竭力避免重新提出痛苦的创伤经验的自我保护本能而在实质上成为一种逆向的幻想(Zurückphantasieren)。这种以狼为其意象的逆向的幻想屏蔽了真实,为当下的意识构造了为它可以接受的故事:病人的所谓记忆实际上是虚构。
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以下简称《阳光》)就是这样一部仿佛是回忆、实际上是逆向幻想的虚构。主人公马小军(夏雨扮演)就是弗洛伊德的那个被称作狼人(der Wolfsmann)的精神病人;作为叙述自己童年经历的讲述人,他实际上潜在地把有识别力的观众当成了对他进行治疗的精神分析者和精神病学家;而作为他的经历的视觉再现的《阳光》则是我们在目前中国的文明中所能遇到的最经典的精神病病例。虽然没有迹象显示姜文或者原著作者王朔接触过弗洛伊德的《摘自一例幼儿精神病史》,然而《阳光》就其严格地符合弗洛伊德对所谓狼人所患精神病的种种症状的描述这一点,是不折不扣的当代中国的狼人病例;而其同狼人病例如此严格的契合又揭示了当前中国文明、文化和文艺中的一些深层的问题。因此电影所依据的原创小说的标题《动物凶猛》在不止一种意义上概括了这部小说/电影作品的内容:王朔的凶猛的动物在幻想的、扩展了和翻转了的意义上对应于弗洛伊德作为象征的狼(而且狼的确是为王朔所痴迷的一个意象,他有一部小说的标题就是《我是狼》,涉及同样的精神病症状),而王朔/姜文的《动物凶猛》/《阳光》就是我们当下的文明中所产生的狼人自叙的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