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
1
二十年前,我们提到香港经常说它是“文化沙漠”,这个说法在很长时间内使我们面对那个资本主义城市发达的经济和令人羡慕的生活水平多少能保持一点心理平衡。那个时候香港人的形象在我眼里是喧闹和艳俗的。我在广州、汕头机场曾亲眼看到他们一飞机一飞机地到达,花花绿绿地下来,人人穿着喇叭裤,戴着金戒指和太阳镜,手提录音机和大包小包的尼龙衣服,都是准备赠送大陆亲友的,随机同到的还有他们托运的无数彩色电视机,而那时汕头除了党政军机关电影院路灯其他地方一律没电,这些电视机录音机第二天便都高价卖给了北方来的倒爷。他们似乎人人都是财主,住满广州汕头仅有的几座酒店和华侨旅行社,每人进出都带着一大堆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亲友团,一吃饭就开好几桌。我在电梯间经常听到他们认识不认识的互相大声抱怨国内亲戚的贪婪,国内酒店的服务差,有蚊子,想吃的东西吃不到。那时我还不太能分辨香港人和东南亚各国华侨的区别,现在想来那也不全是香港人,也有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地的华人。随着他们的到来,城市中出现了餐厅中的伴宴演唱、的士、出售二手服装的摊贩市场和妓女,今天已成为我们生活方式或叫消费模式的那些商业活动在最初就是带着深深的香港烙印进来的。
那时我不知道这也叫文化,餐厅中的伴宴演唱会发展到卡拉OK,酒吧乐队;的士会造成广播电台专为有车一族播放流行音乐;摊贩市场除了卖衣服也卖流行杂志盗版光盘和盗版软件;妓女,直接造就了歌舞厅夜总会桑拿室洗头房洗脚屋这些新兴娱乐产业的繁荣,更重要的是为流行小报地摊刊物乃至时装影视剧提供了耸人听闻和缠绵伤感的永远话题。
当时我们的文化概念是不包括大众文化或叫消费文化的,也没有娱乐这个词,一提娱乐好像是下下棋,打打扑克,单位搞个舞会,自己跟自己找点乐。当时右派作家咸鱼翻身,争当“重放的鲜花”;知青作家头角峥嵘,排着队上场;谢晋的电影观众数以亿计;张暖忻郑洞天谢飞吴天明都是新人,每部戏都能轰动一时;随便一个作家或者导演随便一出手都能给人带来一个新观念和新感受。滕文骥在《生活的颤音》还是《苏醒》中让高飞和陈冲正经接了一个吻,便成了那年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喧嚣得一塌糊涂。这还仅仅是开始,文学上“伤痕”“反思”“寻根”之后紧紧跟着“垮掉的”刘索拉徐星,莫言这样的“魔幻中国流”,马原这样的文体革命之父。在王蒙宣布“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还应声而起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人领导的“新写实主义”,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人的“先锋文学”。那时兄弟的“痞子文学”八字还没一撇,正在家里急得团团转。
电影方面,吴天明高就西影厂厂长,钟惦斐给他指了方向:要搞中国自己的西部片。也就在张暖忻他们那拨“第四代”刚红透,一眨眼的工夫,“第五代”出手了,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一下打破了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接着是田壮壮的《盗马贼》、《猎场扎撒》犹如大耳贴子似的贴在中国观众的脸上,扇晕一个算一个。那时大伙也算是群情激愤,特别是田壮壮说了那句“我的电影是给下一世纪观众拍的”之后。有意识地和大众保持距离,就是不为人民服务,还给嚷嚷出来,田壮壮是连作家带导演中的头一个。这个架直到张艺谋拍出《红高粱》才算打完,第五代走出象牙塔,谢晋谢幕,中国观众又被带入了新一轮的狂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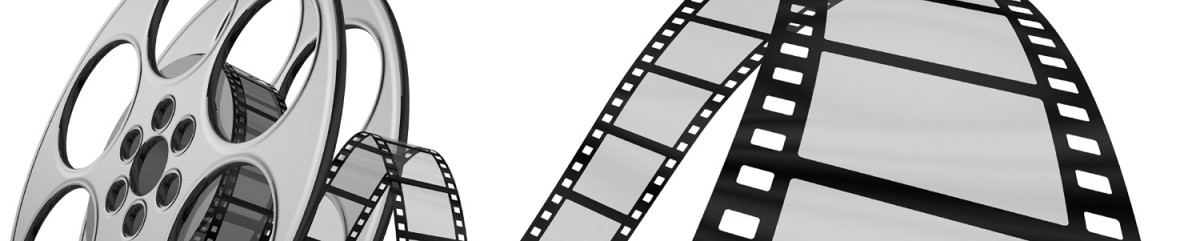

 某些电影、某些书,好象一直是在某处等待,等你去看,等着跟你说话。
某些电影、某些书,好象一直是在某处等待,等你去看,等着跟你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