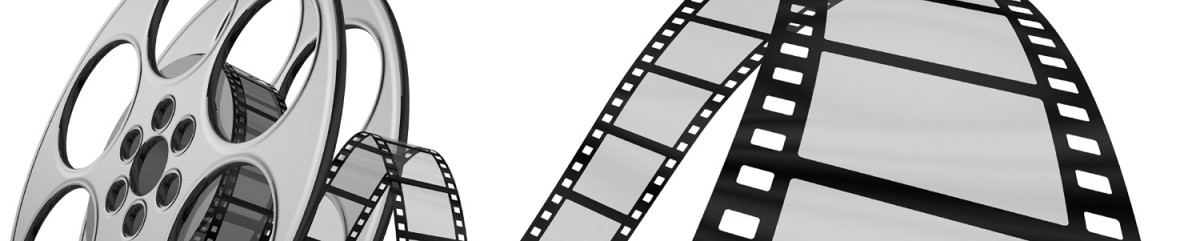
刘皓明:蝴蝶结:娄烨的电影《紫蝴蝶》
究竟有没有一种艺术形式可以化解屈辱和屠杀所带来的创伤?在电影史上涉及日本侵华题材的作品里,姜文的《鬼子来了》(以下简称《鬼子》)结束了叙述这类电影中《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等的政治宣传图解的模式,给后继者们开拓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但是在某些关键的地方,《鬼子》仍然带有很强的在它之前第五代相关电影中的某些特点。在第五代那里,这种特点集中地表现在张艺谋的早期作品《红高粱》中(姜文在里面扮演男主人公)。但是如果在《红高粱》里,这种特点还多少是隐蔽的,那么到了《鬼子》,这种特点就完全公开了。具体地说,这个特点就是用中国男主人公及其替代物的阳物来平衡被外国所蹂躏的屈辱感和创伤感。这种几乎不用象征而是径直表现的阳物情结构成了这一叙述深层次的上的“本我”。这种不断冲到意识表层的“本我”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导演更为有意识的艺术努力。尽管在《鬼子》里,姜文果断地打碎了反现代的伦理道德主义的迷误,但是这种用公然的个体阳物寄托和夸张来在幻想中报复和平衡民族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失败的“本我”的冲动,构成了一种心理分析学意义上的情结。这种情结所导致的对没有组织过的性本能乃至性器官的依赖,使它在实质上等同于义和拳对没有组织过的纯身体力量的依赖。 在义和拳惨烈失败一百年后,这种对没有组织过的、没有“格式化”的身体力量的依赖仍然深存于我们潜意识里并时时作祟这一事实,显明了叙述中日冲突的电影中所存在的一种隐蔽的、涉及问题非常深刻的迷误。但是《鬼子》中的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的?是否可能有其他的模式?也就是说,作为只在名义上是战胜国、其对正义的要求由于内外种种原因被长期延误、搁置和压抑的深受创伤的一方,我们应该、我们能够怎样拍叙述中日冲突的电影?甚或我们根本上能否拍这样的电影?
几乎在所有方面,娄烨的《紫蝴蝶》都是对《鬼子》的反动:它用蝴蝶情结取代了张艺谋/姜文等的阳具情结;用相当成功地扮演过同性恋人物的刘烨(《蓝宇》)替代了经常以极端男性沙文主义者面目出现的姜文;用大都会的上海替代了姜文的华北农村。《紫蝴蝶》故事的核心是一群似乎是孤立的、无党派的抗日青年结成一个秘密恐怖组织,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暗杀活动。为了暗杀日本驻沪特务头子山本,这个组织做了周密的计划:依仗秘密的单线联系,通过暗号而不是通过语言,通过行动而不是通过话语,达到他们的目的。于是就有了车站的接应,处决司徒,暗杀山本,将计就计去参加舞会……然而没有一件事是照着计划实现的:出于不相干的旁人的错误介入、由于动作的迟缓、因为消息的闭塞,由于有叛徒,一切都乱了套。然而在混乱之中目的居然达到了,虽然这目的是由计划外的力量实现的,过程也不干净利落,我方损失以及侧损失均过大,而且结果仿佛也于事无补,改变不了历史的进程,从军事和政治的效果上看是徒劳的,不可能改变或影响国际关系的进程和走向,并没能影响或推迟日本对上海乃至全中国的全面侵犯。
 对《紫蝴蝶》的情节的概括让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悬念或者动作片:它的确几乎就是。它几乎就是然而却不是。它这样几乎是而实际上却不是使得这一切都成为假象,成为炫目的徒有其表,成为噱头;在这些假象、这些炫目的表演的背后,《紫蝴蝶》很可能会误导、引诱和败坏。
对《紫蝴蝶》的情节的概括让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悬念或者动作片:它的确几乎就是。它几乎就是然而却不是。它这样几乎是而实际上却不是使得这一切都成为假象,成为炫目的徒有其表,成为噱头;在这些假象、这些炫目的表演的背后,《紫蝴蝶》很可能会误导、引诱和败坏。
之所以说《紫蝴蝶》的这些行动主线是噱头,并不是因为它们在技术层面上失败了,——恰恰相反,它们是相当成功的,在最近十几年来为数不多的行动片中,它属于极少数那几个成功者之列。但是这样的成功却不是有关其本质的。这是因为这种成功用来服务于一个更中心的主题,行动本身不是目的,行动是点缀,是背景,是道具。作为点缀、背景和道具,它们服务于电影的中心主题,这个中心主题就是电影的标题所明示的:即蝴蝶。因此,所有这些似乎是属于雄性的节奏、情节、氛围最终服务于一个高度阴性的图符和它所代表的旨趣。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里,蝴蝶代表着男女之情以及他们的殉情。但是娄烨的电影里的这个情(我们先不管传统的蝴蝶是怎样的),却主要不是爱,主要不是爱情,甚至不是激情、不是欲情,而就是情:它是一种糅合了伦理和欲望的神经官能症上的依赖情结,是一种把欲望及其满足即刻转化为伦理的机制。这就是说,这种情虽然主要是男女之情,但它却不仅仅是具有直接性关系的男女之间的情,它还包括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属间的情;而且其实在它里面任何男女之情都被转化为这种有病态倾向的、高度依赖性的亲属伦理情,也就是说任何性关系都立刻被转化为亲属关系:性侣成为哥哥妹妹;而哥哥妹妹形同性侣。所以在电影里,这样的情不仅包括了辛夏/丁慧(章子怡扮演)同伊丹英彦(仲村亨扮演)之间、伊玲(李冰冰扮演)同司徒(刘烨扮演)之间、辛夏同谢明(冯远征扮演)之间的“情”,也包括辛夏同她被日本浪人谋杀的哥哥之间的情。由于这种情是以神经官能症化的依赖为其基础的,所以它总是非常缠绵、痛彻心肺、生离死别的。从戏剧角度讲,这种情的英文所谓melodramatic(曲剧)效果尤其通过中日冲突的大背景得到高扬。电影的中心情节都是为这样的情所引起的,影片所力图制造的悲情,就是来自敌对国的辛夏与伊丹英彦个人之间的情与“民族”情的冲突。但是所谓的“民族”情,其实并不真正是民族的,也就说并不是属于命运的;它实际上也被表现为个人情、表现为伦理化的欲情。在辛夏的哥哥被日本浪人谋杀之前,辛夏同伊丹的个人情不构成同“民族”情的冲突。在日据的东北,在军事占领、政治歧视、经济掠夺的环境中,辛夏同伊丹英彦拥有几乎是伊甸园里的爱情。是辛夏的哥哥被日本浪人杀害这一事件把满洲国里“天真烂漫”的学生辛夏变成了上海的恐怖组织成员丁慧。无独有偶,在风雨飘摇的上海,穿行在抗日游行人群中间而不为所染的司徒同恋人伊玲营造着避风挡雨的情的巢穴。是伊玲在车站被流弹误中而死这一事件(再加上他被无辜逮捕和严刑拷打)把司徒精心营造和保持的巢打烂,使沉湎于儿女之情的他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抗日杀手。而谢明在大出击后同丁慧歇斯底里的床戏,更暗示着他参与和领导抗日地下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被伤害的情,出于他的这种情被背叛的感觉,而不是对命运的有意识的抗争。(甚至被谢明处决的告密者也是用家庭的亲情来为其叛变辩护的。)出于这种被伤害的情的报复,在谋杀之后他在床上对丁慧所施的,几乎就是姜文导演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对米兰的强奸的重演,而且更卑劣。
把中日冲突这个深刻影响了东亚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件用个人的情之间的冲突来演绎,是《紫蝴蝶》——尽管它在技巧方面有一些追求——令人感到不安的根本原因之一,而这样的情交由蝴蝶这个负荷沉重的图符来代表,则尤其牵涉到一些更广泛的问题。这种以情来演绎中日冲突的构思,是对《鬼子》的反动。因为在姜文的那部电影中,那种推动着村民凭个人的人情和伦理情来“教化”和“感化”外国入侵军队的无意识的、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文化本能,被无情地宣告破产;而《紫蝴蝶》则恰恰要通过伦理的情、这种以爱的面目出现的精神官能症的缺失感和依赖感来诠释和演绎那个如此重大的、决定着命运历史事件。这无疑是个大倒退。
通过对这样的精神官能症的情的戕害的展示,《紫蝴蝶》企图达到一种悲剧感。但是,这种“悲剧感”不可避免地回到了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这是因为娄烨和陈凯歌都试图用个人的、“普通人”的、伦理的思维和情感方式来质疑和颠覆战略的、命运的、发生史(geschichtlich)的历史事件;他们都想通过某些个人和属于个人的东西被属于历史的力量所毁灭的个例,来控告和消解历史;他们都认定这种毁灭是能产生悲剧效果的。但是用这种方式所处理的个人与历史的冲突所产生的,其实并不是悲剧的,而只是悲情的。因为悲剧最终是对命运和历史的肯定,尽管是以牺牲几乎是半神的英雄为代价的;悲情则一味渲染和鼓动个人所受的真实的和臆想中的损害,并以此为理由来解构命运,甚至对命运进行谩骂,把命运庸俗化。悲剧从根本上是悲观主义的,那是一种尼采所谓的“强者的悲观主义”(ein Pessimisimus der Stärke):这种悲观来自于强者因所充溢的健康和其生存的极度丰富而倾向于我们的存在中那种艰难的、恐怖的、恶的和成问题的,它渴求吓人的东西,渴求敌人,渴求配得上它的敌人;悲情则完全不是悲观主义的,因为它来自于弱者脆弱的神经和孱懦的体质,来自于弱者的画地为牢和固步自封的本能,它自欺欺人地尽一切可能、不惜一切代价回避我们存在中一切令人不安的东西,力图回避我们的生存中一切艰难的、恐怖的、恶的和成问题的,它回避敌对,直到艰难的、恐怖的、敌对的,总之,一切恶,找到他门上来摧毁他最后的庇护所——所以尽管从不吝惜眼泪和哭喊,就世界观来说,悲情说到底是自我安慰的乐观主义,是鸵鸟的乐观主义;悲剧的发生在于英雄力图突破和超越其所属的种的本质所规定的界限——必有一死的英雄想要等齐于不死的、大能的神;悲情则发生于凡人、弱者最后一块栖身和安居的巢穴里的最后一个角落被他所不愿正视、不能也不想理解的力量所摧毁的时候。由于悲剧是出于强者的悲观主义,由于悲剧的英雄走向毁灭是因为他试图僭越神人之界,是他的力量超越了必有一死的凡人的极限,所以悲剧是克制的、自控的、“酷”的、没有情感泛滥的,它并不要求观者的眼泪,它所要求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至多是恐惧与怜悯;悲情则正相反,它是哭天抹泪的、感情泛滥的、伤感的、不懂得节制的。虽然风格的考虑阻止了《紫蝴蝶》像《荆轲刺秦王》那样到处滥用哭天抢地的场景,但是在几个最关键、最泄露其实质的地方,它仍然不得不诉诸这种手段:辛夏在哥哥和司徒在女友被杀后的撕肠裂肺的哭喊。由于这些哭喊起着分别标志辛夏和司徒从沉溺于男女之情走向行动的重要作用,所以这两处无节制的情感的宣泄显示着《紫蝴蝶》同《荆轲刺秦王》乃至绝大多数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在文化和集体无意识上根本性的同一。
然而同《荆轲刺秦王》相比,《紫蝴蝶》显然是有所不同的。这种不同几乎全都表现在技术和形式方面。同陈凯歌的话剧式的作品相比,娄烨显然更注重为电影所特有的形式手法。在摄影、取景、镜头技巧、剪接、照明、音乐和音响效果乃至整部电影的叙事技巧和节奏等等方面,娄烨无一不显示出他的追求。这些追求虽然在他以前的作品《苏州河》里已经十分明显了,但是《紫蝴蝶》表明,如今这些手法运用得较以前成熟了。
《紫蝴蝶》中所有这些形式上的追求其实都属于现代的范畴。它们同它们所服务于的、毫无疑义地属于前现代甚至反现代的悲情的故事内容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反差,并在效果上互相拆台和互相恶化。在一方面,属于现代的这些电影的形式和技巧因素把属于前现代和反现代的故事内容包装起来,美化了它,使它得以更有效地引诱、唆使和煽动观众参加到悲情的宣泄中,强化和巩固伦理主义的情感和思维模式;在另一方面,前现代的故事内容使得电影所运用的形式手法和技巧成为不折不扣的奇技淫巧,也就是说,成为藻饰和噱头。
前现代/反现代的故事内容同现代的形式技巧之间缔结的这种非神圣同盟,最集中地体现在电影的主背景里:旧上海。旧上海就是这样一种非神圣同盟的集大成者——她拥有几乎所有的现代花头:堪与欧美城市媲美的各种风格的西洋建筑和城市规划,以及那些渗透在生活中各个方面的从西方舶来的现代生活的便利设施。但是如果对于西方来说,这一切只不过是装备、方便和点缀了西方列强的世界帝国的一个哨卡、贸易站和桥头堡,对于许多本土人来说,它们的用处则是丰富了腐朽的花样,为蜗居者们提供了一个洞天,使他们可以益发沉溺于内敛的情而更加不会产生扩张和竞争的强者冲动。同电影的实在的和象征的故事内容相一致的是,在《紫蝴蝶》里,上海是完全从这样的内敛的本土角度来表现的。这样的本土的、“上海人”的、鸳鸯蝴蝶派的上海被表现为怀旧的对象。这种怀旧同特别是司徒和伊玲的卿卿我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对上海的怀旧同对这种男女之情的怀旧浑然成为一体,使得上海实际上成为情的最大的和最高的对象。
从较浅的层次上说,显然,电影用以演绎关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命运的中日冲突所利用的那个伦理的、精神官能症的、内敛的情是自晚清以来尤为泛滥的情和感伤主义的继续;而这种感伤主义和泛滥的情在文学史上——正如鲁迅早在《上海文艺界之一瞥》中所显示的那样——曾特别同鸳鸯蝴蝶派联系在一起。因此娄烨的电影在标题上同鸳鸯蝴蝶派的一致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出一种深层的文化无意识在被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批判和清洗之后的沉渣再起,而且这种浮起来的沉渣几乎带着一种暴力来报复此前对它的批判和清洗。之所以说这几乎是一种报复尤其是因为这种对上海的怀旧其根源来自于未经新文化和两次革命洗礼的海外:旅居北美的学者和文人对张爱玲、胡兰成、鸳鸯蝴蝶派、乃至新感觉派和其他“海派”的鼓吹(——张胡二人在日据上海的那段情几乎可以被看作是《紫蝴蝶》里灾变发生前司徒和伊玲之间情的原型),台湾的上海热,以及上海出生的香港导演王家卫的的电影等等。所有这一切共同促成了文学、艺术、学术和电影上的“上海/鸳鸯蝴蝶的怀旧情结”。从电影史上说,娄烨的上海怀旧电影在时间上既不是第一的、在成就上也不是最引人瞩目的。王家卫将尚情主义和对电影技巧的极度追求的结合使得他成为娄烨艺术与精神上的教父。如果说在王家卫那里,先锋的电影技巧和情感的反现代之间所存在的张力乃至相互的摧残到他最近的一些电影里才变得突出起来,那么在娄烨这里,这种龃龉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具体到《紫蝴蝶》这部电影,这种明显无疑是由电影的题材所造成的。在《紫蝴蝶》这里,我们不再有王家卫所有的那种沉溺于、同情于其中所表现的情的奢侈,因为这种情被置于一个最为脆弱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之下:自以为被置放进封闭的玻璃瓶中的安全的蝴蝶恋人刹那间被打碎,蝴蝶被情人自己的鲜血所玷污,紫蝴蝶之紫,就是血污的颜色;而蝴蝶是死蝴蝶。
被血所污的蝴蝶就是娄烨这部电影的“题解”。在血污的蝴蝶这个象征上,集中着全部娄烨心目中的戏剧性和“悲剧性”。然而这种“悲剧性”却也正是他同传统的鸳鸯蝴蝶派分轩轾的地方。因为传统的鸳鸯蝴蝶派总的来说有意避免对他们来说是当前现实的中外冲突、避免在他们封闭的世界里引入来自西方的暴力侵入;在《紫蝴蝶》里,娄烨则试图包容和演绎这种暴力侵入,力图通过这种暴力侵入同内敛的鸳鸯蝴蝶派式的世界之间的对比与冲突来制造“悲剧感”。可是由于他所追求的这种戏剧性并不是悲剧性,而实质上只是悲情,所以在美学意义上,这个追求是被误置的,而作为这一追求的图符,血污的蝴蝶,则也是被其作者误解的:“紫蝴蝶”这个中心图符具有娄烨所不可能意识到的更深层的象征意义:只把紫蝴蝶解作被血所污的情人是远远不够的。
在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里[1],我曾借助济慈的《灵神赞》(“Ode to Psyche”)一诗说明在心理分析学上,蝴蝶往往被看作是女性外阴的一个图符。而就其内敛的本能、就其在进攻性上几乎先天的缺乏、就其对隐秘的偏爱等等特征而言,“紫蝴蝶”则俨然是一个充血的“公然展示的精巧的生理器官”。这个充血的女阴邀请着来自外族的阳具,下意识地期待通过把它接纳到自己里面而最终消解它的进攻性的勃起状态、通过这样的交媾来构孕子女,从而将它纳入家庭和伦理的体系,完成对夷狄的同化过程。这种潜意识里的愿望旨在达到的几乎可以类比于萨宾妇女被罗马人强奸后的效果,即最终使得萨宾男人和罗马男人的战争由于抱着由强奸所诞生的婴儿的萨宾妇女隔离于交战的双方而停止,并让萨宾部落最终被罗马所同化和吸收。然而所不同的是,在罗马人那里,家庭首先是一个法权制度和概念,罗马人对萨宾人的同化是一种法权的同化;而在中国文化的意识与潜意识里,家庭首先是个伦理关系和概念,其次是个建立在伦理关系上的“情”的维系,它所期望的同化则是伦理和亲情的同化。同化这一古老的做法显然并没有在中日之间重演,因为日本既不具备进行法权同化的能力,更不具备进行伦理同化的欲望(除了两者之间国土和人口的反差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采纳了英国等西方国家成功的殖民方法)。倒是中国由于历史上无数的先例,一直有很强的、用伦理主义同化异族的潜意识冲动。但是在现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方兴未艾的二十世纪上半期,这样的伦理主义的同化、教化、感化的做法是时空错位的。如果在儒家书写的历史上,中国历史上的同化都被描述为伦理的同化而有意掩盖或淡化了这种同化所必需的暴力前提,那么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则根本不具备罗马人那种以阳具为武器和以武器为阳具将毗邻部落中的妇女纳入其家-国法权体系的能力。但是正像《鬼子》里所叙述的那样,如果做不到主动到异邦进行种族和法权的延伸与同化,同化异族的潜意识冲动仍然驱使中国试图对入侵的异族进行伦理的同化。然而由于相对于日本而言,中国缺乏罗马人同化萨宾人所依赖的更优越的武力乃至更优越的民政组织、法权制度和文明的其他方面,所以现代中国始终无法自我认同于罗马人。这一事实在姜文的《鬼子》里就表现为由于不得不承认华北的百姓无法像罗马人那样用自己真正的阳具通过对邻邦妇女进行强奸而征服和同化这个异族,于是就有了让他们的驴子强奸日军的母马这一情节来在幻想中满足同化的冲动。但是如果作为被害者,患神经官能症的中国人无法认同罗马人,那么剩给他们的,就只有去在伦理和情的层次上认同萨宾妇女。在一定意义上,这正是《紫蝴蝶》所做的。同《鬼子》相反,《紫蝴蝶》放弃了徒然的阳物幻想,选择了用女阴来执行同化的任务。就像作为图符蝴蝶在同性恋理论里被认为包含有具体而微的阳具那样,在这种同化努力中,女阴被指定了某种化被动为主动的任务。在近代中国,这种利用女阴的象征来同化、消解、乃至最终征服现代化的入侵者的情结是有渊源和连贯性的。它同阳物征服幻想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当源自北方的义和拳对自然身体的超自然功能的迷信和依赖破灭之后,就有了源自南方的赛金花以女阴征服八国联军首领德国人瓦德西的神话。
比起赛金花的传说来,《紫蝴蝶》的“进步”在于它不得不承认这种同化的努力在实际上失败了。片尾在与鸳鸯蝴蝶派沆瀣一气的旧上海靡靡之音的伴奏下,日军对上海的空袭和对南京的屠城——the Rape of Nanjing——的原始记录片镜头,显明了赛金花/紫蝴蝶式的女阴同化始终没有能将入侵的阳物伦理化、没有能将非法的强奸转化为合法的婚姻。——这个结局当然是娄烨不得不遵循的历史事实。但是作为一部电影,《紫蝴蝶》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能把这种用女阴来在伦理上同化现代化了的外国入侵者的“蝴蝶结”当成一个问题来质疑和挑战,没有能把日本的唯美主义和中国的伦理主义的反差提升到一个哲学的高度(例如它把咖啡店的日本女店主被司徒误杀伦理化了,忽略了其明显的唯美的因素),而是在整体上,继续被蝴蝶结的集体无意识所误导,并把这种情结所导致的在现实中无可置疑的失败设定为其所追求的悲情效果的核心,从而在观众中延续和强化了这种集体无意识,在效果上将这种无意识和在这种无意识的情结指使下的病态生活慢性化和永久化了。相形之下,《鬼子》虽然同样暴露了利用未组织起来的身体来消解屈辱和失败的潜意识中的情结,但是它对感化期待的伦理主义的无情批判使得它最终远远胜出习作水平的《紫蝴蝶》,成为一部近乎杰作的作品。然而倘若中国的艺术家要创作真正的悲剧,把我们从悲情的恶性循环中解放出来,仅抛弃感化期待的伦理主义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把阳物/蝴蝶情结作为更深层次上的怀有同化期待的伦理主义以及血仇报复一起摒弃,才有可能接近悲剧的深广领域。因为正义(dikê)和法律(nomos)是对建立在这些原始情结之上的血仇报复与伦理主义的扬弃,就像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索福克勒在《安提戈涅》(Antigônê)里所体现的那样,同正义和法律产生的冲突才是悲剧的冲突。
(后记:这篇旧文写于2003年《紫蝴蝶》公映后不久,先是投《读书》杂志,不中。后在数个杂志之间辗转,均未获刊载。回过头来,无论从娄烨先生后来的艺术发展,还是今天更一般的状况看,本文应不算是无的放矢。)
——————————————————————————–
[1] 《梦迷蝴蝶》,载《读书》1996年第2期:1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