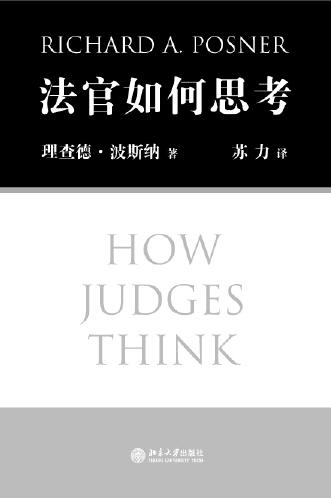[本文为《
检察日报》记者对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的
李本(Benjamin Liebman)和
吴修铭(Tim Wu)的采访,原载2006年7月24日《检察日报》,作者刘卉。他们的这一研究以
“China’s Network Justice”为题发表于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Summer 2007)。]
记者:李本先生,你好!作为一个从事中国法研究的外国学者,你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曾给中国学者耳目一新的感觉(见《检察日报》2005年7月25日报道《228例媒体名誉侵权案揭示了什么》)。这次中国行,你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研究成果?
李本:主要想与中国学界同仁交流我最近完成的一篇论文,是关于信息论和中国法院关系的,特别是互联网将对中国法院产生怎样的影响。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我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首先,尽管西方社会非常关注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但是针对具体机构的分析凤毛麟角。其次,中国法院制度正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而我们搜集的资料表明,在某些方面中国法官在向其他国家的同行们逐渐靠拢,而在另一些方面他们则独辟蹊径,对信息的使用正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发展,至少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是与众不同的。
此次与我同行的还有这篇论文的合作者,我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成员吴修铭教授。
信息论应用扩展到法律领域
记者:信息理论似乎是经济学概念,它与法律有关系吗?
吴修铭:信息论,也叫信息经济学,在过去15年间已经成为美国和欧洲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目前,信息论的应用已经扩展到了社会学、法律和其他研究领域。信息经济学跟法律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法律有时可以帮助控制经济体系内的信息传递。比如,美国相关法律规定,食用产品必须说明脂肪和盐的含量,这实际上是通过法律保证生产商将必要信息传递给消费者。第二个方面,它可以帮助了解与法律有关的决策者怎么做决定。比如,不同的信息怎样影响到司法制度,法官如何作出判决。
记者:能具体谈谈第二个方面吗?
吴修铭: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官都会受到他们所接受到的信息的影响。法官阅读案例,与其他法官交流,与朋友交谈,看报纸,这些活动都会对法官的判决有影响。随着信息技术成本逐渐降低,法官更容易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如果阅读案例变得更加容易,那么更多的人就会去阅读。如果很容易就能够与法学教授或其他法院的法官通信,那么这种交流就会越来越频繁。
李本:为了避免信息对法官的负面影响,有关适用判例的方式、限制单方接触当事人的规定以及那些规范法官之间交往的规则也顺势而生,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成是对法官判决时所能获取信息类型的限制和规定。
互联网影响中国法院的方式
记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导致信息爆炸性增长,人们获取信息也更加方便。互联网改变着整个社会,包括法院、检察院。
李本:互联网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对法院产生影响,即:一、构建法院内部信息网络;二、利用公共网络进行调研;三、通过互联网对法院施加舆论压力。
就第一种方式而言,法院设置局域网,一方面为法官提供信息,包括法律、通知以及相关的新信息。法官可以在局域网上搜索法律和有关解释,上级法院和法院院长也可以向其管辖范围内的法官传达信息;另一方面局域网可以协助法院进行案件信息管理,从而提高法院效率,也有利于对法官进行更为有效的监督。
就第二种方式而言,目前很多中国法官使用互联网对待决案件进行调研,这是中国法院的一个重大变化。过去,法官遇到新问题或疑难法律问题,首先会想到与同事讨论,也可能会请示上级法院。但是,一个地方(比如青海)的法院就很难了解其他地方(比如北京)的法院是如何处理类似案件的。据我了解,现在法官们经常上网搜索实际判决、媒体报道和学术界的讨论,从而了解其他地区的法院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另外,在互联网上搜索到的法律法规信息远远多于法院局域网。
就第三种方式而言,通过网络对待决案件进行新闻报道和公开讨论,比如孙志刚案、佘祥林案和聂树斌案,都是网络报道促进案件解决的例证。但是网络压力的作用也有另外一面,这就是网络报道的大众效应。大众压力可能会迫使法院变更审理程序、不恰当处理被告人等。据媒体的评论,刚刚宣判的黄静案就曾因互联网给司法机关带来不小压力。
客观评价互联网对法治的影响
记者:两位如何评价这些影响?
李本:互联网的使用使法官之间的横向互动越来越多。这类横向互动的发展,或者说是非正式的参考别处判决的做法有可能会使全国范围内的判决更为一致。这种横向互动也会鼓励法官进行创新。这种互动还会在法官间强化自身的职业身份。
此外,大众压力对法院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法院和媒体的相对位置。对此我们不能归罪于互联网,互联网的舆论监督当然是好的和必需的,只是互联网的发展同时确实可能会导致对案件的更多干预,会消解法院为抵制压力所做的各种努力。互联网还可能会迫使法官在真正的压力形成之前就屈服于大众的意见。
吴修铭:是的,我们论文的初步结论是:第一,中国法官相互交流越多,法官判决就会越统一和一致;第二,公众注意到判决结果越容易,法官判决就越有可能屈从于公众压力。我想对第一点进一步阐释。
“理性羊群行为”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它认为,人们喜欢去做其他人在做的事情。在“理性羊群行为”下,不好的东西有时会很流行。司法制度也会有同样的现象。当交流成本更便宜,效仿手段更容易,法官就会跟其他人一样,也去效仿别的法官的做法。这样,一个司法制度像服装一样,也会有它的流行趋势,而且有时在特定情形下不好的判决会变得流行。当然,总体上说,法院获取更多信息的趋势促使法院适用法律更加一致是件好事,它体现了“相似的案例判决也应该相似”的基本法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