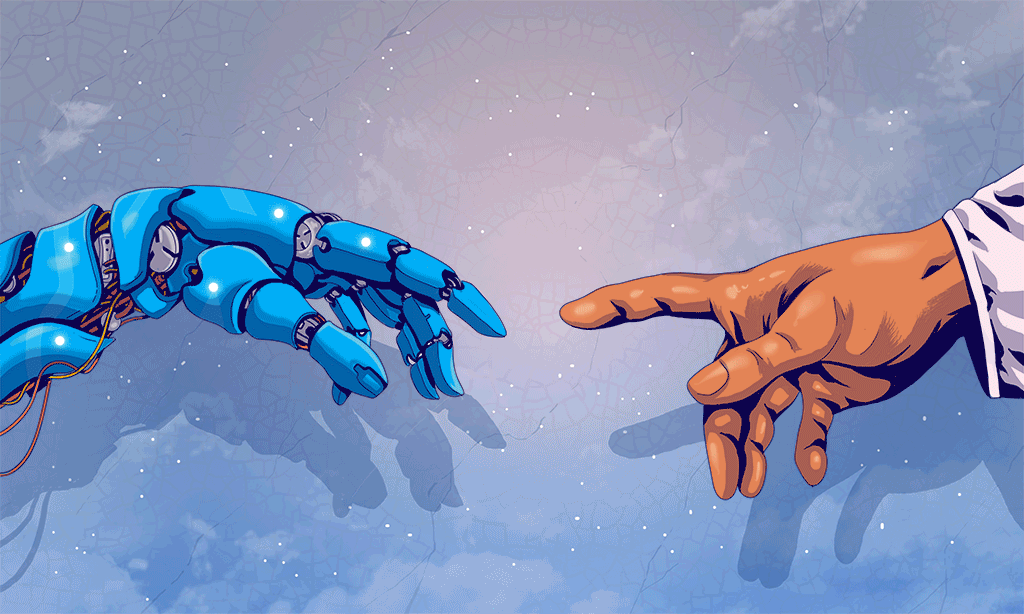
冯象:呐喊和思念——《我是阿尔法》弁言
此书是《以赛亚之歌》(北京三联,2017)上编的姊妹篇。那书研究《圣经》和宗教,这一本侧重法律。近年因为专注于解经译经,法学方面的文章写得少了。此番结集,重读一遍,觉得几个题目颇受益于一门课“知识产权与中国革命”的教学。不论知识产权、劳动法、宪法,还是大学教育、接班人伦理和人工智能,都是经过课堂讨论,得了学生反馈的。可见“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而“教学相长”,对于写作的重要了。
课以“中国革命”为名,听上去有点另类,仿佛招引删帖的一个敏感词,实际是有来历的。解放后,新清华的办学传统,叫作“双肩挑”“又红又专”,就是根据“祖国的需要”培养人才,不囿于训练工程师。一九九五年法学院重建以来,毕业生便有许多入职各级党政机关和国企,及报名到中西部下基层挂职锻炼的(据说人数为诸院系之首),表现优异的不在少数。但是出了校门当干部,不能只懂些法条学理,开口美国,闭口欧日,摆弄课本里的一套。那样办不成事,容易犯错,脱离群众,甚至挤进了“官场”也难以立足。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原本是共产党闹革命的“法宝”,现在经常给“忘了”。
所以,回国服务之初,法学院让我招收知识产权专业的博士生,开必修课,就想到了这一历史视角。内容安排上,大致是一半的课时讲前沿问题,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另一半联系这些新技术新经济的挑战,反思二十世纪革命的经验教训,考察网络时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探索人类理想社会的前路。因为博士生不多,课程遂隔年一讲,并向硕士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开放,不限专业。要求是,选课同学须自己选题,与老师讨论,期末交一篇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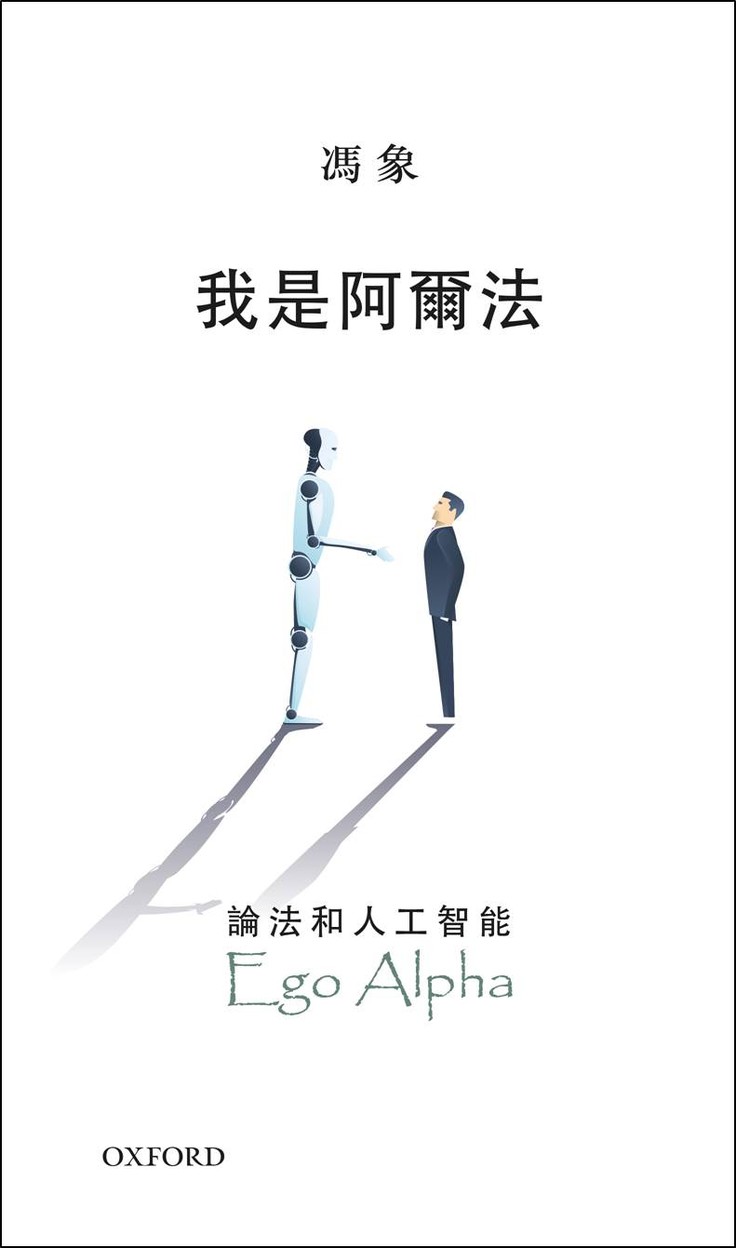 八年下来,似乎效果不错,学生论文有发表的也有获奖的。更可喜的是,同学们的事业选择,无论本科、研究生,都十分多元化;除了律所法院检察院跟大公司、政府部门,还有参军、留学、做公益、走学术道路的。后者尤其令人欣慰。因为说实话,现在的大学,整个体制,各项政策,对“青椒”(青年教师)真是太压抑了。别的不谈,光说崇洋媚外弄虚作假的风气。打出一个“国际一流”的名头,招聘便只要“海归”,论文要英文“核心期刊”发表,申请职称要“国际评审”。结果,博士生纷纷拿国内做的论文到国外再混一个学位,以便求职;论文代写评审作弊成了暴利产业,连国人顶礼膜拜的《自然》《科学》也防不胜防。我听不止一个年长的教授感叹:幸亏生得早,不用评这评那了,不然只好央求在美国教书的学生来填职称表格,靠他们保饭碗了!
八年下来,似乎效果不错,学生论文有发表的也有获奖的。更可喜的是,同学们的事业选择,无论本科、研究生,都十分多元化;除了律所法院检察院跟大公司、政府部门,还有参军、留学、做公益、走学术道路的。后者尤其令人欣慰。因为说实话,现在的大学,整个体制,各项政策,对“青椒”(青年教师)真是太压抑了。别的不谈,光说崇洋媚外弄虚作假的风气。打出一个“国际一流”的名头,招聘便只要“海归”,论文要英文“核心期刊”发表,申请职称要“国际评审”。结果,博士生纷纷拿国内做的论文到国外再混一个学位,以便求职;论文代写评审作弊成了暴利产业,连国人顶礼膜拜的《自然》《科学》也防不胜防。我听不止一个年长的教授感叹:幸亏生得早,不用评这评那了,不然只好央求在美国教书的学生来填职称表格,靠他们保饭碗了!
如此“逼良为娼”,谁还有心思好好教书、做学问?当然,受损害的首先是学生,因为教课在“体制”的眼里不算“成果”;“青椒”若是把时间精力多花一些在学生身上,即可能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说“欣慰”,是感动于青年对理想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在这困难的关头。
然而,困难终会过去。教书做学问一事,对于能安心坐冷板凳、不怕吃苦或者家里有一定经济条件者,我想是应该鼓励,积极支持,抱乐观态度的。理由在课上也谈过,举了三条:一是大学推行雇佣制,教师全面合同工化,在中国未必行得通。有许多制约官僚主义,不容它猖獗的因素,中国革命的遗产便是一个。第二,要相信“中国特色”,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校园里也不都是书呆子,一辈子学不会维权;活人哪能被尿憋死?但最重要的是,第三,人工智能来了。新兴的“智能经济”及其标志性的不可避免的大失业、全民福利,将迫使人们重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我们熟悉的大学教育模式,包括专业设置,连同上述升级版的官僚化科研体制,很可能像老百姓说的,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又到了开学季。新闻说,大学新生当中,新世纪出生的“零零后”占了不小比例。我知道,年轻人之间,相差三四岁,想法跟兴趣爱好便很不同。可是人过了耳顺之年,对年龄的感觉就趋于“印象派”了,“八零后”到“零零后”会画在同一个轮廓里,看作一代人——这一代,未来要应对或携手合作的,会是一个更美好的机器人世界吗?
我因此反而越发怀念从前那个朴素而热烈的时代了。
怀念也体现在了本书的编排:起头取一个七十年代大山里的故事《青蛙约西》,跟结尾的未来智能社会那一面共产主义的旗帜呼应。同时,循内子建议,增加一点异域的趣味,收一篇八十年代的旧译作附录。原文是一位英国同行(中世纪史教授)写的,介绍龙在西方宗教传统里的演化,颇具知识性,于读者或有参考价值。原载《九州学刊》,现在市面上大概难得一见了(参阅《木腿正义》增订版前言)。
我把这本小书,连同内中的呐喊和思念,蛙精与七首毒龙,献给我的老师阿尔弗雷德先生(1922~1999)。先生是纽约人。二战应征入伍,上欧洲战场开过坦克。战后复员,进哈佛英文系读研究生;因才艺出众,博士毕业获破格留校,教授戏剧和中世纪文学。先生性情幽默,讲论史诗及日耳曼神话,辄“吐嘉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深受学生爱戴,尊称“教授”,大写加定冠词不带姓氏,The Professor,以示全校独一无二。他的故事,记忆中的吉光片羽,已经写在《创世记·石肩》等文章里了,兹不赘述。
最后一次探望先生,是在一九九三年暑假,去港大任教之前。我从耶鲁回来,到瓦伦屋(哈佛英文系旧址)呈上拙译《贝奥武甫》,给他留念。像往常一样,聊了一通英雄屠龙、洞府藏宝的喻义谱系。末了,先生道,把书搁家里去吧。遂陪伴先生走回雅典路他的寓所。先生弓着背,拄着杖,身子辉映在夕照下,慢慢迈上台阶。然后转过头来,招一招手,消失在如今唤作阿尔弗雷德学社的门洞里了。
二〇一七年九月(美国劳动节)于铁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