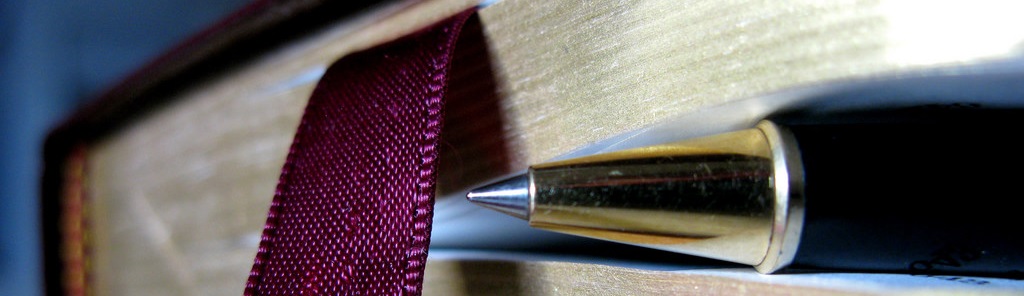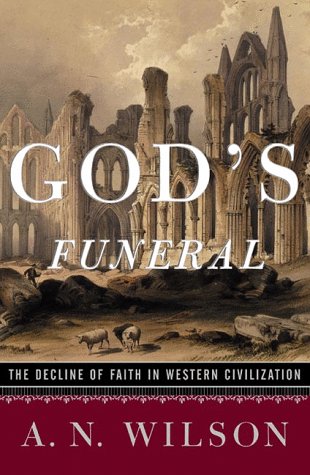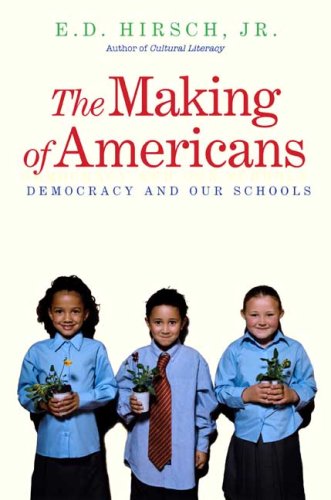高峰枫:谁的“燕京学堂”?
2014年5月5日,北京大学宣布正式启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计划(Yenching Academy,Peking University)。根据北大的官方介绍,这是一个独立建制的教学科研实体机构。燕京学堂为住宿式学院,将开设一年制的“中国学”硕士项目,包括“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语言、文学与文化”、“经济与管理”、“法律与制度”和“公共政策”六个方面的课程体系,主要以英文讲授。2015年9月,第一届学生即将入校,其中包括六十五名海外学生、三十五名中国大陆学生,所有人都将获得全额奖学金。教师的配置,是从北大现有教师中联合聘任三十人,从国内外招聘“杰出学者”二十人,并邀请“国际顶尖访问教授”二十人。
虽然目前公布的资料和数据都不多,但根据有限的报道,可大体获知这一新机构的办学宗旨和特色。我对于“燕京学堂”在命名、选址以及学科定位等方面都存有不少疑惑,特借《上海书评》一角,发表一点浅见,希望能将所牵涉的复杂问题辨析清楚。
北大与燕京
在北大发布的官方文稿中,对于这一机构的定位和宗旨有这样的阐释:燕京学堂“根植京师大学堂的中华文明底蕴,绵延北京大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命脉,承接百年燕园孕育的博雅教育理念和国际化视野”。这一句大可斟酌。新文化运动恰恰以激烈反对传统文化而著称,这样的“精神命脉”是很难和传统文化的“底蕴”相协调的。而且,此机构的正式名称中有“燕京”字样,英文表述也启用传统的拼写(Yenching),再加上“百年燕园”的提法,凡稍知近代教育史的人,都自然会联想到著名的燕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