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日,李先生去了。十一日一天接的电邮,都是先生逝世的沉痛的消息。去年三月访问北京,到蓝旗营小楼拜访他,精神还挺好。谈起我的亚瑟王故事,马上就翻开大辞典似的,举出一串古法语、中古高地德语和拉丁语文献的素材例证,一个音节都不含糊,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样。师母说他每天散步锻炼,中西医结合,比前两年有进步。本想今年秋天再去探望的。现在,这期待突然落空了;“西山苍苍,永怀靡已”,这两天,先生的音容笑貌越发清晰亲切,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了求学的日子。
我是一九八二年二月考进北大西语系读硕士的。李先生是系主任,但那一学年他在耶鲁讲学,所以入学后并未见到。回想起来真是幸运,赶上了“末班车”:老先生们多数还健在,虽然有几位已经不教课了。最先拜访的是德语专业的杨业治先生。杨先生是先父与先母在清华读书时的德语老师,《德汉词典》的主编,在海德堡大学念的希腊语,精通西洋诗律和音乐理论。用现在的话说,是“泰斗中的泰斗”了。那时我的兴趣在古典语文。拉丁语在云南已自学了一点,用一本上海福州路旧书店两角钱淘来的苏联教材(我小时候学过四年俄语,在乡下又补习了一阵,读普希金和契诃夫的短篇);在北大,老师是法国专家贝尔娜小姐。希腊语则刚开始自学。先父便写了信,让我带去找太老师求教。杨先生家和孟实(朱光潜)先生家一样,也是小洋楼,经过文革,有些破旧了,但很安静。杨先生慈祥而认真,看了信二话不说即进入正题,检查我的作业,一句句改正。不久,王府井外文书店“内部发行”他和罗念生先生推荐影印的 Liddel and Scott 《希英词典》(缩编本),又通知我进城去买。有一次,谈到中世纪艺术中的符号象征,我表示有兴趣。杨先生说,研究中世纪,先得过语言关。等李先生回来,你跟他学,他一定欢迎。我就记住了。
大约五六月间,李先生回来了,召集研究生开会。他和先父是清华十一级同学(一九三五年入学),初次见面,只问先父近况,非常客气。过了两天,又叫我去,让我谈谈学习,我就把学古典语言的计划汇报了。先生说,你有这个兴趣和基础,就跟我做中世纪这一段吧!果然被太老师言中了。接着,送我两本书:牛津版《乔叟研究目录》和 Henry Sweet 《古英语入门》。原来先生有个习惯,见到好书即买两本,一本自用,一本给学生。前些年读到汪曾祺先生回忆西南联大和沈从文先生的文章,说沈先生买书,常常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到学生生活拮据,可供他们借阅,借了不还也从不介意。先贤爱护学子如此。这在李先生,在北大也是有口皆碑的。
这样,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就每周两晚,到蔚秀园先生家读古英语。方式是先把指定的课文(古英语《圣经》和编年史选段)一句句念出,分析语法,再译为现代英语。不明白处由先生讲解,参较中古高地德语、哥特语(代表东日尔曼语,十七世纪绝迹)和古冰岛语(主要文献为北欧萨迦,代表北日尔曼语)的同源词。再上溯至印欧语的第一次音变和第二次音变,前者即格林/威尔纳定律,是历史语言学家重建的使古日尔曼语“脱离”其他印欧语,如梵语、希腊语、拉丁语的一系列辅音音变;后者是区分高地德语(及其后裔现代标准德语)和西日尔曼诸语,包括英语的辅音音变。这些内容,后来先生在《英语史》(商务印书馆,1991)中有所阐述,但作为大学教材,大大简化了。
中古英语(即法国诺曼人入主英伦以后,十二世纪中叶到文艺复兴之前那三百多年的英语)方面,则阅读乔叟(代表伦敦方言)和各地方言文献,例如代表中部西北方言的头韵体长诗《加文爵士与绿骑士》(故事见拙著《玻璃岛·绿骑士》,北京三联,2003)。然后对照法国学者Fernand Mosse的经典《中古英语手册》,写读书报告与先生讨论。但重点放在乔叟。乔叟(约1343-1400)史称英诗之父,是中古英语文学的巅峰。因为在他以前,英语基本上只是下层百姓的土话,宫廷和司法语言是诺曼贵族讲的法语,教会和学术界则用拉丁语。乔叟的词汇,约有一半来自法语和拉丁语,修辞和诗律也深受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文学的影响。但他的诗歌语言的基础和核心是伦敦方言;后来伦敦方言成长为英国的民族共同语,跟他的文学成就和崇高地位是分不开的。所以从历史语言的角度看,非常值得研究。乔叟也是先生早年留学耶鲁钻研过的题目。北平解放,清华请他回校执教,他觉得新中国百废待兴,便放下写到一半的博士论文,于一九五零年回国服务了。当然,回国后频繁的政治运动,再埋头于勉强贴个“人文主义”标签的乔叟,就明显地不合时宜了。五七年先生逃过反右一劫,据说是被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保下的:西语系黄继忠老师划为右派,先生为之抱屈,对江书记“提了不恰当的意见”。江书记却实事求是,当众宣布:“李赋宁虽批评我,但他并不反党”(中华校园网载先生文《我与北大人》)。不过,此类事情我从不向先生打听,因为先父早有嘱咐:拜访老先生,规矩与老干部不同,只许谈学术,绝不问政治——怕我说话出格,惹出事来。
李先生希望我接着做乔叟,对我而言是再好不过,因为早就对照方重先生的精彩译文读过原作(见拙著《政法笔记·不上书架的书》,江苏人民,2004),时代背景也不生疏。但是我好高骛远,想找个题目跟古典语文的学习结合起来。先生说,那也行,《坎特伯雷故事集》片断三巴斯妇(Wife of Bath)《开场白》里提到一本书,你可以从它入手,探讨乔诗中的拉丁语及有关文献的运用。我就乐了,没想到先生点了这么个题目;那段开场白是乔叟的神来之笔,大意如下:
织布能手巴斯妇家道殷实,四十岁上得了第五任丈夫,一个年方二十的“牛津学生”。新郎官文文雅雅,样样都好,只是不爱求欢。成天价手里捧一本书,名叫“Valerie and Theofraste”,读着读着就笑出声来。一天晚上,他坐在壁炉前又念将起来(古人很少默读)。巴斯妇尖起耳朵听,却是些夏娃害亚当、叁孙遭出卖、谁家淫妇往熟睡的老公脑袋上钉钉子、哪里的巫婆在情人的酒里搁毒药的故事,控诉的全是古往今来夏娃女儿们犯下的罪行。那巴斯妇是个风流泼辣货,女权先驱,一听这个,全明白了:原来小丈夫对她嘀咕的那些妇德训诫,什么“姑娘衣一脱,羞耻心全抛”(圣杰罗姆《反约维年书》1:48),“美女若不贞,金环挂猪鼻”(化自拉丁语通行本《旧约圣经·箴言》11:22),都是这里头看来的!不禁怒火中烧,将那“淫书”一把夺下撕了,再对准牛津学生的面颊一记,把他打个仰面朝天,跌在木炭灰里。新郎官爬起来,发疯一样,一拳将老婆打昏在地。从此巴斯妇聋了一只耳朵,小丈夫却晓得听话了(《开场白》525行以下)。
Valerie 和 Theofraste,是两篇中古拉丁语作品。前者全称《瓦雷里劝陆非奴不娶妻文》(Dissuasio Valerii ad Rufinum de non ducenda uxore),古人以为圣奥古斯丁所作,其实是亨利二世朝(1154–1189)一位通人马普(Walter Map)的手笔。马普是威尔士人,曾任牛津副主教,博闻强记,机智脱俗。传统上不少拉丁语醉酒歌归在他的名下,据说还写过一部拉丁语亚瑟王传奇,今存古法语译本,即“标准本”散文《湖中郎士洛爵士》。但现代学者能够确认的马普著作,只有一本掌故书《庭臣琐闻》(De nugis curialium)。《不娶妻文》即出于此。《庭臣琐闻》在中世纪并无名气,仅一部十四世纪羊皮纸抄本传世,到十六世纪才见著录。《不娶妻文》却流布甚广,乔叟笔下的牛津学生爱不释手,大概既是讽刺也是时代风貌的真实写照。Theofraste即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古希腊逍遥学派哲人提奥弗拉斯特(约公元前372-287)。中世纪有一篇《提氏论婚姻金书》(Aureolus liber Theophrasti de nuptiis),归于他的名下。《金书》与《不娶妻文》齐名,也是攻讦女性、鄙视婚姻的布道文章。巴斯妇在《开场白》里还列出小丈夫“淫书”中其他篇目的作者,诸如奥维德、特尔图良(二世纪教父)、圣杰罗姆(约342–420,教父、通行本《圣经》译者)等,都是古代关于贞操性爱与婚姻的权威。由此看来,牛津学生读的是一本讨论婚姻问题的名家“文选”。这也是中世纪书的常态:羊皮纸昂贵,誊写费时,最好一本书顶得上一部专题百科,有用的知识和道德教训一块儿收录其中。勤奋的学者,例如乔叟,会到各地的寺院图书馆去抄书(他自称拥有六十本这样的书,算是不小的私人收藏)。抄书也是寺院僧侣的一项收入,因为常有贵族和有钱人家出资请他们做书,题目自然取决于出资人的爱好和需要。寺院便成了中世纪文化知识,包括异教知识甚至一部分亵渎神圣的文字的保存者。这一艰巨而神秘的知识生产和流通过程,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先生在小说《玫瑰之名》里有生动细致的描写。
于是,我对巴斯妇小丈夫的“淫书”大感兴趣。当时听说牛津大学出版社新出一版《庭臣琐闻》,可是北大图书馆、北图和中科院图书馆都没有,连一九二四年的旧版本也没有。特尔图良、圣杰罗姆等教父的拉丁语原著倒是有一些,书中插的发黄的借书卡上往往只一个遒劲的签名:钱钟书。二手资料例如中世纪语文历史宗教等领域的学术期刊也少得可怜。写信去法国向我的老师波士夫人求助(见拙著《玻璃岛·圣杯》),她立刻买了一批书寄来,却是一套古法语传奇,也是乔叟借鉴引用的,但不属于牛津学生的“淫书”:应该是我的信没写清楚。只好报告李先生,题目太冷门,缺书,没法写论文。先生笑道,不错不错,我出那个题目是考考你。现在国内的条件,只够打一个基础;系统的训练和深入研究,你得出国留学。之后,根据我的兴趣和图书馆书刊资料,先生把论文方向定为乔叟的诗律研究;我选的题目,则是乔叟早年一首寓言体悼亡诗《公爵夫人书》的“四重音诗行的断续问题”。
一九八三年秋,哈佛燕京学社再度来华面试(前一年录取了张隆溪学长,再前一年则是赵一凡学长)。李先生和杨周翰先生、贝尔娜小姐做推荐人,我申请了哈佛和耶鲁的英语系,两处都中了。次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提前半年毕业。李先生大概是希望我进耶鲁的,因为那是他的母校。但学社的奖学金优先给哈佛,而且“乔学”在哈佛有悠久的传统和最强的教授阵容,我就到了哈佛。
在哈佛,先生替我打好的古英语和乔学基础马上“见效”,让我得以跳过中古文学专业必修的英语史、古英语基础和乔叟讨论班(seminar),直接进入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的学习以及古典与中古语文的训练。而博士论文的选题也顺理成章,从乔叟的诗律转向全面的语言考据,即古法语《玫瑰传奇》之中古英语译本(格拉斯哥残卷)三片断中乔叟手笔的真伪问题。一九八七年过完大考(博士资格考试),即写信向先生汇报了论文选题,并提出翻译《贝奥武甫》。先生非常支持,叮嘱我翻译上的问题可向杨周翰先生请教(次年杨先生来美讲学,多有指导;见拙著《木腿正义》,中山大学,1999,页120),还写信给北京三联书店沈昌文先生大力推荐。译稿后来就由沈先生亲自编辑,于一九九二年出版(沈先生之谦虚认真,也让我十分感动:他把前言中感谢他的话删去了,封底也不印编辑姓名)。
这几年每逢同学聚会,常谈起在北大受教于李先生的两年。不是怀旧,而是有感于九十年代以来西学在中国的衰落;究其根源,则连着大学教育和学术的腐败。漫漫长夜降临之际,自然就格外怀念先生的学问风范。清华十一级外文系可谓人才济济,除了李先生,还有查良铮(穆旦)、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等;杨周翰先生从北大毕业前也是他们的同班。如今那一代英杰都逝去了。李先生论英国诗人、批评家阿诺德(1822-1888),曾写过这么一段话:蜜蜂用蜜和蜡布满蜂房,给人类提供了最高贵的两样东西:甜蜜和光明。阿诺德就此发挥,解作“美和智”,其完满的结合即理想的文化。我想,先生留给我们的,一言一行之中,正是那“蜜与蜡”一般的“美和智”的教育与学术理想。正是因为那理想的“甜蜜和光明”,我们在黑暗中的前行和抵抗,才有了信心和希望。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五日于铁盆斋;载《文汇读书周报》(二〇〇四年五月廿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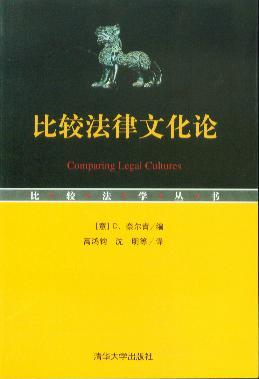 现在,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本翻译难度较大的书:多数篇章语言晦涩,论述抽象,涉及的知识领域众多,而且跨度很大。(读者如果有兴趣读一读原文的话,当知此言不虚:David Nelken, ed.,
现在,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本翻译难度较大的书:多数篇章语言晦涩,论述抽象,涉及的知识领域众多,而且跨度很大。(读者如果有兴趣读一读原文的话,当知此言不虚:David Nelken, 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