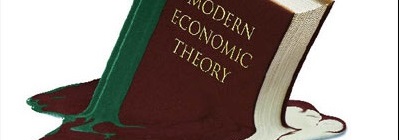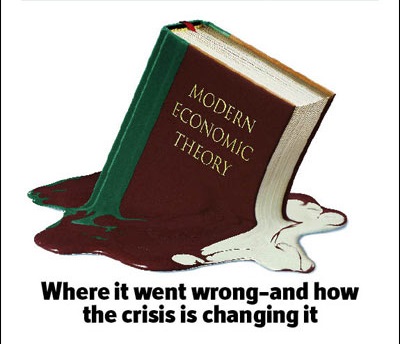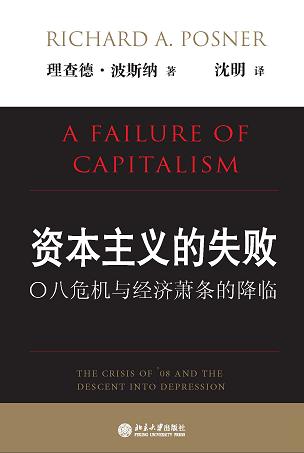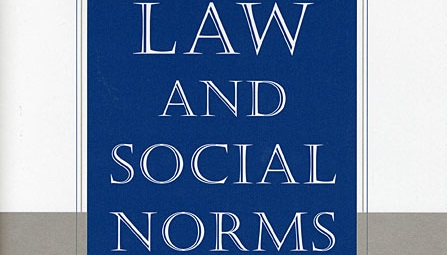“对牛乱弹琴”之“东拉西扯”终于说到了《中心化与个人》,我也忍不住想说几句。
洪波(KESO)的“错误”在于,作为一个明星网志作者,他不应该写这个“中心化与个人”的问题。因为在(1)反中心化的立场和(2)明星网志作者这两个前提之下,他不可能逻辑周延地书写,特别是关于他自己在公共话语空间中的位置。
我的看法是:在网志世界中,读者(或者“fans”)数量多,就是中心化。如果说,网志和门户网站、其他新闻网站一样都是媒体的话(网志作者们不是纷纷说“we the media”吗?),那么就此而言,网志和门户网站就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也因此,纯粹新闻性的个人网志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他们没法和真正的传媒企业竞争,或者退一万步说,他们至多成长为新的传媒企业(一个畸形的例子就是“博客中国”),即脱离个人网志的队伍。即使个人网志的队伍加起来,也没法和传媒企业竞争,因为在这时候,非中心化恰恰成为了致命缺陷。对于媒体而言,如果受众数量多还不是中心化的话,那么什么才是中心化呢?
洪波说:“中心化的核心在于,一个机构客观上控制了大多数资源。以新浪为例,因为新浪几乎成为传统媒体在互联网上面对读者的惟一通道,成为一个事实上的信息资源中心,所以新浪就成为一个中心,并具备了通过议程设置引导甚至误导用户的能力。此外,新浪还从这种中心化中获得了广告和其他的利益。”以控制资源的数量来界定中心化,原则上我同意这一点,然而洪波没有说明的是,“资源”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包含哪些内容。现如今,人们不是常说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吗,一个控制了很多注意力(就是说,具有很多受众)的媒体算不算中心化呢?我认为算。在指出“新浪与大多数传统媒体签署了内容授权协议,让大多数传统媒体变成了它的签约供稿者”之后,洪波得出结论“新浪则成为这种雇佣关系中的雇主”,我觉得这是相当意气用事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件事不过是普通的商业交易和市场分工而已。至于广告收入等等,就更没什么好说的了:商人(合法地)赚钱难道不是好事吗?(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甚至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谁会愿意生活在一个商人不赚钱或者没有商人的社会中?
和洪波谈到的“新浪”相比,“对牛乱弹琴”不算中心化(“其实,我的blog的读者不算多”),然而在中文网志领域中,有目共睹,“对牛乱弹琴”已经非常中心化了,而且就上面说过的“媒体”这一点而言,“对牛乱弹琴”的中心化和新浪的中心化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对于这一点可能会有种种反驳意见,我预先的回应是:对于所有网志作者来说,尤其是对于洪波来说,DONEWS并不是最好的(也不是第二好的)BSP(从技术性角度来评价),为什么他的网志始终还“坚守”在那里呢?至于洪波所说的“光Bloglines上拥有几千乃至数万订户的,就不在少数,他们都中心化了吗?恰恰相反,他们反映的是去中心化的力量”——这是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意的。
在另一篇文章《RSS与互联网去中心化》中,洪波把互联网去中心化的希望寄托于RSS等技术:blog和RSS本质上“都是基于个体的,去中心化的。……RSS的个人性,表现在它的聚合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的。”这同样难以令人信服。在“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的”一语前面,我们到底可以放上去多少个不同的主语,有谁能说得清?再说,RSS也是“天下之公器”,传统媒体巨头们(CNN、NYT、Washington Post、BBC等)不也纷纷采用了RSS服务吗?去中心化,肯定要靠技术手段,然而未必是RSS之类的技术。“代码就是法律”,“架构就是政治”,去中心化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也许只能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代码所构建的技术架构才能实现(前提是,去中心化是一个可能追求而且值得追求的目标)。就此而言,RSS、Web 2.0之类的热门话题与“去中心化”的关联程度其实还不及GWF及其背后的Cisco之类的企业政治行为呢。
就像其他一些流行的观念一样,反中心化的立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中心化固然会带来种种弊端(其实人们总是在享受着中心化的好处的同时批评其弊端的。请想一想微软和Google吧。对了,你猜着了,我要说的就是那个词儿——“不厚道”),然而,一个大致合理的世界不过是通过较为公平的竞争由一些“中心”取代另一些“中心”而已。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叶芝所谓“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在“基督重临”之前的此岸世界是不可能发生的。
有点扯远了,回到开头的问题,总结一下:洪波是一位明星网志作者,他拥有数量众多的读者和“fans”——如果这是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事实的话,那么,他就只能放弃反中心化的立场,至少(其实是至多)不公开(书写)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中心化与个人》这篇短文的发表不禁使我猜测,洪波兄似乎忘记了维特根斯坦的箴言:对于那些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