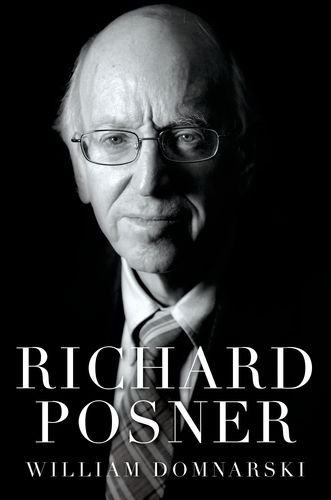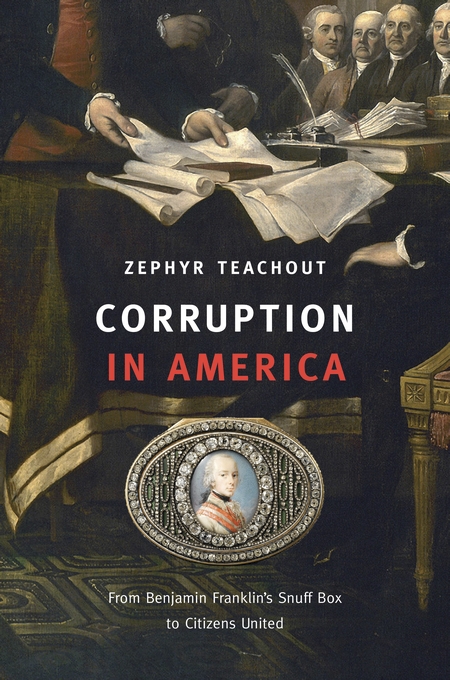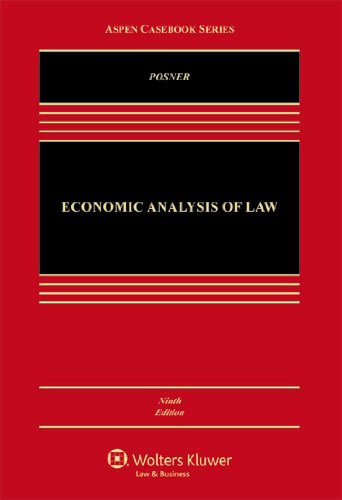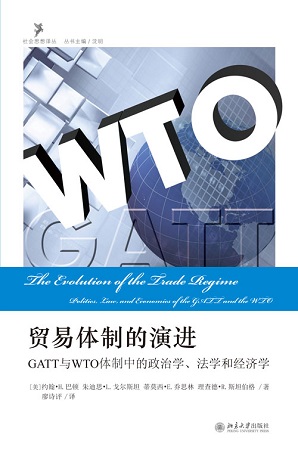清末民初以来之中国政治,最显明特征是政党的兴起。区别于帮会、家族、道门、公司、学社等各种连带手段,政党以更强的组织力纵横于近代政治。[1] 梁启超言:“故曰天下者,党派之天下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故文明之国,但闻有无国之党,不闻有无党之国”;[2]“天下不能一日而无政,则天下不能一日而无党。”[3]
列宁主义政党以最强大的组织效能和政治统合力,凸显于民国政党林立之间。被称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的胡适于1926、1927年在英国、美国演讲,告诉英美听众,虽然西方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科学和文明,但只是皮毛而非实质性内容。苏俄共产党带给中国的俄式政党组织功夫,才是中国人学到手的第一项真本事,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4] 毛泽东在1939年认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5] 党的建设,一是思想建设,二是组织建设。1942年,为克服各机构之间“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中共中央决定在组织上实行党委对党、政、军、民、学各项事务的一元化领导。[6]
对于一元化领导,二战后日本防卫厅总结对华作战时认为:军事的成败在于军事以外的力量。进行总体战争,须有一个包括全体国民在内的有机的组织。中共的组织特色是党、政、军三位一体,军和政是党的两臂,党挥动两臂以推动革命,兼有政治、经济工作、社会思潮等非军事力量,形成了一个从中央直到基层、以党为中心的具有强大统制力量的军、政、民的巨大组织体,完全能够适应总体战的要求。[7]
战争环境中的“党委一元化领导”方式,作为革命党的成功夺权经验,鼓舞了建国之后和平时期的执政党。如日后彭真讲话称:“我们说,各级公、检、法机关,还是由各级党委来统一领导,党的领导还是一元化。这个一元化,我们长期经验证明是好的。”[8]“党委一元化领导”思想的两层蕴意之一,在于财经、政法、文教卫、工青妇等事务悉纳入党委统一领导范围。其中,党委对公安、检察、法院等政法机关的领导,在近年被中央决策层突出强调,在语词修辞上被简练表达为“党管政法”[9]。“党管政法”与“党管干部”[10]、“党管武装”[11]一起,构成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治理原则。在具体的组织方式上,“党管政法”,从武装夺权年代的无常设机构,到一届政协时期的过渡方式,再到设立党内正式组织机构,经历1949年建国后的最初十年,逐渐定型化。
本文对1949年至1958年间,“党管政法”思想如何一步一步表征、形成为清晰明确的机构的史实进行叙述,澄明其组织演化的线索主要在于诉讼结构和政治治理考虑:在诉讼结构单一化和侦查中心主义观念下,“党管政法”事实上主要表现为“党管公安”,作为一个党内协调政法各事务的机构无存在需要。侦查—批捕—预审—起诉—审判—执行和司法行政事务等不同职能分立的形态确立后,战争年代一元化领导思想、总前委的组织设计经验被运用于政法场域,建立了统筹、协调政法各职能的机构。在这一机构的形成过程中,中共中央基于各种政治因素、党的内部治理框架考虑,进行不断的调整,逐渐完成了政治顶层的机构设计。文革前17年,彭真作为最高决策层内对政法机关进行领导的负责人,其经验直接影响了他于文革后复出重新领导政法后的工作思路。这一组织史表达,因此不仅只是一种历史叙述。
一、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
中共中央在延安时代后期开始形成稳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大量政治、军事、社会治理技术亦在延安时期发轫、成形。但是,处在武装夺权年代,作为常规化政治下治理工具的法律之治显得冗余。中共中央所在的模范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法院,仅是一个四人编制,并且与行政合一,受“三三制”下的政府领导的法院。[12] 以今日诉讼法侦查、批捕、起诉、审判、执行之分类方式视之,其当时最重要的诉讼活动是侦查(锄奸—保卫),而这一活动由设于党委内的工作机构中央社会部和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政治部锄奸部担当。[13]“党管政法”表征为党管公安。
在史前史时代,曾有名称上易导致误解歧异之机构:1946年6月成立由谢觉哉为主任委员、王明等11人组成的“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14],其任务是“从新的观点出发研究法律”和起草宪法草案。[15] 1948年8月,该委员会改组为由王明为主任、王明夫人孟庆树等9人为委员的中央法律委员会,[16] 其任务亦只是草拟法律、编译法律书籍等。[17] 在机构职能、设立思想、人员构成上,两者与“党管政法”机构完全没有传承。在政权建立之前的军事战争年代,法制叙事是无声息的。[18]
1949年9月第一届政协会召开,开国建政。毛泽东在成功夺取政权进城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党内布置工作任务转变时有一个著名陈述:“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19] 在与该讲话一起构成《共同纲领》之政策基础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更明确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20]
具体担当国家暴力垄断的机构,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基本建立。由于政务院不可能经常领导中央人民政府的30个部级单位,政务院下面设4个委员会协助办理各项事务。[21] 其中,设政治法律委员会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22]
但是,政治法律委员会从一开始即在组织体制上不顺畅。《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条规定政务院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最高法院及最高检察署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及检察机关,4个机构平行设置。从《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周恩来的说明可见,政治法律委员会指导的机构,在法理上不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但是,在日后董必武的表述中又称:“政法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四点:1、指导、布置、监督和检查民政、公安、司法、法院、检署等部门的工作……。”[23] 政治法律委员会与法院、检察署的这一关系的根据,并非来自法理,而是来自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个人委托。在1949年10月21日政治法律委员会成立大会致词中,董必武说明:“政治法律委员会隶属于政务院,任务是负责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并受主席毛泽东和总理周恩来的委托,指导与联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24] 这样,与政务院平行设置的最高法院、最高检察署,又同时受政务院下属的政治法律委员会指导,在政权组织关系上显示出不圆融。
不过这只是枝节问题,重要的是1949年10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和组织架构只是毛泽东设计之社会主义革命尚未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尚未开始之前的过渡时期政权的机构。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时,四野西线38军113师正在湖南怀化与国民党刘嘉树兵团激战,四野主力尚在怀化、宝庆、衡阳湘中以北一线,准备和白崇禧部队进行衡宝战役;一野和华北野战军19兵团刚分别进行完兰州、宁夏战役,准备进军新疆;二野正在从江苏、浙江向湘西隐蔽集结,准备进攻西南五省;三野正在准备攻打福建厦门。[25] 长江以南和西南、西北的大部分地区尚在国民党控制之中,新解放区土改、镇反和建立基层政权都未进行,政治和经济基础上的阶级力量对比尚未彻底变化。
所以,此时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是联合政府,整个政权架构只是毛泽东1940年筹划之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两步走之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26] 在政务院的4个副总理中,共产党员2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21个政务委员中,共产党员10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1人;各部、委、院、署负责人93人中,共产党员51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42人。[27] 从作为联合政府的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的人员组织构成来看,中共中央不会将政法领导职能尽托付于此机构。
1949年10月成立的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为董必武,副主任为彭真、张奚若、陈绍禹、彭泽民。在这5人中,主任董必武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在当时的4位副总理中,郭沫若和黄炎培都是民主人士,董必武为排名在陈云之前的第一副总理。彭真在这一时期同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28]、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等多个要职,主要精力在建都之初的北京市的工作。[29] 对于他们来说,这样一个职务只是兼职。
另外3位副主任中的彭泽民是归国华侨,曾任武汉国民政府海外部长,后赴香港行医,建国后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30] 张奚若是无党派人士,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31] 陈绍禹即是王明,“延安整风”尤其是七届二中全会之后的陈绍禹(王明)仍然出任了副主任,似可见该机构之份量。[32] 王明在担任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法制委员会主任期间,起草了《婚姻法草案》,[33] 但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12月,王明和妻女赴莫斯科养病,1956年1月再次赴苏联养病,直到1974年去世。或许是认为这两个职务过于边缘化,日后王明在配合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进行论战的自传性作品中,对其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任职事务未著一词。[34]
对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的47名委员,[35] 根据其各自的党派政治身份分类如下:
(一)中共党员17位:罗荣桓(最高检察署检察长),吴溉之(最高法院副院长),李六如(最高检察署副检察长),谢觉哉(内务部部长),武新宇(内务部副部长),罗瑞卿(公安部部长),杨奇清(公安部副部长),李木庵(司法部副部长),张曙时(法制委副主任委员),李维汉(民委主任委员),乌兰夫、刘格平(均系民委副主任委员),陶希晋(政法委秘书长),吴玉章(中央委员),邓颖超(全国妇联副主席),廖承志(全国青联主席),谢雪红(台盟主席)。
(二)非中共党员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30位:沈钧儒(最高法院院长),张志让(最高法院副院长),赛福鼎(民委副主任委员),蓝公武(最高检察署副检察长),陈其瑗(内务部副部长),史良(司法部部长),许德珩、陈瑾昆(均系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张文、王葆真(均系民革中常委),李任仁(民革中执委),周鲸文、刘王立明、叶笃义(均系民盟中委),郭冠杰、郭则沉(均系农工党中执委),黄琪翔(农工党),陈铭枢、郭春涛、许宝驹(均系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常委),陈演生(致公党中常委),易礼容(全国总工会常委),李秀真(农民劳动英雄),邓初民(教授),吴耀宗(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辑部主任), 周善培(实业界),颜惠庆(慈善界),林仲易、章士钊、江庸(均系律师)。
这样一个人员组成结构,显然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组织,在政治上较难完全实现共产党的意志。刘少奇在1949年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即就此点向中共中央进行提醒。从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可见整个政协的人员结构:“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一百卅四人,其中党员四十三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四十八人,中间人士四十三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十六人,在进步人士中有十五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36] 在政治法律委员会30名非党人士中,虽然赛福鼎很快入党,另有“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许德珩、陈瑾昆等人和李秀真这样的晋察冀翻身农民,或还有秘密党员,但是毕竟还有相当多与共产党“半条心”、“两条心”而不是“一条心”的人员。
而由前文可知,政治法律委员会职权是“指导、布置、监督和检查民政、公安、司法、法院、检署”以及指导或联系民委、监委,所列各部门中较多属于权力份量很重的机构。其中的公安部是由此前的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合并而成,最初纳入中央军委序列,称中央军委公安部,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与“枪杆子”并列的“刀把子”机关。非党的民主人士切入此要害部位,与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路线相冲突。彭真在全国公安会议上公开表达了这种担心:“民主人士要求什么都与闻,甚至想了解侦察工作,参加侦察会议,这是不行的”;“我们整天与民主人士、开明士绅在一起,不要认为他们不会影响我们,其实,他有他的生活方式、作风,如政法委员会就有这种经验,他们总想影响我们,连一个术语都要坚持。我们是领导他们改造他们的,我们随时要自觉,否则会受影响。”[37]
除政治法律委员会组成人员之外,在政治法律委员会指导、联系的部、委、院、署中,联合政府、过渡政权的特征亦十分显明: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司法部部长史良均是民盟成员,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志让曾为北洋政府大理院推事,时为无党派人士。[38] 最高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因肾癌体弱以及主要精力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实际由两位副检察长主持检察工作,其中一位副检察长蓝公武是无党派人士。[39]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在1927年11月被开除中共党籍,时任民革中央常委。[40] 在公安、法院内部,在接管国民党政权的警察局、法院、审判厅的时候,均留用了大量旧警察和推事,[41] 尚待进行司法改革。
在这样的态势下,中共中央选择了另外的治理机制。
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
早在1927年第三次修正《党章》开始,中共“在所有一切非党群众会议,及执行的机关(国民党,国民政府、工会、农协会等等)”中的治理对策就是组织党团。[42] 七大以后,将“在政府、工会、农会、合作社及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中”的党的指导组织“党团”改称“党组”。[43] 1949年11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署成立联合党组,由罗荣桓任党组书记。最高法院、最高检察署实际主持工作的,分别是中共最高法院党组副书记吴溉之和党内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李六如。中央政府司法部内担负实际领导职责的,是中共司法部党组书记李木庵。这样,对公安、法院、检察署、司法部内部的党组等进行领导的,亦只能是来自党的机构,而非统战性质的组织。
1950年1月9日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成立,共11人,书记为周恩来;政法分党组干事会为9人,书记为董必武,干事为彭真等8人。195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指示调整政法委员会党组干事会,增加彭真、罗瑞卿为干事会副书记,增加吴慨之等4人为干事会干事。[44]
此后,政法方面的最重要的政策指示不是由中央人民政府或政务院向政治法律委员会发布,而是由中共中央、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向政法分党组干事会发布指令。[45] 政法机构内的重要事务系由政法分党组干事会做出决定。通过党组以党内方式向公安、检察署、法院、司法部党组进行命令传递、工作动员,是这一时期政权运作的突出特点。[46] 在1951年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彭真表态说:“党的领导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过去很模糊,我们应该明确是公开的、合法的。实际上我们党在领导着,但不说不承认,反会引起民主人士的怀疑”;“不知哪来的一股风,似乎党的领导不能提。”[47] 1952年7月前后,董必武、彭真、罗瑞卿等人先后生病,董必武专门召集了政法五机关处长级以上党员干部进行讲话,他强调:“五机关的工作将由民主人士来领导,党不依靠党委和支部这个集体力量还依靠什么呢?”[48] 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202次政务会议,讨论政治法律委员会《一九五四年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时说:要做好公安、检察、监察工作,第一是党政统一领导。[49]
但是,这种党内通过党组间进行领导的方式,有违党内关于条块关系处置之基本策略。根据七大《党章》规定:党组干事会及书记,由所属党委指定之。党组,服从各该级党的委员会之领导,并执行其决议。[50] 这就排除了党组之间的隶属、领导关系,而均应只服从所由产生的党委。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政务院成立党组,在政治法律委员会等4个委员会设4个分党组,最高法院及最高检察署成立联合党组。按照七大《党章》规定,政务院党组、政法分党组,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署联合党组,均作为党组,党内关系平行。中共中央的该决定中亦明确重申:“上述政务院党组与最高法院及最高检察署联合党组之间,无领导关系,均分别直属于中央政治局领导。凡党中央一切有关政府工作的决定,必须保证执行,不得违反。”[51]
除此党内体制问题之外,政治法律委员会及其分党组干事会在运转效率上也有极大问题。政务院4个委员会设立后,不是一个普通的办事机构,而是突破政府组织法规定,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各部委院之间的一个新层级。周恩来说:“政务院设有四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相当于政务院的一个分院。”[52] 董必武更明白说明:
“关于联系与指导性的委员会,如政法、财经、文教等委员会是否列一级的问题,在第四小组的讨论中,曾经有三种意见:一、算作一级,像现在组织法上所写的那样。二、不算一级,不发号施令。三、不规定是否算一级,由事实发展去决定。现在政务院下有三十个部门,如果每周开一次政务会议,一个部门的工作,每月无法轮到讨论一次。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故肯定把它列为一级,以便联系和指导与其工作有关的各部门工作。这样,各部门的工作是受双重领导,一方面受政务院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受其所隶属的指导委员会的领导。”
董必武还强调,政治法律委员会等“四个委员会,地位较高,故在图中的部位亦较高。政治法律委员会所指导的部门以黄色实线表示之”,政务院对政治法律等指导性委员会和各部、会、署、院、行均有直接指挥之权,以黑色实线表示之。[53] 这一时期,中央层级内负责文件信息综合工作的办公厅,即有政务院办公厅、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三个。
此中央政府内三级体制在政法机关的具体运作,在以下实例中可见:1950年7、8月间公安部召开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内务部召开第一届全国民政会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署、司法部和法制委员会召开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三个会议开完,8月12日,政法分党组书记董必武给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书记周恩来写书面报告,汇报三个专业会议的情况,并提出需报中央研究解决的问题。周恩来“对报告有些意见”,耽搁一段时间后,再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54]
由此体制,可以分析出三点:
第一,从各院、部、委、署,到政务院4个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再到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再到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不计算地方上的大区、省、专署、县,仅中央一级内有如此多层级,低效率以及信息在层级之间的衰减较难克服;
第二,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成为除军委之外政府各部、委、院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署(党组)等所有机构与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主席请示、汇报的前置程序,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从外观上有被棚架之感;
第三,政务院各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和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对于各部、委、署(党组)的请示汇报,不是一个简单地向中共中央的转呈、呈递,而是依本机构职权有处理、筛选。中共中央即在实际上被搁置于一线工作之外。
毛泽东很快察觉出此问题,并以毛泽东风格的方式对此进行了严厉斥责。毛泽东告诉公安部长罗瑞卿:报告要直接送给我,不直接送我不行。要知道,我们这里是有仓库的。[55] 罗瑞卿立即将公安部召开的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总结等会议文件送毛泽东。在罗瑞卿起草的该文件上有几处述及党的领导,“曾被一位较负责的同志删去”,[56] 毛泽东在该文件上批示:“凡将党的领导作用删去而改为笼统字眼或改为单纯行政领导的地方,原稿是对的,删改是不对的,均应恢复原稿。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57] 1950年9月13日,毛泽东另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批评信:“政法系统各部门,除李维汉管的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中央有接触外,其余各部门,一年之久,干了些什么事,推行的是些什么方针政策,谁也不知道,是何原因,请查询。”对此,毛泽东要求“以上情况,请作一总检查,并加督促。”[58]
组织上的不圆融、低效率、毛泽东的政治考虑、作为过渡时期在政权人员安排上进行的统战考虑等因素,使得政治法律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这一机构,无法在当时顺畅运作。
因此,当1952年朝鲜战场局势稳定转入谈判后,中共中央即开始转入国内问题。1952年6、7月间,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将大区书记调至中央,对大区中央局、大区政府限权,以逐步撤销6个大行政区层级,加强中共中央对各项事务的统管权力。[59]
“新税制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加快了对体制的变动。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结果导致各地物价波动和抢购。毛泽东看到山东分局、北京市委等地的报告和报纸后,方才知道新税制之事,遂于1953年1月15日对周恩来、财政部部长薄一波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政务院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60] 同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文规定,“今后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需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后,始得执行”,“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直接提请政务院批示或办理的事项,除例行事务外,凡属涉及方针、政策、计划的事项,均应限于中央已经讨论和决定了的问题,或是中央已经批准的计划成批准的原则范围之内的问题”,并认为“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 [61]
在毛泽东筹划新政体的期间,1953年更发生了高饶事件。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讲了高岗“两个司令部”问题之后,当天午后即带着宪法起草小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乘专列离开北京到杭州起草宪法。[62]
新近发生、正在发生中的事件所形成的语境,最直接影响认知。1954年宪法表现出的整个政治治理的基本结构,是上述诸多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杭州期间起草并于1954年9月一届人大通过的《宪法》,确立了沿用至今的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体制,“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改为仅指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国务院,[63] 人大及“一府两院”均受中共中央领导。新结构按照毛泽东1953年编的八句歌诀中所说,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64]
基本政治治理结构变动后,1954年10月,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国务院的组织和工作问题》的报告,决定国务院成立以政法、文教、重工业、轻工业、财、金、贸、交通、农、林、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序的第一至第八办公室。其中,公安部长罗瑞卿兼任国务院第一(政法)办公室主任,协助总理领导有关部门的工作。经1954年11月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发布《关于设立、调整中央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有关事项的通知》,设立上述8个办公室协助总理分别掌管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工作,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属政治法律委员会等机构的工作结束。[65]
至此,在顶层政治设计中,不再有具体指导政法各机关和各项事务的机构。
三、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
1954年《宪法》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颁布实施,建立西方近代意义的司法体制格局后,司法实践与既有政治观念形成的张力所映衬出的组织空白,不久即被中共中央决策层感觉到。
原本按照1951年董必武的说法,设立政治法律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指导、布置、监督和检查民政、公安、司法、法院、检署等部门的工作;二,负责各部门的互通声气,互相帮助的工作,大家互相配合,则易解决问题;三,在统一领导下,政法各部门能通力合作;四,政法各部门的力量不一致,应相互照顾,相互靠拢一点。[66]
但是,政权初建,政法各机关人数极少,工作难以开展。1951年7月,全国还有四分之一的县没有法院, 2200多个县市,其中只有300个县市有检察署,政法方面最健全的公安机关,还有80多个县无主要负责人。[67] 1950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人民检察署四项规定的通报中要求,“1、因干部缺乏,且为工作便利起见,各级检察机关可暂同公安部门设在一起。2、各级检察长最好暂从公安部门正副负责人中择一人兼任,另选一人为副,以专责成。”[68]
所以,土改期间,由农会选出审判员若干人,在城市,由工会及其他人民团体选出审判员若干人,由县或市政府委派审判员若干人,共同组成人民法庭进行审判,人民法庭有权判决被告死刑、徒刑。人民法庭的上级机关为县或市政府。被告不服人民法庭的判决时,向县或市政府司法机关提出控诉。[69] 1950年“双十指示”后到1953年的镇反,在西南、西北、长江以南广大的军管地区,由各地军区司令部、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剿匪指挥机关所组织之军事法庭进行审判。[70] 1951年5月决定收缩之后,捕人批准权在地委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在省一级。[71]
因此可做如下概括:第一,作为常设的公检法机关之间的工作“相互照顾、相互靠拢”并无运行故障。第二,即使已设立的公检法司各机关偶有工作意见不一致,但各机关均依照简约的党的指导性政策办事,没有坚硬的程序法、实体法所形成的制度性制衡、冲突。第三,当时政法体制是“大公安、小政法”,公安作为绝对老大,弱势边缘的法检两院和司法行政机关是工作配合、协助,政法各机关间不产生日后侦查中心与审判中心的冲撞,侦查、审判与检察院监督权的冲撞。第四,在当时的诉讼结构和战争年代以来侦查中心思想下,公安机关由党委直接紧密领导,党掌握公安工作即抓住整个政法事务的中枢,如1949年10月周恩来接见全国公安工作高级干部会议的与会人员时所说:“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72]
所以,由一个专门机构进行统揽、协调并无产生的需要。[73] 政治法律委员会1951年仅拟在省级以上政府内设立,协助政府首长主管政法各部门业务方针政策的研究、拟议、执行及其相互关系和内部组织的调整、联系、统一。而直接办理绝大多数案件的专区、市县基层,则不设立政治法律委员会。规定“专署级县级人民政府有必要并有条件时,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逐步设立政法联合办公室。”[74] 1951年11月,全国编制会议在给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的报告中提出整编意见,将中央法制委员会和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合署办公。政委、财委、文委三委员会,只设到省(市)。政委、文委在大行政区和省(市)只设委员会,不设编制名额。[75]
由于朝鲜战争结束,土改、镇反完成,从1953年开始“一五计划”,整个政权进入常规化时期。1954年《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逮捕拘留条例》颁布,近代西方形成并定义的侦、诉、审、执、羁押型强制措施批准、司法政务担当等诉讼和诉讼辅助各职能的承担机构初具。但是,中国的刑事诉讼建立了既不同于此前民国时期“五权宪法”下突出司法院作为最高五权之一,司法院下辖最高法院、司法行政部等机构,检察院设于法院内,检察院领导警察侦查的格局,也不同于英美以法院为整个诉讼进程的中心、控辩平等对抗的诉讼结构,而是碎化诉讼职能,将侦查、批捕、预审、起诉、审判、执行由不同机关承担,各机关之间“互相配合、互相监督”。[76] 这样一种指导思想,被写入反映中共中央文革前基本政治治理纲领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77] 此外,司法行政机关也实际楔入诉讼结构,切分了部分权能: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任命下一级地方法院的助审员,负责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法院的人员编制和办公机构也由司法部规定。
但是,一旦由不同机关分阶段、分职能地完成诉讼,其间必然会发生不一致而形成冲突,不批捕、退回补充侦查、不起诉、撤回起诉、判决无罪或改变罪名、抗诉等成为诉讼常态。而战争年代以来,一旦要由不同隶属关系的机构共同完成一件任务,中共中央的基本政治应对策略就是成立一个涵括一切该任务目标内的机构,由该机构总揽全局,统一协调各方,以最大程度节约交易成本,实现中心工作。
1942年华北八路军面临日军残酷的“治安战”,华中新四军面临日伪前所未有的“清乡”作战时,中共中央提出“一元化领导”思想,并做出重大组织调整应对,要求“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 [78] 决战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遂行大规模的作战,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必须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以协调和指挥各部队的作战行动,并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负责。”[79]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战区内有中野、华野两支野战军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以及地方党委苏北工委、冀鲁豫区党委。毛泽东电令“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一个‘统筹一切’的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80] 1949年1月平津战役,战区内有东野、华北两支野战军7个兵团和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以及平津两个地方市委、两个军管会等机构,毛泽东下令成立平津前线总前委,“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他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以一事权而免分歧。两市委、两军管会关于上述工作均直向总前委请示,由总前委向中央负责。”林彪为总前委书记。[81] 1949年3月晋中军区地方部队3个独立旅、第四野战军炮兵1师和华北野战军18、19、20兵团、第一野战军第7军围攻太原,3月17日,中央军委亦决定成立太原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由徐向前任书记。[82] 总前委机构的设立,是1942年以来一直坚持的“党一元化领导”思想的一个具体组织表达。
建国之后,因袭战争年代的语词,将文教、财贸、工业、农业、政法等各行业均称为“战线”,而“政法战线”担负着和平时代对付“不拿枪的敌人”和“国家安危,系于一半”的责任,被认为是一个仅次于军事作战的真正的作战领域。但是,1954年初具格局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结构创立后,中共中央体制内部并无一个“政法战线”的总前委来统筹、协调政法各机关之间的姿态和矛盾、冲突。前述政治法律委员会被撤销后,由公安部长罗瑞卿担任主任的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政法办公室)仅负责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监察部的工作。但是,在横向关系上,国务院一办仅是在国务院内四个部的协调,完全不涉及与国务院平行的两个政法机关——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
在纵向关系上,在政法、财经、文教等所有事务上,国务院一办也不可以单独向各省市委发布指令。这一设计是1954年《宪法》和毛泽东歌诀中所清楚表达的,通过1955年严厉斥责财政部的一个事件,毛泽东再次明白地强调了这一体制。1955年1月财政部党组就关于目前税务干部中贪污盗窃国家税款的情况给国务院并报中央的报告上,末尾请国务院将这个报告批转各省市党委。毛泽东两次就该事情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七人写出批语。在批语中强调“这是财政部党组写给国务院,请它‘批转各省市党委’的一个报告。这种请政府命令党委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不止一个部如此,请作纠正”;“由国务院向各省市委下达命令的办法不妥,此类内部命令,似由国务院与党中央联名下达为宜。”[83] 从其具体操作上来看,这种作法似乎并不违反党的工作方式:由财政部党组提出,请国务院将报告进行批转,国务院可以以国务院党组的名义批转给各省市党委,从外观上看,还是一个党内工作报告下发。但是,如果国务院可以以这种方式给省市委党委下达命令的话,那么中共中央就在实际上无法“大权独揽”。
因此,1955年开始的肃反由中共中央成立的中央十人小组领导,各省、市党委成立五人小组领导。但这样一个小组是一个非常设的临时机构,[84] 而公、检、法、司所涉政法各项事务则是经常性的工作,依体制的结构性张力出发,势必要在中共中央层面有一个正式的机制。
实际上,早在1952年,毛泽东、刘少奇设计的中共中央机构的设置序列中,除了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外,即拟设立政法工作部,由彭真任部长。[85] 但因1953年高岗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出于复杂的政治考虑,政法部的设立被实际搁置,而此时这一体制张力形成的需要比1952年更加突出。1955年4月,刘少奇在向华北地区各省、市委负责人的谈话中,透露了中共中央的这种设计考虑:“苏联的经验是,政府有一个业务部门,党委有一个部管这个部门的干部和政治思想工作、检查工作。它不直接管业务,但也要懂得一些业务,就象军队中的政治部一样。我们将来恐怕也要这样做。”[86]
1955年12月,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并报毛泽东。该报告称:“目前政法机关的设置,各部门党组分别直属党中央,政法各部门缺少一个统一的协调组织。因此,建议在党中央设立一个法律委员会或法律工作组,协助中共中央加强对国家机关中政治法律工作部门的协调和统一领导。”报告还提议由彭真或罗瑞卿负责委员会的领导工作。[87] 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先后同意设立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1956年7月6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彭真任主任委员,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臣、中共司法部党组副书记陈养山任委员。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法律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部门的分工制约等问题,办理中央交办的工作。”第一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即是“公安、检察、法院、司法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88] 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成立,被认为是“在组织上解决了国家机关中政法部门的统筹和协调问题。”[89]
中央法律委员会成立后,关于“二次镇反的必要性和成绩的估计问题”、“少杀长判”、“多留少放”、“联合办公”等刑事政策、政法方面的重大事项,交由“中央法律委员会作了结论”。尤其是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对法律适用的不同理解和实践做法的冲突,均提交中央法律委员会解决。[90] “党管政法”思想在中共中央组织史上第一次生成正式机构。[91]
但是,由于中央法律委员会的成立迟于政治法律委员会,后者常被确定为是1980年设立的中央政法委员会的源始。[92] 而且,在1949年10月之后至1954年9月之前,在文件、领导人的讲话中,也确实多次使用“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政法委”、“中央政委”等称谓。[93] 但是其与“党管政法”思想下成立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仅是一种“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94] 这一时期所称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与时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组织角色、政制位置完全不同。
在当代中国政治的语言表述中,只有在能指( the signified)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时,所指(signifier)[95]才可以为“中央”。只有中共中央系统的工作机构和部门,包括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对外联络部、党校、政策研究室等,其机构名称前才可被冠以“中央”。此外的国家政权体系内的组成部分,包括全国人大、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虽然可被统称为中央国家机关,以示与地方相区别,但在机构正式对外名义上均不能称谓为“中央”。“中央政法委员会”这一名称,标明该机构系属中共中央的工作机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的简称。
1949年成立的“中央政法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的简称。此“中央政法委员会”之“中央”,是用以区别于华东、中南等六个大行政区的政治法律委员会。在1954年撤销大区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之前,大行政区的机构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名称相同,[96] 尚没有中央政府一级称为部、省一级为厅、市一级为局的这一依层级划分机构名称的区分。此一时期中央政府系统内的机构与中共中央的机构一样,均冠以“中央”,以示与大区中央局、行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的同名称机构相区别,如中央公安部,区别于华东公安部、中南公安部;中央水利部,区别于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称中央政法委以示区别于非大区行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此处的“中央”只是相对于地方而言,是在政权层级的最高一级意义上使用,中央法律委员会和1980年成立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之“中央”是相对于“边缘”使用,意指领导中枢。在1954年《宪法》颁布后,“中央人民政府”作为组织名义不再使用,中央公安部、中央水利部等称谓罕用,冠以“中央”名义的机构,均为中共中央的办事机构或工作机构。
“中央”这一语词在“所指”差异上的辨析,使得回看“党管政法”思想在中共中央组织史生成之过程更加清晰。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设立,是“党委一元化领导”、“统筹一切”的“总前委”思想在政法事务内的运用,与1980年成立的中央政法委具有一脉相承的政治观念支持,是理解中共在执政年代如何逐渐形成“党管政法”思想的历史元点。
四、中央政法小组
从1954年《宪法》到1956年中共八大这一期间,中共中央确立了稳定的基本政治治理结构。然而,此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态和中国国内的政治、社会情势的发展,又促使中共中央不断做出局部调整。
1957年,作为中国共产党“老大哥”的苏联共产党发生了一场重大政治风波:1957年6月18-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马林科夫等六名主席团成员不同意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路线,决定解除赫鲁晓夫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只有米高扬、苏斯洛夫、基里钦科三人支持。但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国防部长朱可夫紧急调用军用飞机,将外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于6月22-29日召开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刚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重新改组了中央主席团,化解了政治危机。[97]
在中共党内,从红军时代、抗战、解放战争领导中国共产革命武装夺权成功,到出兵朝鲜取得战略胜利,毛泽东在重大战略的决断时刻,多次力排众议,最后以结果证明自己的正确,这使得毛泽东获得了巨大威望和自信。“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所有制的公有制改造,并且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因此聚合分散的力量在中国实现“打破常规”的发展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从1956年到1958年,毛泽东与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负责人周恩来、陈云、李先念、邓子恢等人在基本经济设计上发生根本分歧,双方经历了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大跃进的这一波状起伏式冲突。
具有与中国相同政治结构的苏联所发生的事变和中国国内事态,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产生了极大触动,促使毛泽东做出新的部署。
从1956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几十人的会上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后,1957年4、5月份至1958年,他又多次提出在1959年二届人大辞去国家主席,“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98] 在与政府内其他领导人发生分歧后,毛泽东下决心加快对“党—政府”的治理机构进行进一步调整,以组织路线变化服务于要在八大二次会议调整的政治路线。
毛泽东选择的方式,就是进一步将“大权独揽”于中央政治局和向中央政治局负责的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专门通过敲打政法机关,再次提“八句口诀”、强调反分散主义和党委的集中领导:“这几年反分散主义,创造了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政法机关有人提出,说是党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这不行,先不分,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权独揽,……小权小分,大权就不能独揽。”[99]
此后,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形式都进行了调整。1958年2月,毛泽东提出中央书记处对国务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来。周恩来提出设立五个组,党政统一。[100] 随即,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加毛泽东信任的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增加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以便把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的一些问题提到书记处讨论。”[101]
在改组了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后,依周恩来提议,195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政法等5个小组,毛泽东对通知进行了批改,增加了一大段“职权划分”的内容,回应了一年前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的意见,[102] 重申了1942年以来的“一元化”治理思路:“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103]
新成立的中央政法小组组长是彭真,时任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总书记邓小平负总责的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分管统战、政法和港澳方面的工作。[104] 四个组员中,董必武为政治局委员、最高法院院长,乌兰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张鼎丞为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从1956年7月的中央法律委员会到1958年6月的中央政法小组,主任委员和组长均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但是,从组织科层制上分析而言,以规范方式确定中央政法小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则祛除了个人角色因素,不因某个个人的进退迁转而改变结构关系。[105]
中央政法小组直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作报告,使中共中央对政法事务进行的领导变得日常化。根据八大修改的《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1956年9月八大期间,在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毛泽东对总书记邓小平说:“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106] 据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回忆,在中央决定邓小平做总书记时,邓小平曾向毛主席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专管党务,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仅负责承送。而毛泽东不同意,并强调书记处是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们做,抓全面工作,发文用中央名义。[107]
这样,如前所述,1954年10月后,政府各部、委均对应一个国务院办公室:一办为政法,二办为文教,三办为重工业,四办为轻工业,五办为财、金、贸,六办为交通,七办为农、林、水,八办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此后,各办公室又分别由中共中央一个部主管:三办、四办对应中央工业工作部,六办对应中央交通工作部,[108] 二办对应中央宣传部,五办对应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七办对应中央农村工作部,八办对应中央统战部。[109]
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5个中央小组成立后,在重要事权上,更强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力量。在政法领域,政府序列内的政法事项工作,由一办(国务院政法办公室)协调,一办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之上是中央政法小组,中央政法小组直接隶属于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至此,由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即被认为是毛派头子、“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首的邓小平[110]出掌中央书记处,为副帅,毛泽东作为中央主席掌握中央政治局,为正帅,将毛泽东认为已经产生和可能产生的分散主义消解,加强中共中央对全局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经历了1959-1961年的政法体制大变动和文革“砸烂公检法”,1978年后,各政法机关渐次发展或得到恢复。198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彭真担任书记的中央政法委员会。同年2月份,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111] 至此,1958年完成的“党管政法”制度设计,在经历文革时期的断裂后,延续至当代中国的治理。[112]
五、综 论
晚清以来,西方输入中国并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动的,不是铁路、电话、马克沁机关枪和蒸汽机,而是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式。毛泽东有此表述:“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13]
列宁主义反对不统一、不协调步伐、分散、各自为政、强调各自的独立性。仅在下部、中层治理上,适当建立分散权力机制,但其目的仅是防止隐蔽信息或某一个体独大,或使最高层无法及时进行政治判断或被架空。而在最高层,则要求有一个终极意志者,由该意志判断者综合协调、统一各方,以最大程度的节约交易成本而实现最大政治效能。
中国刑事诉讼法以区分职能、分阶段、交错的方式,将整个诉讼活动分配给公检法司机关:公安负责普通刑事案件的侦查,检察院批捕,公安预审,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同时,检察院又对公安、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的整个活动进行监督,并对其职务犯罪进行侦查。在1954年至1959年,地方法院助审员由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任命,最高法院助审员由司法部任命,地方法院的设置由司法行政机关报批,各级法院行政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法院人员编制和办公机构由司法部规定。[114] 在列宁主义的政治观念看来,这必然不能形成合力,因此必须由一个踞于其上的机构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西方的盎格鲁—萨克逊自由主义政治设计是:政制没有一个最后的权力行使者,为防止某个权力者对政治体形成伤害,所有权力以交错、互相牵制、制衡的方式存在,每一种权力都不可能突出太远,谁都动弹不得。在司法上,从侦查到起诉、审判,都在犯罪控制和适当程序(due process)平衡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以分散的权力运作方式设置警察、检察官、法官的权力。并在所有诉讼阶段引入律师参与,在侦查阶段引入普通民众担任的治安法官(the justice of peace),在起诉阶段引入民众组成的大陪审团(grand jury),在定罪上引入民众组成的小陪审团(petit jury),进一步碎化、分割常任的权力行使者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追诉权力。
亚里士多德说:“木材不能自成床,青铜不能自造像,这演变的原因只能求之于另一事物。”[115] 上述两种司法治理的不同,出自政治范式的差异。以西方的标准定义,国家就是在一定地域垄断了暴力和税收的组织体。[116] 而在列宁主义“政党—国家”(party-state)的治理形态下,暴力垄断这一国家核心定义即由“党管武装”和“党管政法”进行表达。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而“道术将为天下裂”。[117] 本文仅是依赖纸面文献的一个材料考订,关于跃出纸外的“行动中的”政法委的权力地位与政法各机关的具体关系,需要进一步的细致观察功夫,分裂之后的道术之争是跟进的主题。
[1] 关于这一背景参见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谢彬:《民国政党史》,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
[2]《政党说》,载《清议报》第78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二十一日。
[3]《论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将亡之中国》,载《清议报》第79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初一日。
[4]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237页。
[5] 毛泽东:《发刊词》,《共产党人》(创刊号),1939年10月20日出版,第5页。
[6]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载《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339页。该决定由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为中共中央起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华北治安战》(下),天津政协编译组翻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462页。
[8] 彭真:《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几个问题——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摘要)》,《红旗》1979年第11期,第7页。
[9]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意见》,中发[2005]15号;周永康:《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努力开创政法工作的新局面》(2007年12月24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132页。
[10] 《公务员法》(2006年1月1日实施)第4条。
[1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民兵工作意见》(2002年11月8日)。
[12]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次精兵简政实施方案纲要》(1942年6月1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汇编》(第6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页;《一九四三年边府工作报告》,《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汇编》(第7辑),同前,第458页。
[13] 《西北局关于目前锄奸问题的指示(初稿)》(1943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 一九四三(一) 甲3》,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第31-37页;李力:《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上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174页。
[14] 《谢觉哉日记》(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7页。
[15] 1947年,毛泽东正带昆仑纵队在陕北群山中与胡宗南大军周旋,革命前途尚未明朗,对一个由“革命老人”为主的机构起草宪法的作法,毛泽东在信函中对设立该机构的意图有含蓄表达:“宪草尚未至发表时期,内容亦宜从长斟酌”;“法律工作是中央新设领导工作的一个部门,兄及诸同志努力从事于此,不算‘闲居’。”《致吴玉章》(1947年11月18日),《致张曙时》(1947年11月18日),《致陈瑾昆》(1947年1月16日、11月18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0、288、290、292页。
[16] 《谢觉哉生平年表》,《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9页。
[17] 《中央关于中央法律委员会任务与组织的决定》(中央书记处1948年12月12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63页。
[18] 关于无声的司法之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861年梅利曼案(Ex parte Merryman)和1864年米利根案件(Ex parte Milligan )。
[19]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4页。
[20]《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88页。
[21] 《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1949年9月7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等:《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22]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1949年9月27日)第18条。
[23]《逐步建立和充实政权机构》(1951年11月4日),《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201页。
[24]《对中南局关于在地级以上党委设农委与政府设农村工委问题的批语》(1952年6月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25] 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97页;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295页;南京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82、399-415页;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531页。
[2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1940年第98、99期,第23页。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28] 1945-1956年间中共中央未设政治局常委,设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与1956年之后的中央书记处地位、职权不同。
[29] 彭真在1953年3月后接替董必武任政法委分党组书记,开始更多对整个政法事务负总责。《彭真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68页。
[30] 《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6-57页。
[31] 《浦薛凤回忆录(上)万里家山一梦中》,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57页。
[32] 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之后相距5年,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上仍集中谈了王明问题。对王明的最后政治认定,见《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265页。
[33] 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276页。
[34] 王明:《中共50年》,徐小英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35] 《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委员名单》,载《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0日,第1版。
[36]《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37]《彭真同志在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9月17日),《公安会议文件选编(1949.10-1957.9)》,公安部1958年9月出版,第114-115页。
[38] 《新中国第一代大法官张志让》,政协武进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5年10月编印,第37-69页。
[39] 罗东进:《我的父亲罗荣桓》,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页。
[40] 元邦建:《谭平山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 124、164页。
[41] 《关于接管平津国民党司法机关的建议》(1949年1月21日中央书记处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9-62页。
[42]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从一大到十七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43] 《中国共产党党章》(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通过),第60条。
[44] 《彭真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5、115页。
[45] 《中央转发政法委分党组关于司法改革工作报告的通知》(1952年7月9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313页;《对中央关于政法系统机构与干部配备等问题通知的批语》(1953年3月),《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页。
[46] 《董必武传(1886-1973)》(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39、752、784、789页;《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
[47] 同注37,第114页。
[48]《同政法部门党员负责同志谈话要点》(1951年7月),《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64-166页;《尊重党外负责干部的领导,加强党内外团结》(1952年7月16日),《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143页。
[4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页。
[50] 《中国共产党党章》(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通过),第61、62条。
[51]《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1949年11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九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
[52] 《必须加强文化教育工作》(1952年10月24日),《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53] 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基本内容》(1949年9月22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1页。
[54] 《在董必武给政务院党组报告上的批语和批注》(1950年8月17日),《关于送审政法部门总结报告事给毛泽东的信》(1950年9月13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168-171页、292-293页。
[55] 1950年8、9月间,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转告罗瑞卿:他同毛主席谈话的时候,毛主席说了一些话,意思是公安部不向他作报告,主席很生气。罗瑞卿立即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先问罗瑞卿为什么不给他写报告,罗瑞卿说写了报告。毛泽东说:写了,拿我的收条来看。并且说罗瑞卿:你的党性比××差,比××委的人差。他们××部,××委买茶叶的事我都知道,你们公安部的事情我不知道。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147页。该书作者点点为罗瑞卿的女儿罗峪平(罗点点)。
[56] 黄瑶等著:《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264页。
[57]《在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总结上的批语》(1950年9月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58] 《关于检查督促政府各部门向中央报告工作的批语》(1950年9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13页。——着重号为引者加。
[59] 在大体制变动前,在中央办事机构内的一个微调是取消了三个办公厅中的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办事机构,齐燕铭:《关于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办事机构给周总理和毛主席的信》(1950年11月5日),马永顺等编:《齐燕铭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6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235、250页。
[6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1953年3月1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72页;同注27,第136-137页。
[62] 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
[63] 1954年《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64] 毛泽东说:“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1958年1月21日),《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7页。
[65] 同注49,第419页。
[66] 同注23。
[67] 《关于筹设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方案的说明》(1951年7月20日),《目前政法工作的重点和政法部门工作人员存在的几个问题》(1951年9月11日),载《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168页。
[68]《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人民检察署四项规定的通报》,《检察制度参考资料》(第1编)(新中国部分),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1980年编,第21页。
[69]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26-227页。
[70]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1951年2月21日)
[71] 《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1951年5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页。
[72] 同注56,第249页。1990年,中共中央文件将公安“系于一半”的提法扩大为“政法部门系国家安危于一半”,足显政法格局变化。《中共中央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中发[1990]第6号),1990年4月2日。
[73] 1949-1954年间,政法委指导的内务部事权曾较大,但后来逐渐萎缩,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后更大为压缩。内务部(民政部)虽在此间和1978-1988年间列为政法口,但并未切入诉讼结构,与其他机关少有冲突。《民政部大事记(1949-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1988年编印,第3-89页;《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279页。
[74]《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关于省(市、行署)以上人民政府建立政治法律委员会的指示》(1951年5月31日),《机构编制体制文件选编(上)》,劳动人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602-603页。
[75] 《致政务院党组干事会》(1951年11月15日),《薄一波书信集》(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238页。
[76] 《在全国检察业务会议上的报告》(1954年11月21日),《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页;《在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6月9日),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
[77]“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3-54页。
[78] 同注6。
[79]《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3卷),军事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233页。
[80]《由刘陈邓粟谭组成总前委统筹一切》(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231页。
[81] 《中央决定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织总前委》(1949年1月1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479页。
[8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部队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第408-433页。
[83]《关于不能由政府向党委下达内部命令的两个批语》(1955年1月13日、1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84] 《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年8月25日),载前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134-148页。
[85] 《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问题》(1952年7月15日、18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337页。
[86]《关于党委领导和党政分工问题》(1955年4月),《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24页。
[87] 《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88] 同注29,第888页。
[89] 《董必武传(1886-1973)》(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15-916页。
[90] 《罗瑞卿同志在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1957年9月3日),讲话第三部分“政法四个机关的某些争论和关系问题”,《公安会议文件选编(1949.10-1957.9)》,公安部1958年9月出版,第543-545页。
[91] 1955年前后,在省级党委工作机构内,多设立与此职能相近的政法工作部。《广东省志·中共组织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中国共产党辽宁省政法志(一九四五-一九八五)》,中共辽宁省委政法委员会1996年印行,第21页。
[92] 曹思源认为,政法委源起于1949年建国之初政务院下设的政治法律委员会,并认为这个机构本是个临时机构,但却在《宪法》和《党章》中均无规定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应该早予撤销。曹思源:《政治文明ABC——中国政治改革纲要》,(纽约)柯捷出版社2004年版(Cozy House Publisher. New York),第107-109页。
[93] 《关于改革司法机关及政法干部补充、训练诸问题》(1952年6月24日),《关于司法队伍的改造和补充问题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刘少奇的信》(1952年6月25日),《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128、135页;《张鼎丞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30页。
[94] 关于“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的含义,[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95] 关于“能指”与“所指”的区分与联系,[瑞士]费尔南迪·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0-116页。
[96] 《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1952年11月17日,第1版。
[97] 《苏共中央(1957年)六月全会速记记录》,《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上下册),赵永穆等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09页;[俄罗斯]Ю·B·叶梅里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455-470页。
[98] 《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1957年5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57-461页;《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关于相机透露毛泽东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给宦乡的电报》(1958年7月3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4、332-333页。
[99]《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11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8月编印,第148页。——着重号为引者加。
[100] 《彭真传》(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66页。
[10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8页。
[102] 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大胆开展批评热烈进行争论 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座谈会》,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第1版。
[103]《对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958年6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269页。
[104] 田酉如等:《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页。
[105] 1959年5月8日,中央政法小组组长改由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罗瑞卿担任。庐山会议后,罗瑞卿出任总参谋长,谢富治调任公安部部长,并从1960年12月至文革初期,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
[106] 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107] 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第36页。
[108] 1956年11月,中央工交部分设为中央工业工作部、中央交通工作部。
[109] 李雪峰回忆说,1954年下半年,中央书记处下设四个办公室,其中中央一办主管政法工作,彭真任主任,罗瑞卿任副主任。李雪峰:《关于党的八大召开前后历史片段的回忆》,《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8页。但此回忆属孤证,缺乏有力量的文献支持。对中央书记处一办,有多个文献互相印证的描述是:根据1955年1月中央秘书长会议确定,中央书记处一办由中央办公厅一办人员略加充实升格组建,职责不变,仍为负责阅读各省市来往文电及其他材料,出席各省市重要会议,并向中央简报情况,提供意见等,由中办主任杨尚昆兼主任。《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8、1211页;《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问题》(1952年7月15日、1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34页;苏维民:《杨尚昆谈在中央办公厅二十年》,载《百年潮》2008年第7期,第18-19页。
[110]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 戎马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09-119页。
[11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通过)》,载《人民日报》1980年3月1日,第1版。
[112] 关于中央政法委较之此前具体职权的大改动,拟另文叙述。
[113] 同注20,第282页。
[114] 《人民法院组织法》(1954年9月28日公布),第2、14、34、40条。
[11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6页。
[116][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7页;[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胡景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美]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9页。
[117]《庄子·秋水》、《庄子·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