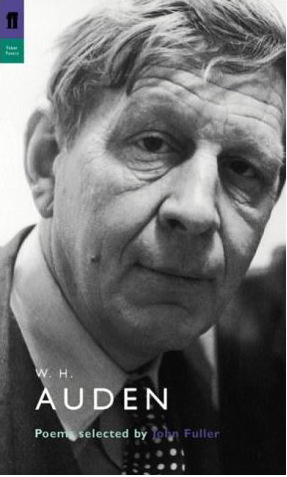臧棣: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
九十年代初,关于戴望舒的诗歌语言,余光中曾经有过一番发难。大意是说,戴望舒的诗歌语言有许多缺陷,远远没有达到成熟;而这样的有着致命语言缺陷的诗人,居然占据着新诗史上一个显赫的位置,是很奇怪的。由于诗歌是一个特殊的语言竞技场,所以,后来的诗人意识到前驱者的语言局限,不仅意味着他自身的成长,而且也是诗歌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但是,在余光中对戴望舒的责难中,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后来者对先驱者所依傍的语言资源和所处的语言环境缺少必要的同情心;不仅如此,余光中对戴望舒的语言才能的判断也极有问题。而最大的疑问在于,当我们用今天的关于诗歌语言的标准去衡量戴望舒那一代诗人时,我们所运用的尺度本身是否具有充足的客观性。
问题不在于戴望舒的语言是否成熟,或者是否完美,因为这太像是一种趣味之争。在余光中对戴望舒的责难中,让我感到不够公允的是,他的批评更多的是出于他自己的语言趣味;并且,他把自己的趣味当成一种客观的审美标准来运用。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戴望舒的诗歌语言不成熟,便令人疑窦丛生了。因为在新诗史上,就绝对的语言才能而言,大概只有两三个诗人能和他匹敌。当然,由于戴望舒所处的时代,新诗语言的整体水准比较低,这或多或少影响了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在个别的文本中,他的语言确实有不少毛病,但必须意识到,无论这些毛病有多少,它们和戴望舒对诗歌语言的自觉意识相比,和他所拥有的语言才能相比,甚至和他自己的另一些更优异的文本相比,都是非常次要的。在我看来,戴望舒目前在新诗史上享有的显赫的位置,不是由于其他的原因,比如,不是由于他在主题上的开拓精神,不是由于他在风格上的创新意识,恰恰是因为他在诗歌语言上显示了一种令人难忘的造诣。如果人们要在新诗的发展史上,为诗歌语言的进展和成熟树几块纪念碑的话,很多名声显赫的人都可以被忽略,但戴望舒的这一块碑是一定要树的。
也许,更需要我们自己不断省思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新诗语言的成熟?为什么很少有人指责小说的语言不成熟,或是抱怨散文的语言不成熟?新诗的语言,在本质上和小说、现代散文的语言是一致的。尽管有过一些短暂的偏离,如新格律诗运动,但在总体上,它根植于“五四”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语言观及其实践:即用来创作新诗的语言,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语言,而是一种和用来创作小说的语言没有什么本质差别的语言。不要小瞧这其中界限的消弭,它预示了一种新的诗歌理想,也揭示了一种新的语言态度:诗歌的语言应该趋同于日常语言。它更极端的主张是,新诗的语言应该口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