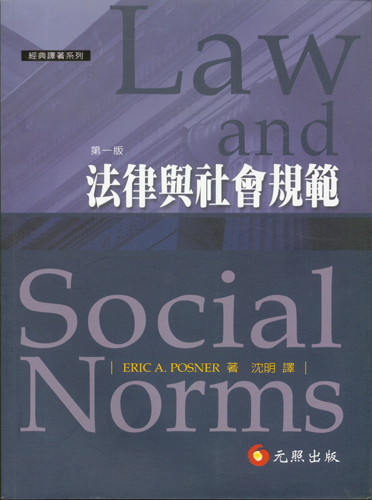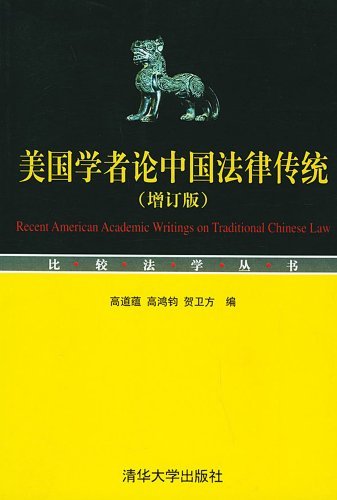Lon L. Fuller, “Positivism and Fidelity to Law – A Reply to Professor Hart,” 71 Harvard Law Review 630-672 (1958).
参考:H. L. A. 哈特: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的分离
何作* 译
哈特教授已经对法律哲学的文献做出了持久的贡献。我怀疑,他讨论的问题将来是否还能够完全再现他的分析力曾经所触及到的那种形式。他的主张并不是简单地对边沁、奥斯丁、格林和霍姆斯的简单重复。这些人的观点在他的分析中以一种全新的清晰的方式展现出来,并达到了一种新的深度,而这种清晰和深度完全是属于他本人的。
我必须承认,当我第一次接触到哈特教授的思想时,在我看来他的主张被一种深层的内在矛盾所困扰。一方面,他极力反对任何对“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的混淆。他绝不能容忍将法律与法律应当是什么的观点加以“合并”,至多容忍一种经过消毒处理的“相互交叉”。他的这一主张似乎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能确定我们谈的是“是什么”还是“应当是什么”,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任何知性的沟通都是不可能的。然而,正是哈特教授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上的不确定性使得我首先难以把握他的思路。有时,他似乎在说无论我们如何谈论法律与的道德的区分,这种区分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并将继续存在。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种区分,如果我们不想胡言乱语的话,就必须接受把这种区分当作现实来接受。而有时,他似乎在警告我们,这种相互区分的现实本身处于危险中,如果我们不修正我们思考问题和谈论问题的方式,我们就有可能丧失一种“珍贵的道德理想”,即忠实于法律这一理想。换句话说,在哈特教授思考中,法律与道德的区分仅仅是作为现实存在的 “是”,还是指一种“应当”,一种我们应当和他在一起帮助去创设和坚持的“应当”,这一点是不清楚的。
这些问题就是当我第一次接触到哈特教授的主张的时我所产生的困惑。但是,经过反思之后我敢肯定,任何将哈特教授批评为自相矛盾的做法将会是不公平的,同时也将一无所获。我们没有理由说,为什么主张法律与道德的严格分离不能够建立在双重的基础上:这种分离既是为了知识上的清晰,又是为了道德上的正直。如果要将这两种推理思路恰当地结合起来会遇到某些困难的话,那么这些困难也影响到了那些主张反对奥斯丁、格雷和霍姆斯的观点的人们的立场。对于我们这些发现“实证主义”的立场难以接受的人们来说,我们也将自己的主张建立在双重的基础上:这种分离在知识上的清晰是外表华美的,但是这种分离产生的效果是(或者可能是)有害无益的。一方面,我们主张奥斯丁的法律定义违背了它意图描述的现实(这只是举一个例子)。由于这个定义在事实上是虚假的,因此它不能有效地满足凯尔森所说的“认识的旨趣”。另一方面,我们主张在某些条件下,相同的法律观可能成为有害的,因为在人类的事务中,人们错误地作为真实接受了的东西正是由于他们的接受行为而趋向于变成真实的。
哈特教授的主张所具有一种坦率的美德,它首次为那些在法律与道德区分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人们提供了真正有益的交流渠道。到目前为止,在这个问题上的敌对阵营还没有真正进行过交流。一方面,我们遇到一系列定义性的命令。法律规则是,也就是说法律规则真的是、不过是并且总是,主权者的命令,法官定下的规则,对未来国家力量触及范围的预测,官员的行为模式等等。当我们问这些定义的服务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的答案是:“怎么还要有目的,除了准确地描述对应于‘法律’这个词的社会现实,这些定义没有任何目的。”当我们反问道:“但是在我看来,法律看上去并不是这个样子,”这时我们得到的回答是:“好啦,在我看来就是这个样子。”在此,争论就不得不停下来。
对于我们确信“实证主义”理论已经对法律哲学的目的产生了歪曲效应的人们来说,这种争论的状态一直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的不满不仅仅是源于我们遇到的窘境,而是由于这种窘境对于我们似乎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要克服这种窘境,我们需要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还要承认:法律实证主义对“法律实际上是什么”的定义不是对一些经验材料的简单反映,而是指出人类努力的方向。由于还没有人承认这一点,所以这种窘境和挫败还继续存在。其实,最大的挫败不过是遇到这样的理论,它主张自己的目的仅仅在于描述,这时,它不仅在直白地加以规定,而且这种规定产生的特殊力量刚好就是由于它不承认规定具有意图。在这种含糊不清的辩驳中,有时候确实透出了希望之光。就像在凯尔森偶尔承认的那样(显然他再没有重复这一点):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可能刚好是基于在感情上更偏向于秩序的理想而不是正义的理想。[1]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一般说来,这20年来一直在进行的争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什么有益的效果。
现在,由于哈特教授的论文,这场讨论开启了新的、富有希望的转折。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双方都承认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够最好地定义对法律忠诚这一理想,并服务于这一理想。法律作为值的人们效忠的某种东西,它一定表达了某种人类的成就;它不可能是权力的简单命令,或者是在国家官员的行为中才能辨识出来可以重复的行为模式。我们对人类法律的尊敬肯定会不同于我们对万有引力这一法则的尊敬。如果法律(即使是恶法)要求我们要予以尊敬,那么这种法律一定表达了某种人类努力的一般方向,这种方向是我们可以理解和描述的,并且是我们在原则上可以赞同的,即使在某些时候对我们来说似乎丧失了自己的特征。
如果说象我相信的那样,哈特教授的主张所显示出来的坦率美德主要就在于引发了忠实于法律这一问题的争论,那么哈特教授的主张的首要缺陷(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就在于,他没有能够感觉到并接受那些由于理论框架的扩大所必然带来的隐含意蕴。在我看来,这一缺陷或多或少地渗透在哈特教授的整个论文中,但是,它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拉德布鲁赫和纳粹政权的讨论中。[2]哈特教授并没有探究纳粹统治下依然保留下来的法律制度实际上运作情况,但是他认为一定有某种东西持续下来了,它依然值得称之为法律,当然这个法律是在使忠实于法律具有意义的这个含义上的法律。哈特教授并不相信纳粹的法律应当被遵守。相反他认为决定不服从这些法律不仅仅体现了审慎和勇气的问题,而是体现了一个真正的道德困境:必须牺牲对法律忠诚的理想以便支持更为基本的目标。如果不首先具体追问纳粹统治下的“法律”本身意味着什么,那么我认为就这样接受了哈特教授的这个判断是不明智的。
我将在后面指出为什么我认为哈特教授对纳粹统治下的情形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他对拉德布鲁赫教授的思想也具有一种重大的误解。但是,首先我要针对一些首要的定义问题,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哈特教授的论文立刻就会显示出关键性的缺陷。
一、法律的定义
在其整个论文中,哈特教授坚持的总体立场与边沁、奥斯丁、格林和霍姆斯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当然,他认为这些人对“法律是什么”的看法彼此相当不同,但是他显然认为这种差异与他要捍卫的整个学派的思想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说唯一的问题就是为“法律”这个词规定一个含义,以便可以追求知识的清晰,那么就有足够的理由把所有这些人放在一起来处理,认为他们在一个方向上努力。例如,奥斯丁将法律定义为最高立法权即主权的命令,而格雷认为法律就在于法官定下的规则。对于格林来说,成文法并不是法律,而仅仅是法律的渊源,它只有经过法官的解释和适用之后才成为法律。现在,如果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实现那种源于明确给出定义并严格坚持这种定义而导致的清晰,人们就可以貌似合理地主张,无论哪一种关于“法律”的概念都可以实现这一点。这两种法律的概念看起来都避免了道德与法律的混淆,并且这两位法学家都让读者明白他们打算赋予“法律”一词的意义。
但是,如果我们的兴趣在于对法律忠诚这个理想,事情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因为此时,在总体的政府架构中赋予司法什么样的地位就可能成为都等重要的大事。在我们国家今天所听到的关于宪法危机絮絮叨叨的争吵中,就可以证实上面的这种观察。在过去的一年里,报刊的读者不断地给编辑写信,严肃地并且显然是真诚地强烈要求我们应当废除最高法院,他们认为这是作为恢复法治的第一步。基于对奥斯丁或格林的深入研究不可能得出针对我们政府的病症提出的这种解救措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那些打算这么做的人来说,指望他们对奥斯丁和格林两人在法律定义中存在的分歧漠然置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从格林的著作中抽取出任何道德主张以应付目前关于最高法院角色的争论,都是对格林著作的曲解,那么,在我看来,我们同样有理由将他的著作在总体上看作是与对法律忠诚这个问题无关。
哈特教授所捍卫的作家们在另外一点上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是关于边沁和奥斯丁以及他们对主权权力所作的宪法限制。边沁认为宪法可以阻止最高的立法权发布某些类型的法律。但是,对于奥斯丁而言,对制定法律的最高权力做出任何法律上的限制都是荒唐的和不可能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宪法规定的修改宪法权决不能用来在没有征得任何州同意的情况下剥夺该州在参议院中平等的代表资格这一条款陷入危机之中,这两位作家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标准来指导良知呢?[3]显然,不仅在日常事务中我们需要有关对法律忠诚的义务的清晰,更主要是在特殊的紧急的多事之秋需要这种清晰。如果所有的实证主义学派在这个时候所提供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法律定义,它都是不同于道德的东西,那么,实证主义学派的教导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什么用处。
因此,我的看法是,哈特教授已经提出来的观点在实质上是不完整的,他要得到他所提出的目标,就不得不更加深入地考虑使忠实于法律具有意义的法律定义。
二、道德的定义
那些和哈特教授持同样观点的人们其特征在于,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保护法律概念的完整性。相应地,一般说来,他们曾经寻求法律的简明定义,但是并没有尽力去阐述他们意图通过定义加以排除的究竟是什么。他们就像那些为了保卫村庄而建造城墙的人,这些人必定知道他们所要保卫的是什么,但他们不必知道,事实上也不可能知道城墙所要抵挡的入侵力量究竟是什么。
当奥斯汀和格雷把法律与道德区分开来的时候,“道德”一词不加区别地代表了几乎一切人们能够想到的用以评判人们的行为而其本身又不是法律的规范。良知的内在声音、基于宗教信仰的是非观念、关于正派和公平竞赛的一般看法、特定文化条件下的成见,这一切都被归到“道德”的标题下,被排除于法律的范围之外。哈特教授在极大程度上因循了其前辈的传统。当他谈到道德的时候,看起来他似乎在其头脑中有各种各样的关于“应该是什么”这些法律之外的观念,不论它们的渊源、具体主张或固有价值如何。这一点在他论述解释问题时特别明显,他认为未经整理的应该是什么的观念只是影响法律的边缘,而没有触及法律确定不移的硬核。
在文章结尾的地方,哈特教授的主张发生了一个转变,这一转变似乎背离了其思想的主旨。这一点体现在他提醒我们存在一种不道德的道德,还存在许多很难说是合乎道德的“应该是什么”的标准。[4]他说,让我们假定,法官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边缘暗区适当地、而且是不可避免地进行立法,而且这种立法(由于缺乏任何其他规范)必定由法官自己的关于应该是什么的观念加以指导。而且,即使是在一个致力于最邪恶目标的社会,那里的法官会以在他看来最适合于有关情形的邪恶来补充法规的不足,这一点也是千真万确的。在文章结尾的地方,哈特教授说,让我们再假定,当法官通过重申某项原则而看来更为清晰地使阐明了这一原则最初追求的是什么的时候,此时在司法过程中就甚至存在某种看起来象是发现的东西。此外,他还提醒我们,在一个致力于精心安排罪恶达到极致的社会里,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发生的,在这个社会里,当一条邪恶规则被适用于其被制定出来时尚未予以有意识地考虑之情形时,该规则的隐含要求可能成为一个有待发现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对那些希望“往法律中注入道德”的人们的一种警告。哈特教授在提醒他们,要是他们的方案被采纳的话,那么实际上被注入法律的道德可能并不合他们的意。如果这是哈特的观点的话,那当然是正确的,尽管有人希望它能更明晰些,因为此观点差不多提出了哈特整个论点中最根本的问题。由于对该观点的阐述并非直截了当,而且我也许误解了它,所以,为了对之加以评论,我只能限于提出一些扼要的意见和问题。
首先,哈特教授似乎假定邪恶的目的可以与善良的目的拥有同等程度的连贯性和内在的逻辑性,而我则拒绝接受这个假定。我意识到,我现在是在引起,或者也许是在躲避那些可能导致伦理学认识论中最困难问题的争端。即便我有能力在那方面作些附带讨论,这里也不是适当的地方。我将不得不以对如下可能看起来有些幼稚的信念的坚持作为我论述的基点,这一信念即,(逻辑)连贯性与善良的关系比起(逻辑)连贯性与邪恶的关系更具亲和力。因为接受了这一信念,我也相信,当人们不得不为其决定作出解释和进行辩解时,不论我们所说的最大善良的标准是什么,其结果一般来说会将该决定引向善良。因为接受了这些信念,那么,认为可能有一天普通法将会通过“严格因循先例”而更加完美地实现了邪恶,在我看来,任何这种设想本身就是相当不协调的。
其次,如果说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因削弱法律和道德之分离而有可能纵容“不道德的道德”注入法律的严重危险的话,问题依然存在:什么是防御这种危险的最有效的手段?我本人认为在奥斯汀、格雷、霍姆斯和哈特等人所信奉的实证主义立场中不可能找到这种防御手段。因为这些作者对我来说似乎是把问题歪曲成了似是而非的简单化,却并未涉及真正的危险存于其中的困难问题。
第三,让我们设想一位致力于通过其判决实现某个会为大多数普通公民认定为错误或邪恶的目标的法官。这样一位法官有可能会通过公开援引某个“高级法”来悬置法规的字面含义吗?或者,他是否更有可能躲避在“法律就是法律”的格言后面,以看起来是法律自身要求的方式来解释他的判决?
第四,在我们各自的国家,哈特教授和我都不属于任何显著意义上的“少数群体”。这一点对于一个追求对法律与政府的哲学思考的人来说,既有利又不利。设想我们两人都被放逐到某个国家,在该国我俩的信仰十分令人厌恶而我俩也相应地认为该国占支配地位的道德是彻底的邪恶。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理由害怕法律有可能被暗地里操纵得对我们不利;我拿不准我俩中的任何一个是否会担心法律禁令可能因诉诸一项比法律高级的道德而被取消。如果我们感到该法律本身是我们最安全的避难所,难道那不是因为即使是最坏的政体,其对于把残酷行为、排斥异端的行为和不人道行为写入法律也是有所犹豫吗?而且,这种犹豫本身并非产生于法律和道德的分离,而确实是产生于法律与那些道德要求的一致性,那些道德要求最急迫、显而易见最无可非议,人们没有必要以坦陈这一点为耻,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
第五,我认为,在司法程序发挥作用的广阔领域,不道德的道德,或者至少是不受欢迎的道德之被注入法律的危险并没有提出真正的问题。在这里,危险恰恰是来自相反方面。例如,在商法领域,英国法院近几年来已经,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陷入了“法律就是法律”的形式主义,这种情形构成了一种针对已由曼斯菲尔德所成就的一切的反动。[5]当商事案件持续增加地被提交仲裁的时候,问题已经达到一种接近危机的状态。产生这种发展的首要原因在于仲裁员是愿意考虑商业需求和商业公平之一般标准的。我意识到哈特教授对“形式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我试图在稍后说明为什么我认为他的理论必然会导致形式主义倾向。[6]
第六,在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中,有一个问题在任何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讨论中都占支配地位,以致于全面影响了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述和传闻。我指的是由教皇关于天主教法官就离婚问题之职责的声明所引起的这类问题。[7]这一声明确实引起了严重的争端。但它并没有提出法律与那些已经通过体验和讨论而自发形成的对正确行为的一般看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更确切的说,这一争端是两种声明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声明都自称拥有权威性:要是你愿意的话,(可以说)这是一种法律在反对另一种法律。当我们把这种争端作为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整个问题的关键时,有关的讨论就改变了性质而且被歪曲了,以至于有益的交流成为不可能。在谈到关于“实证主义”的争论的最后一方面时,我无意于暗示哈特教授自己的论述被任何隐蔽的意图所支配:我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同时我相当有把握我已经准确地指出了那些读到哈特这篇文章的人思想中将会产生的最主要的争议点。
在对上述稍显不足的讨论的后续内容中,我不想使自己看起来采取了与哈特教授相反的方向来简化问题。由“不道德的道德”所引起的问题,值得作一个不论是较之哈特教授还是我在这些篇幅中所提供的更为细致的探究。
三、法律秩序的道德基础
哈特教授着重反对“法律的命令理论”,根据该理论,法律仅仅是一种足以使命令有效的暴力。他注意到,这种命令可以由一个手持上膛之枪的人发出,而“显而易见的是,法律当然不是枪手这种情形。”[8]这里没有必要细究命令理论的不足,因为哈特教授已经比我更清晰而简明地揭示了它的缺陷。他的结论是,法律制度的基础并不是强制力,而是某种“被认可的指明了立法之必要程序的基本规则”。[9]
当我接触到哈特文章中的这一论点时,我敢肯定哈特教授即将承认关于他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的限定条件。我有把握地预期他接下来会说如下的话:我始终坚持保持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明显区别的重要性。因此,现在可以提出关于这些为制定法律提供框架的基本规则的性质的问题。一方面,这些规则看起来似乎不是法律规则而是道德规则。它们的效力来源于一种普遍认可,这种认可最终是基于一种认为其正确和必要的观念。在权威公布的意义上,它们很难被说成是法律,因为它们的作用在于指出公布在何时才拥有权威。另一方面,在法律制度的日常运行中,它们被看作是普通法律规则,并经常像普通法律规则那样加以适用。那么,在这里,我们必须坦陈,存在一种可以被叫做法律与道德之“合并物”的东西,对它来说“交叉点”这个术语并非恰如其分。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哈特教授并没有经循以上思路,我发现他完全没有涉及那些使法律自身成为可能的基本规则的性质,而是把注意力转向了他所认为的批评实证主义这一方在思想上的混乱。我们且不去考虑哈特对于分析法学的讨论,他的论点如下:有两种观点与奥斯汀和边沁联系在一起。一个是法律的命令理论,另一个是坚持法律和道德的分离。对这两位作者持批评态度的人及时地认识到(用哈特教授的话说是“隐隐约约地认识到”)法律命令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经由一种思想上的松散联系,他们错误地假定,为了提出反驳命令理论的理由,他们也必须反对法律和道德必须得严格分开的观点。这是一个“自然的错误”,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个错误。
我认为,那些确信边沁和奥斯丁不适当地和过于简单地阐释法律和道德关系问题所犯下的错误是导致法律命令理论这一更大错误的一部分的人们没犯什么错误。我认为,如果我们自问假如奥斯汀抛弃了命令理论,那么会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发生什么的话,这两个错误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更加清晰。
读奥斯汀的法理学讲座五和讲座六[10]的人禁不住会对他缠住命令理论不放的固执作风留下深刻印象,尽管他自己的敏锐见解每次都在把他拉向抛弃该理论的方向。在君主主权的情形中,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可是我们将对确定谁是“合法”君主的王位继承“法”发表什么样的意见呢?一个命令的本质在于他应该由一个上级对一个下级发出,然而在“多人主权”的情形中,比如说,一个议会,主权者似乎是在向自己发出命令,因为一个议员可能被他自己起草和投票通过的法律判定为有罪。主权者的法律权力必须是不受限制的,因为有谁能够裁定一个最高立法权的界限呢?然而“多人主权”在它能够制定法律之前必须接受规则的限制。这样一个机关只有在“法人资格”限定范围内行事才能获得发布命令的权力;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依照“为制定法律而规定和认可的方式与标准”来进行。法官行使由最高立法机关授予他们的权力,被委托执行“直接或迂回的命令”。然而,在联邦系统,联邦与其成员之间权限的冲突是必须由法院来解决的。
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奥斯汀以不同程度地发现了,他极力挣扎。他一次次地在抛弃命令理论的边缘摇晃,似乎有点支持哈特教授的观点:在“被人们接受的指明制定法律之必要程序的基本规则”之中辨别出了法律秩序的基础。然而奥斯汀没有采取断然行动。他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一定明白这样做的后果将会是丧失法律与道德之间黑白分明的区别,而此种区别是其《讲座》的全部目的——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其致力于学术生涯的持久目的。因为,如果是“被人们接受的基本规则”使法律成为可能——对于奥斯汀来说此规则必定不是法律规则,而是实证道德规则——我们将对立法机构颁布的用于调整自己立法行为的规则发表什么样的意见呢?我们有选举法,向特定地理区域分配立法代表的法律,有关议会程序的规则,关于投票人资格限制的规则,以及其他许多性质相近的法律和规则。这些法律和规则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塑造立法过程。然而,我们如何把那些其有效性归因于被接受的基本规则和那些即使被人们普遍认为是邪恶的或者愚蠢的也依然有效的规则,严格说来是法律的规则区别开来呢?换句话说,对于哈特教授自己关于“某些被接受的指明制定法律之必要程序的基本规则”的阐述中的“基本”和“必要”,我们如何界定?
凯尔森理论中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有教益的。事实上,凯尔森对于奥斯汀犹豫太久的问题采取了断然措施。凯尔森意识到在我们能够区分什么是法律与什么不是法律之前,必须得接受一些法律由以产生的基本程序。在任何法律体系中,必须存在某个明确指向法律必须由以产生之源头的基本规则。该规则凯尔森称之为“基本规范。”他是这样说的:
基本规范的有效性不是因为它是以某种方式创制的,而是因其内容被假定为有效。那么,其有效性之情形类似于某种自然法的规范……纯粹实定法的思想,就象自然法的思想一样,有其局限性。[11]
值得注意的是,与哈特教授说的是调整制定法律之行为的“基本规则”不同,凯尔森仅提到某种独一无二的规则或者规范。当然,在任何现代社会象这种独一无二的规则都是不存在的。基本规范的概念被公认为是一种象征,而非事实。它是一种象征,体现了实证主义意图清晰而明确地检验法律之要求,还体现了在那些其有效性归因于渊源的规则和那些其有效性归因于接受和内在要求的规则之间划出一条清晰而明显的界限之要求。奥斯汀通过坚守命令理论而回避了这些困难;凯尔森通过虚构了一个将现实简化成能够为实证主义所吸收的形式而回避了这些困难。
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法律只有凭籍非法律规则的效能才使自己成为可能,那么,对由此产生的所有问题的充分考察将要求我们把成文宪法存在与否的影响引入考虑范围。这样一部宪法在某些方面简化了我正在讨论的问题,在某些方面又使其变得复杂。就成文宪法规定基本的立法程序而言,它也许能消除一个议会实际上在为自身作出规定的情况所产生的困惑。与此同时,在成文宪法下运作的立法机关可以制定对立法程序及其可预见的结果产生深远影响的法律。如果这些法律起草得足够圆滑,它们将符合宪法框架,但却暗中破坏宪法所意图建立的制度。如果说三十年代的“收买法院”建议没有明确阐明这一危险的话,它至少暗示我们这种恐惧并非凭空想象的产物。成文宪法并不能自行贯彻。为使其发生效力,不仅要求我们就象对普通法规那样对其表现出尊敬的服从,而且要求我们就象对道德原则那样,不仅为我们所积极信奉,而且努力实现意愿的一致。一个人可以作出适当的努力去修正一部宪法,但只要该宪法尚未被修正,此人就必须在其范围内活动,而不得违背或者绕过它。这相当于是在说,一部成文宪法要想有效力,必须是被认可为,至少是被暂定为不仅仅是法,而且是好法。
以上这些考虑与对法律忠诚的理想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关系甚大,(因为)它们揭示出实证主义观点对于有效地服务于该理想而言本质上的无能。因为我认为实现这一理想是我们必须筹划的事,而这一点恰恰是实证主义者所拒绝去做的。
让我说明一下我所说的实现忠实于法律这一理想意味着什么。设想我们正在为某个刚从暴力与骚乱中兴起的国家起草一部宪法,在该国,任何与先前政府的法律连续性都被已打破。显然,这样一部宪法不可能独力提升自己使自己具有合法性;不能仅仅因为它说自己是法律它就能成为法律。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所起草的这部宪法之有效性取决于普遍接受,为了使这种接受牢固可靠,必须存在一种普遍信念:认为该宪法本身必要、正确和有益。因此,该宪法的条款应该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目的上保持简明和可理解。序言和其他关于所要追求的目标的说明,在某部普通法律中会是令人不快的,而在我们的宪法中将会有一个适当的地位。我们应该把该宪法看作是在为今后制定和施行法律的政府行为规定一个基本的程序性框架。对于政府权力的实质性限制应该被控制在最小程度,一般来说,这种限制应该限于其必要性可被普遍认可的那些限制。实体目标应该尽可能地依据程序来实现,按照这样的原则来进行,即如果人们被强迫以正确方式行为,则一般来说他们会做正确之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产生的那些宪法似乎已经大大地忽略了以上被考虑的情形。这些宪法中混合了大量的经济和政治措施,让人不难想起规定这些措施的制定法。这种情形并不罕见。这些措施之所以被写入宪法,不大可能是因为它们代表了被普遍认同的目标。有人怀疑原因恰恰相反,即是因为害怕这些措施无法幸免于议会权力日常运作的变动。因而,作为立法行为正常伴随物的意见的分歧就写入了使法律自身成为可能的宪法文件之中。这一步骤显然含有了对于今后实现对法律忠诚这一理想来说可谓严重的危险。
我冒昧地提出对于宪法之制定的上述议论,并非因为我认为这些议论能够(过)宣称达到了特别深刻的程度,而是因为我希望通过为实现对法律忠诚这一理想设计所必需之条件来说明我的用意。即使在我这一低调的目的限度内,我说过的话也可能显然是错误的。要是这样的话,就不该由我来说,我是否也错得清楚明白。不过,我敢断言,如果我错了,我错得有意义。我对法律实证主义学派感到困扰的是,该学派不仅仅拒绝涉及我刚才已经讨论过的问题,而且从原则上将其排斥于法律哲学的范围之外。该学派关心的是为人们的所作所为贴上正确的标签,而似乎没有兴趣来追问这些人正在做的是不是正确的事情。
四、法律自身的道德性
哈特教授在其文章中论及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复述为秩序与良好秩序的区别。法律可以说代表普遍秩序,而良好的秩序是指这样的法律,它必须回应正义、道德或者人们认为应当是什么的要求。正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无庸质疑地同意,要明确区分秩序与良好秩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这一命题的重新阐述有助于看清哈特教授研究所具有的勃勃雄心。举例来说,当我们说法律仅仅表现为所有政体下的——包括民主的、法西斯的、共产主义的——公共秩序时,这种秩序当然不是指陈尸房或墓地的秩序。我们所指的秩序必须是正在有效运行的秩序,它至少必须非常好,以致于不管以这样还是那样的标准来衡量都能认为它是有效运行的秩序。一个有效运行的秩序往往也需要一些连接处的缝隙,并因此不会达到绝对完善。这样一个提醒足以表明,任何试图明确区分秩序与良好秩序的努力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复杂的问题。
然而暂且让我们假设我们能清晰的区分秩序与良好秩序的概念。即使在这种不真实的、抽象的形式下,秩序本身的含义仍包含着可能被称为道德因素的东西。下面我举例说明处于最原始、最基本状态下的“秩序的道德性”。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绝对的君主,他的话是他的臣民所知的唯一的法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假设他极端自私,在他与臣民之间的一切关系中都只是为了寻求他自己的利益。这个君主不断地颁布命令,承诺要奖赏顺从者,威胁要惩罚悖逆者。然而,他又是个荒淫无道而且健忘的家伙,他从未曾尝试去弄清实际上是谁在遵循他的命令,又是谁在反对他,结果他经常惩罚忠诚的人,而奖励悖逆的人。除非这个君主愿意接受一个最能在他的言行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系的最低程度的自我约束,否则他永远不会达成他自私的目标。
现在我们假设我们的君主洗心革面了,当今天他有机会来颁发奖赏或命令砍人脑袋时,他开始顾及自己昨天所说的话。然而在这一新的责任的约束下,我们的君主却在另一方面放松了自己,他对自己发布的命令的措辞变得令人绝望的漫不经心,它的命令非常含糊并且用难以听闻的喃喃自语来发布,以至于他的臣民从来不知道他到底要他们做些什么。很明显地,如果我们的君主想为了他自私的利益着想,而在他的国度内创建一个类似于法律体系的东西,他就必须振作起来承担起另一个责任。
法律即使仅仅被看作是秩序,也包含它自身的隐含的道德性,如果我们要创建一种被称为法律的东西,即便是恶法,这种秩序的道德性也必须得到尊重。法律自身无力创造这种道德性。除非我们的君主真的准备好去面对他的地位所带来的责任,否则再颁布一个不足取的命令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而这一次如果他不修正他的方法的话,就会自食恶果并面临惩罚的威胁。
在两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正确地说法律不能基于法律而建立。第一,制定法律的权威必须得到道德态度的支持,正是这种道德态度给法律赋予它所宣称的能力。在这里我们正在讨论一个能使法律成为可能的外在于法律的道德性,但只此一点是不够的。我们可以规定在我们的王国中,被人们接受的“基本规范”指的是君主自身成为唯一可能的法律渊源。只有我们的君主准备好接受法律自身内在的道德性时,我们才能说法律存在了。
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法律的外在道德与内在道德彼此相互影响,一方面的恶化几乎不可避免会使另一方面也恶化。它们之间的联系极为紧密,人类学家劳伊指出:“被普遍接受的伦理命题是法律体制的最终支撑,也是他们顺利运行的保证”,[12]此时,我们可以说他心目所想的既有外在的道德也有内在的道德。
我所说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性”似乎被哈特教授完全忽略了。哈特简单地提到“管理法律的正义”,这个正义由同等情况同样对待组成,而不管对“同等”的定义采用的是多么高尚还是多么堕落的标准。但是他很快便放弃了法律的这方面的特征,因为他认为这与他所致力于创立的理论没有任何特殊联系。
从这一点来讲,我认为哈特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正是由于他忽略了要对秩序的道德性要求进行分析,导致了他在通篇文章中都将法律看作是自动投射到人类经验中的事实资料,而不是人类抗争的对象。当我们认识到秩序需要我们努力才能达成时,很明显,法律体系的存在——即便是坏的或邪恶的——永远都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简单的日常经验的事实时,仅凭一个简单的断言“纳粹的法律仍是法律,尽管是坏法”就想解决掉纳粹暴政所带来的问题是不可能的。相反,我们不得不追问:在纳粹统治下发生的整体上被贬抑和滥用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秩序中,究竟会有多少法律制度得以幸存,以及对于那些在其中被迫苟活的有良知的国民来说,这样一个遭到毁损的法律制度到底包含着什么样的道德意涵。
然而,没有必要通过详细论述纳粹政权这一样的道德激变,来发现实证主义哲学自称的服务于一个高尚的道德理想(即对法律的忠实)根本不可能实现。我相信,不管是那些迫切想满足法律秩序道德要求的人,还是那些在值得忠诚的秩序中负有职责的人,在他们所面对的日常问题中,实证主义哲学明显地表现出来无能实现在自己的理想。
让我们来假设一名初审法官的情形,这名法官具备处理商业事务方面丰富的经验,并且在他之前裁判过许多商业争议。作为一名司法等级制度中的下属,我们的法官理所当然负有服从它的最高法院颁布的法律的义务,然而我们这位想象中的法官很不幸,他处于一个令他悲哀的认为漠视商业习惯和需求的最高法院之下。在他看来,这个法院所做的很多商业领域的决定都是毫无道理的。如果这个有良知的法官在这个两难境地中转而求助于实证主义哲学,那么它能期待什么样的援助?提醒他有责任忠实于法律显然毫无用处,因为正是这种责任使他陷入尴尬境地,他已认识到这一点并因此而痛苦不已。而对他说如果他自己立法也肯定会“出现漏洞”,或者说他的贡献只能是“局限在从克分子运动到分子运动”,这同样也毫无帮助。这种说话的方式与这些人意气相投,他们喜欢将法律看成是对于国家权力的管辖范围以及方向的描述,而本身不具有任何目的性。但我不能相信这一建议背后的实质上极端老套的观点能够通过文采斐然的雄辩得以提升,以至于对我们的法官有一些真正的帮助,举一个例子而言,他不可能知道最高法院认为他的特定贡献是太宽了还是太窄了。
同样对核心与边缘暗区的区分于法官来讲也是毫无助益的。我们的法官的尴尬境地往往并不是特定的先例造成的,而是来自扩展到许多判决并不同程度渗透进这些判决的的关于商业性质的错误概念。就这些产生于特殊词语运用的问题而言,他很可能会发现最高法院经常使用实际的商业交易中感到陌生的日常商业术语。如果他像一名商业经理或会计那样来解释这些词语的话,会导致所援引的先例在逻辑上的混乱。另一方面,他发现很难辩明最高法院所用词语的确切含义,因为在他头脑中,这些含义本身就是混乱的产物。
实证主义者们极力坚持要严格区分法律是什么以及法律应当是什么,正是这种坚持致使实证主义哲学无助于法官,这一点还不清楚吗?除非我们的法官将忠于法律的义务与制定应当是什么的法律的责任前后协调起来,否则他永远不可能找到一个解决其两难境地的满意方法,这一点难道也还不明白吗?
我所假设的例子很可能太极端了,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却遍及整个法律体系中。如果法官与最高法院的观点的分歧不那么强烈的话,要鲜明生动的表现其尴尬境地会更加困难,而其主张的复杂性实际上会增强。这种复杂性是执行任何司法功能的常伴物,并可能在行政法的领域达到极致。
你可以假设一种情形——当然不象发生在哈特的国家或是我的国家里——在那里一名法官有着深厚的道德信仰,并恰恰与最高法院同样深信不疑的道德信仰相反。他也很可能认为他所必须遵从的先例是一种他认为是邪恶的道德的直接产物。如果这样一名法官在其职位上不能为他的两难境地找到解决之道的话,他很可能别无选择地被迫刻板的从文字上引用先例,因为它不能理解给这些先例赋予生命的哲学。但是一个法官在这样的情形中,是否需要法律实证主义的帮助以便找到逃离其困境的令人忧心忡忡的出路,我深表怀疑。而且我也不认为这样的困境会出现在这样一些国家,在这里,法律与好的法律被认为是需要不断更新的相互合作的人类的成就,在这里,法律家至少仍然对“什么是良法?”与“什么是法律”抱有同样的兴趣。
五、在不尊重法与正义的政权覆灭后,对法与正义的尊重的恢复问题
纳粹政权倒台后,德国法院面临一个真正可怕的困境。对他们来说,宣布整个独裁体制非法,或把希特勒政府所制定的每个决定和法律规定一律视为无效,都是不可能的。对12年间发生的所有事,任何一种方式的全盘否定都会带来难以容忍的骚乱。另一方面,把纳粹政权以法律的名义做出的邪恶所造成的影响继续带入到新政府中去,同样不可能,如果这样的话,将会使纳粹毒害对无限的未来造成不良影响。
这实际上是一个影响到法律所有部门的普遍存在的困境。这一困境在一系列的告密者案件中变得极为突出,那些告密者利用纳粹恐怖去铲除私敌或不喜欢的配偶。如果所有的纳粹统治下的法规及司法判决都不加区分地被认为是“法”的话,那么,这些卑鄙的小人们就无罪,因为他们只是把他们的受害人交给只有纳粹自己知晓的名之为法律的程序。告密者平安无事,因他们的恶意而受害的人或死亡,或囚禁数年后被释放,或更惨痛的是仍无人问津,所有这些都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尤其是对于受害者幸存的亲戚和朋友。
这一事态的紧迫性,哈特教授不会不考虑。实际上他极力赞许一个权宜之计,而这一权宜之计本身不能不包含悲观失望的成分。他认为,应制定一个具有溯及力的刑法,这是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并遭遇最少的反对的方法。这一法规将因其告密行为惩罚告密者,并判他有罪,同时哈特教授认为该行为在当初做时是完全合法的。[13]
另一方面哈特教授无条件地谴责法院这样的司法判决:法院自己宣布那些告密者进行告密所依据的纳粹法律无效。在这一点上,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提出一个问题,即哈特教授所提出的问题是否真的有益于对法的忠诚。无疑,用一个具溯及力的刑事法规来对抗告密者,必然意味着适用于告密者及其受害人的纳粹法律,就那些法规而言将会被视为无效。伴随这一转变,存在的问题看起来将不再是是否宣布一度是法律的东西已不再是法律,而是由谁来承担这一肮脏的工作,是法院还是立法机关。
但是,正如哈特教授所说,这些攸关胜败的问题意义如此重大,绝不能因语义混乱而冒把握不住这些问题的危险。即便整个问题是词语问题,我们还是应提醒自己注意,我们处在一个词语对人们的态度具有有力影响的领域。因此,我想为德国法院申辩,并据我的看法提出一些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判决没有抛弃哈特教授认为他们抛弃了的法律原则。为了了解这些判决的背景,我们应更近历史,就象要闻到女巫的大锅里东西的味道一样,而不是被哈特教授带得更远。我们还必须考虑在他的文章中被忽视的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对我所称的法律本身的内在道德,纳粹法律究竟遵行到何种程度。
在整个讨论中,哈特似乎假设,在纳粹法与英国法(比方说)之间唯一的不同是纳粹利用法律去实现许多在英国人看来是邪恶的目的。我认为这一假设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我看来,哈特教授接受这一假设使他的讨论不能成为对其所要阐述的问题的回答。
在整个的纳粹统治期间,纳粹频繁运用了一种对美国立法者来说并非一无所知的手段,即制定具有溯及力的法律来矫治过去法律上的无规律性(irregularities)。这种具有溯及力的法律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运用是发生在1934年7月3日的“ROEHM清洗”后。这一党内火并事件结束时,七十多个纳粹成员被“谋杀”(人们不免要这样说)。这时,希特勒返回柏林,并从其内阁中弄出一个法律,来认可并加强在1934年6月30日至7月1日所采取的手段,却没有提到这些现在被认为是已被依法处死的人们的名字。[14]过了一段时间,希特勒宣布,在ROEHM清洗期间,“德国人民最高法院……由我自己组成”,如果一个人认真考查这一具有溯及既力并赋予“已采取的措施”以合法性的法律,一定会明白这种说法并不是对他采取这种举动的能力进行夸张。[15]
现在,在英国与美国,当然有一些宪法性限制条款可能禁止某些种类的溯及力,尽管如此任何人都不会说“依照法律的性质,法律不能具有溯及力”。我们会说,在正常情况下法律操作应具有可预测性,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不具有可预测性的说法是有争议的,但是任何主张溯及性违反了法律本身的性质将被视为故弄玄虚,无法服人。为了看到溯及力提出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的这一真实的问题,我们仍然只能去假设一个国家,在那里所有的法律都具有溯及力。如果我假设一个绝对的专制君主,他让他的王国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仅凭制定一个补救性(curative)法规来赋予截至目前已发生的所有事情以合法性,并宣布有意在未来每六个月都实施同样的法规,我们很难说他能建立法律制度。
用法规来改变过去法律的无规律性,这一趋势的普遍增长反映了该规则中法律道德性的堕落,而没有了法律道德性,法律本身就不可能存在。这些法规造成的威胁笼罩着整个法律体系,使所有法规的重要性有所削弱。并且肯定地,当一个政府要把发生时视为谋杀的行为通过这种法规而转变为合法处死时,必然隐含着这种普遍威胁。
纳粹统治期间,关于“秘密法”的谣言不断。在拉德布鲁赫的文章中(该文受到哈特教授的批评),他提到了一个报告,即关于通过秘密法使集中营中集体屠杀合法化的报告。[16]现在,肯定再没有别的法律比秘密法更能体现法律上的畸形变态了。是不是任何人都会郑重地赞同下列做法,即战后德国法院应在希特勒政府已留下的文件档案中寻找未公布的法律,并根据这些法律来决定公民权?
立法者有义务将其立法公之于众,这一义务的程度当然是一个法律道德性的问题。这一问题至少从 the Secession of the Plebs 以来就处于热烈争论之中。可能没有一个现代国家不被这一问题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所困扰。在现代社会,最有可能产生这一问题是涉及有关未公布的行政指令。发布这些指令的人常常相当诚挚地认为,这些指令仅影响组织内部事务。但由于这些程序由行政机构执行,即使在其内部行为中,也可以严重地影响公民的权利与利益,因此这些未公布的或“秘密”的规章,经常成为人们控诉的对象。
但是,大多数社会中靠隐含的法律要得体适应(legal decency)的限制对法律溯及既往的控制,在希特勒政府则以令人震惊的形式遭到了破坏。实际上,整个纳粹法律所含的道德性是如此稀少,以至于难以弄清到底那些法律应被视为未公开的或是秘密的。因为对执法人发布的是未公开发布的指示,且通过强加一个蛮横无理的解释,这些指示就会破坏任何公布的法律。因此,说每一个法律的含义都是“秘密的”是有道理的。即使希特勒发布一个把集中营中的一千人都处死的口头命令,也立刻成为一个行政指令,根据该命令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并具有有效性,因为其是“合法的”。
然而,希特勒政府对法律道德的最严重的公然冒犯,并未采取象我刚所讨论过的在那种极端怪异事例中所采取的一些微妙形式。首先,当法律体制变得碍手碍脚时,纳粹经常可能做的是完全避开这些法律,并“通过党徒走上街头来实现”。无论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都没有人敢让他们为此做出解释。第二,只要有利于他们行动的方便或者如果法院害怕法学家式的解释可能引起“上司”的不高兴时,纳粹控制下的法院经常无视任何法律,即使这些法律是由纳粹自己制定的。
纳粹完全无视即使是自己制定的法律,是导致拉德布鲁赫持有其文章中的观点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观点受到了哈特教授的严厉批评)。我认为,象哈特教授那样,完全不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要想对战后德国法院的行为做出公平的评价是不可能的。
以上这些评论看起来似乎不具有一般性,并且更着依赖于主张而不是可证明的事实。下面,让我们立刻转向哈特教授所讨论的一个真实案例。[17]
1944年,一个德国士兵在奉命出差执行任务期间,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探亲,就在他呆在家的那一天,他私下里向他妻子说了一些他对希特勒政府的看法,表达了他对希特勒及纳粹党其他领导人物的不满。他还说,在当年7月20日的谋杀希特勒企图中,希特勒没有丧命太可惜了。他刚刚离开,他的妻子(因他长期离家服兵役“已投向另一个男子的怀抱”,并想把他除掉),就把他的言论报告给了当地的纳粹党头目,并说:“说那样的话的人本不应活着。”结果,他丈夫遭到了军事特别法庭的审讯,被判处死刑。经过短时期的囚禁后,未被处死,又被送到了前线。纳粹政权倒台后,那个妻子因设法使其丈夫遭到囚禁而被送上法庭。她的抗辩理由是:据当时有效的法律,她丈夫对她所说的关于希特勒及纳粹党的言语已构成犯罪。因此,当她告发她丈夫时,她仅仅是使一个罪犯归案受审。
这一抗辩基于两个法律,一个是1934年通过的,另一个是1938通过的。让我们先考虑第二个法律,它是更全面地创设一整套战时特殊犯罪的法律之一。我仅转述相关部分,并翻译如下:
下列人因为破坏国家抵抗力量而构成犯罪并应当被处死:公开地设法拉拢或煽动他人拒绝在德国军队及其联盟军中服兵役的;公开寻求伤害或动摇德国人民及盟国人民坚决抗敌之意志的。[18]
现在,几乎难以相象,今天德国某个法院会持以下看法,即那个丈夫对他妻子——她因性别而免除兵役——的言论违反了这一法规的最后的总括性条款,尤其是想到上面所引的条文是一个全面处理有心潜逃、自残以逃避兵役及类似行为的法律。随之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在决定该丈夫的言论是否真的违法时,希特勒政府所适用的解释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应被接受。
当我们注意到这个法律仅适用于公开的言行时,这一问题就变得尖锐起来,因为该丈夫的言论是在他家里私下说的。现在看来,显然纳粹法院(应注意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军事特别法庭)相当普遍地无视这一限制,并延伸到所有的言论,不管是私下的,还是公开的。[19]哈特教授还会说,这一法规的法律含义将根据其明显的统一的司法解释原则来决定吗?
现在让我们再看另一个法规(哈特教授据此法律认为该丈夫的言论属非法行为),即1934的一个法规,相关部分翻译如下:
(1)发表任何公开恶意的或煽动性的言论反对国家及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领导人物,或发表的言论透露了有关他们采取的措施、建立的体制的基本部署,以及其他性质上削弱人民对其政治领袖人物的信任的行为,该行为人都应判处囚禁刑。
(2)虽未公开发表恶意言论,但当他意识到或应意识到这些言论会传到公众耳朵里时,以公开言论论处。
(3)只有根据国家司法部长的命令才能追究这些言论。如果该言论反对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领导人物,司法部长只有经领袖代表人的建议和同意,才能追究。
(4)在领袖代表人的建议和同意下,国家司法部长确定那些人为上述第一款所规定的领导人。
这一法律掺杂了许多不受控制的行政自由裁决从而被破坏的如此厉害,立法的残酷简直无以复加。我们需要注意的只是以下两方面:第一,根据此法,无论如何判处那个丈夫死刑(虽未执行)是毫无道理的;第二,如果他妻子告发他的行为使他的言论成为“公开”的话,那么根据此法就不会存在任何私下的言论。针对战后重建的复杂性,德国法院认为,宣布这些事物不是法很合适,对于这件事,我想问,读者是否真的和哈特教授一样感到愤怒?是否能够严肃地主张:如果战后法院研究希特勒统治时期的“解释原则”,然后郑重地运用这些“原则”来确定这一法规的含义,那么这一程序将看上去更像司法程序?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法院运用他们自己的相当不同的解释标准来解释纳粹法规,他们会真的尊重纳粹法律?
哈特教授严厉批评德国法院和拉德布鲁赫,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必须被实施,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种道德上的两难困境(这种困境在边沁和奥斯丁看来将是相当明显的事)。通过一个简单的脱身妙计,即说“当一个法律如此邪恶时,它就不再是一个法律”,他们逃避了他们应当面对的问题。
我认为,这一批评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就法院而言,他们不说“这不是法”(就象他们过去所说的那样),而说“这是法,但它如此邪恶,我们拒绝适用它”,必定于事无补。无疑,当法院拒绝适用它认为是法的东西时,就是道德混乱达到高峰的时候。并且哈特教授不赞成让法院本身面对这一“真实的问题”。他宁愿选择一个具有溯及力的法规。有趣的是,这也是拉氏的选择。[20]但是与哈特不同的是,德国法院和拉氏是这一严重紧迫局势的现在活着的参加者。其中告密者问题就是这些紧迫问题中的一个,同时如果德国要恢复正常的法律制度,它将再也不会让这样一个历史重演,即将法律掌握在群众自己手中,而让法院等待一个法规。
至于拉氏,说他没有意识到他所面临的是一个道德上的两难困境,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公正的。其战后的著作一再强调,德国努力重建一个合理的、有序的政府时面临的矛盾困境。至于忠实于法律的理想,还是让拉氏自己的话来表达他的观点:
我们不能欺骗自己,以致看不到下列事实——尤其是我们在十二年专政期间的经历——在“法定的无法”和拒绝接受正确制定法规是法的一个特征的观念中,包含着对法治多么恐怖的危险。
事实上并不是法律实证主义使一个人意识到他面临着两难境地的问题,而拉氏自欺欺人,相信他不会碰到任何问题。造成哈特与拉氏不同的真正原因是:我们应如何来陈述这一问题?我们所陷入的两难困境的性质是什么?
我希望,当我还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陈述哈特所看到的两难困境,而只好用下列词句来表达时,不会造成对哈特教授的不公。一方面,我们有一个被称为法的、与道德无关的数据,它有一个特点,能够产生让人服从它的道德义务;另一方面,我们有做我们认为是正确和恰当的事的道德义务。当我们面对一个我们认为是彻头彻尾的、邪恶的法律时,我们必须在这两个义务之间做出选择。
如果这就是实证主义者的立场,我会毫不犹豫的反对它。该观点所阐述的“两难困境”,在文字上确切地表达了一个问题,但这一问题毫无意义。就象说,在给一个饿汉食物与being mimsy with the borogoves* 之间必须做出抉择。对于忠实于法律的道德义务,实证主义哲学从来没有给出任何清楚的含义,我并不认为这么说是不公平的。这一义务似乎被认为是独特的(sui generis),完全与许多普遍的、超法律的人类生活目的不相干。实证主义的基本假设——法必须与道德截然分开——似乎要否定任何沟通守法义务和其他道德义务的可能性。不存在能够衡量他们各自对良心的要求协调规则,因为他们存在于完全分立的世界。
尽管我不会同意拉氏所有战后的观点(尤其是关于“高级法”方面的),我认为,与哈特相比,他更清楚地看到了在寻求重建被粉碎的法律体制时德国所面临的“两难困境”的真实性质,即德国人必须恢复对法和正义的尊重。虽然二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但如果要试图将二者同时恢复,会遇到许多矛盾困境。这一点,拉氏看得非常清楚。在本质上,拉氏认为这个“两难困境”是两方面要求的交合,即对秩序的要求与对良好秩序的要求。当然,从对这一问题陈述中找不出简单明了的方式。但是,并非象法律实证主义所声称的那样,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个相对的要求之间没有任何活生生的联系,就象在真空中抗辨一样互不影响。当我们试图建立秩序时,我们有意识地提醒自己注意,秩序本身不会对我们有帮助,除非于事有益。当我们试图建立良好秩序时,我们要提醒自己注意,没有秩序,正义本身也难以实现,在追求好秩序的同时不要失去秩序本身。
六、法律实证主义的道德含义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相信,纳粹德国对实证主义哲学的普遍接受使通向专政的道路更加平坦,我们现在要谈论的问题是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哈特教授将这种信念看作是所有对实证主义的指责中最让人不能容忍的,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里我们确实在开始进入一个危险的争论领域,恶言恶语充斥其中。德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没有哪一个法律哲学问题比断言在奥列弗·温得尔·霍姆斯法官的观点中有“极权主义”含义更能使人大费笔墨与激动不安了。从达尔文、赫胥黎和海克尔(Haeckel)时代起,对霍姆斯法官这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即使使用措辞最为谨慎的批评,似乎都会让读者回想起过去的那些尖酸刻薄的评论。[21]认为霍姆斯可能并没察觉其哲学的所有意涵的想法没多大用处,因为这只是用一种侮辱代替了另一种侮辱。回想起霍姆斯年轻最亲密的伙伴(肯定是一个感觉敏锐的观察者)的说法也没有多少帮助,这个说法就是:霍姆斯“至少是将两个不同的人各劈一半而压缩成的一个人,他们在一张紧绷的皮肤下组合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争吵,霍姆斯将这种不同组合起来的方式无疑是非凡卓越的”[22]
在法理学汹涌澎湃的波涛里冒险前行,到此为止还没有看到那个人像哈特教授那样从容不迫,一心沉浸在划动帆船。在他看来,拉德布鲁赫在评价德国法律职业的脾性,并假定德国法律职业追随实证主义帮助了纳粹掌权时,暴露出了自己的“极端幼稚”。[23]他认为拉德布鲁赫对这件事以及其他事情的判断说明对“自由主义的精髓一知半解”,而自己还错误地认为他正在向德国人传达自由主义。[24]人们从诸如告密者案件的司法裁决中看到了德国法律思想有益的新方向,而哈特认为这些人揭示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25]
让我们至少把那些没什么用处的骂人工具放到一边,尽可能冷静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像在德国被实践与鼓吹的那样,法律实证主义与希特勒取得政权是否具有或者可能具有因果关系。这里应该回想一下,纳粹统治前的75年里,实证主义哲学已在德国取得了在别的国家未享有的地位,奥斯丁曾称赞一个德国学者将国际法引入以明晰著称的实证主义的范围中。[26]格雷欣喜地指出,他那个时代“才能卓著”的德国法官正“公开放弃所有非实证主义的法”,并且引用勃格鲍姆(Bergbohm)作为例证。[27]这是一个启发人的例子,因为勃格鲍姆是一个雄心壮志要使德国实证主义实现其抱负的学者。在自称是实证主义的作品中,他因为遇到了自然法思想的残迹而感到沮丧。尤其是,他一直困扰于一些频繁再现的想法,如法律的效力归于可以感觉到的对秩序的道德需要,或者需求法律秩序正是人类的本性之类的想法。勃格鲍姆宣布了一个计划(却从未实现),计划将自然法沼泽里最后散发出的瘴气从实证主义的思想那里驱走。[28]德国法学家们一般倾向于把英美的普通法看作是一个凌乱而无原则的法律和道德的混合物。实证主义是唯一在科学时代能被称为“科学”的法律理论。[29]对此观点持异议者被实证主义者冠之以现代人最害怕的称号“幼稚”来表示他们的特征。其结果是1927年就会有报道说“发现犯有追随自然法理论的罪过是一种社会耻辱”。[30]
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添上一个注意事项:德国人看起来从未取得英国人(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人)曾拥有的非同寻常的能力,那就是在条件局限的情况下坚持他们的逻辑。当一个德国人对法律下定义时,他想使他作的定义得到认真对待。如果一个德国作者想到了美国法律实证主义的口号:“法律只不过是法官和其他政府官员的行为模式”,他是不会把此口号看作一个有趣而微不足道的对话开场白的。他已经相信了法律并依其行事。
德国法律实证主义不仅仅禁止法律科学对法律的道德目标作任何考虑,而且它对我前面讲到的法律自身的内在道德也漠不关心。因此德国法律家特别愿意把冠以“法律”之称的任何东西接受为法律。这些东西是政府出钱印刷的,而且看起来是“从上面下来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盛行于德国法律职业中的观点是有利于纳粹分子的。根据以上思考,我既不认为这种意见是荒谬,也不认为它是刚愎自用。希特勒并非凭借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他成为领袖之前已是首相,对法律形式的利用开始时小心谨慎,后来由于巩固的政权而变得胆大。对既定秩序的第一次袭击是攻打法律家和法官们守卫的城墙(如果说有人守卫的话),这些城墙几乎未经战斗便倒下来了。
告密者案件的判决与拉得布鲁赫的著作中都曾谈到一个“高级法”,哈特教授和其他人为此的烦恼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如果法学曾更多地关注法律的内在道德,它就不必求助于这种概念来宣布残暴的纳粹法规无效。
以冠冕堂皇的法律形式掩盖自身的独裁统治是如此远地背离了秩序的道德、背离了法律自身的内在道德,以致于它不再是法律制度,对我而言,这并没什么可惊奇的。当一个自称为法律的体系是以法官们普遍漠视他们声称要实施的法律条款为基础时;当这种体系习惯于是通过有溯及力的法规矫治法律的不规律性(甚至是最严重的不规律性)时;当这一制度只能诉诸于街道上的恐怖袭击,以逃避合法性伪装下所强加的那些有限的限制,却没有人敢于对此提出挑战时;当所有这一切已成为独裁统治的真实情况,对我来说,至少拒绝名之为法并不难。
我认为,告密者案件所涉及法规的无效性就可能建立在我刚才所勾勒出来的种种考虑之上。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人们不仅这么说,而且这么认为,如果你和自己的同代人都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么你会觉得要逃离某种法律的唯一路径就是以另一种法律来抵消它,后者必定是“高级法”。因此,这些有关“高级法”(它们是发出警报的合理理由)的想法本身就可能成为德国法律实证主义迟来的果实。
这里应该谈到,自然法理论主要是在罗马天主教著作中提及的,不是简单地用来寻求一种使人成功地一起生活的原则,而是用来追求能被称作“高级法” 的东西的。把自然法理解为人类法律之上的法律,这一点实际上看起来是任何教义的要求,只要这些教义断言,对自然法要求发表权威性声明是可能的。迄今为止发表的权威声明所影响的领域里,在我看来,罗马天主教教义与其对立观点之间的冲突是两种实证主义之间的冲突。幸运的是,在法律家关心的绝大部分领域中,这样的声明并不存在。我认为在这些领域里,我们当中那些不支持这一信仰的人会感激天主教堂,因为它使伦理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存活下来。
我并不是断言我对告密者案件提出的解决方法不会遇到它自身的困难,尤其熟悉的那一个困难是要明白其限度。但是,我认为,希特勒统治下的法律部门中发生了法律道德最严重的恶化,这是可证明的,如告密者案件涉及的法律部门。我们不会看到什么法律道德的恶化可比得上在普通的私法部门中的恶化了。正是在这些法律的目的由于通常的得体标准(standards of decency)而变得让人讨厌的领域里,法律自身的道德被最明目张胆地忽视了。换句话说,当竭力诱导一个人去说“这是如此邪恶以致于它不可能是法律” 时,相反地,这个人通常可能会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制度的产物,这个制度对法律的道德如此忽视以致于它不能被称为法律。”我认为这并不仅仅是偶然的现象,因为这两句话都意味着,法律的道的性在中断迈向正义和得体的努力时是不能存活的。
但是,像哈特教授和拉得布鲁赫一样,作为告密者案件实际的解决方法,我将更偏爱有追溯力的法令。偏爱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以最接近法律的方式使得曾经一度为法律的东西现在变得不合法。我宁愿把这种法令看作是象征着与过去明显决裂的方式,看作是从司法程序正常运作中隔离出来的一种进行清除活动的手段。因为它是隔离开来行使的,这就有可能会使司法更迅速地返回到给与法律道德性以恰当尊重的状态,有可能更为有效地进行计划,使对法律忠诚的理性重新获得其正常的含义。
七、解释问题:核心与边缘暗区
有必要尽可能地澄清哈特教授的“核心与边缘暗区”之学说的意义,因为我认为一位粗心的读者可能会错误地解释他所说的。该读者易于设想哈特教授仅在为法律家描述一种日常经验的情形:即在对法律规则进行解释过程中,典型的情形(虽然并非普遍的情形)是有些情况似乎明确地适用该规则,而另外一些情况下是否适用该规则则含糊不清。但是,哈特教授却并不是如此简单。他对于“核心与边缘暗区”的大量论述不只是一种确认一些案件难以判断而另一些容易的复杂方法,相反,基于语义论他提出了一种我认为是全新的司法解释理论。可以肯定地说,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以如此不妥协的方式提出司法解释的理论。
依据我对哈特教授的论文的理解,其中包括一些隐含在其中的默会的假定,还有一些他无疑希望提供的一些限定,我们可以将他的理论充分的表述如下:通常说来,解释的任务就是决定法律规则中单个词语的含义。例如,“车辆”(vehicles)在禁止车辆进入公园的规则中的含义。更为特别的是,解释的任务在于确定这样的一个词语的参照范围,或者所指的事物聚合体(the aggregate of things)。交流之所以可能仅在于词语有一个“标准情形”(standard instance)或“核心含义”,它不论出现在什么样的情况中都保持相对不变。除非在异常情况中,我们总是可以认定象“车辆”一类词语拥有其“标准情形”,即拥有这个词语在通常的语境中(无论涉及法律的语境或是与法律无关的语境中)所包含的那个事物的聚合体。在任何法律规则中,不论法律规则的目的是什么,该词语都具有这个含义。将词语适用于它的“标准情形”的过程中,法官不会充当任何创造性的角色,他只是在适用“如其所是”的法律。
然而,词语除了有一个不变的核心含义之外,还有一个含义的边缘暗区 (penumbra of meaning),和核心含义不同,它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当问题的对象(如三轮车)处于“车辆”一词的边缘暗区的时候,法官不得不充当一种更具创造性的角色,此时他必须初次依照规则的目的来进行规则的解释。想一想有关公园的规定所追求的目的,难道认为它禁止三轮车吗?当决定这类问题时,至少存在着 “是”与“应当”的“交叉”之处,因为法官在决定规则“是”什么的时候,是根据他为了解释规则的目的而形成的“它应当是”什么的观念。
如果这就我对哈特教授涉及到“硬核”的理论的正确解释,那么我认为这种理论是相当成问题的。他的理论之最明显的缺点在于假定解释问题主要依靠单个词语的含义。肯定没有那个法官在适用普通法的规则时候,会遵循哈特教授所描述的那些程序(在我看来,是哈特教授规定的程序)。其实,我们通常不认为哈特教授所提出的问题是一种“解释”问题。即使在有关成文法的情形中,我们通常不是确定单的词语的含义,而是文本中的一个句子、一个段落、或者一整页或者更多篇幅的含义。这样的段落无疑不会有无论在何种语境中都会保持不变的“标准情形”。如果一部成文法似乎有一种我们无需精确地探究其目的就可以适用的“核心含义”,那是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我们怎样阐述该法律的精确目标,它都会符合该法律的要求。
即使我们的解释难题出现在单个语词的情况中,哈特教授的分析,在我看来,没有给出发生或将要发生什么的真实叙述。在他对“车辆”的例证里,尽管他告诉我们这一单词在各种语境种都能对其包含的对象范围做出了清楚界定的核心含义,但他却没有告诉我“车辆”一词所包含的对象是什么。如果禁止车辆进入公园的规则在一些案件中似乎易于适用,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规则的“一般目的”是什么,以致于我们认为担心福特和凯迪拉克的差别是没必要的。有些案件我们不问规则的目的就能适用,这不是因为我们将其视为一种仿佛没有任何目的命令性安排,相反是因为,举例来说,不论规则是用以维持公园的安静还是保护悠闲的散步者免于受到伤害,我们不用想就知道,制造噪声的机动车肯定是被禁止的。
如果当地的爱国者想在公园里找一个地方为支座安置一辆二战用的卡车以作记念,然而另一些公民认为看到会引起不快而以“禁止车辆”规则支持其立场,那么,哈特教授有何要说的呢?这辆性能完好的卡车属于“车辆”一词的含义的核心呢还是处于边缘暗区?
哈特教授似乎断定除非词语拥有不受情境影响保持一致的“标准情形”,否则有效的交流将会中断,并且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规则体系”也成为不可能。如果在每一种语境中,词语都有一个仅仅适合该语境的含义,那么整个解释过程将会变得变幻莫测和主观臆断,以致于法治的理想将失去其意义。换句话说。哈特教授似乎是说除非我们准备接受他对解释的分析,否则,我们肯定会放弃所有给予忠实于法律理想以真正意义的希望。如果有人如我一样认为我们不能接受他的解释理论,这真是预示了一个非常暗淡的前景。但是,对忠实于法律这一理想的未来,我从不持有如此悲观的观点。
有一个例证将会有助于不仅验证哈特教授核心和边缘暗区的理论,而且也验证它与对法律忠诚这一理想的相关性。让我们就定,在翻开法规的时候,我们碰到如下规定:“睡于火车站者应为轻罪,得处5美元罚金”。我们毫不费力就可理解这一法规指向的目标的一般性质。实际上,我们的脑子里可能立即会浮出这一画面: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姿势难看地躺在车站里的长椅上,使疲倦的旅客不能坐着休息,听着他鼾声大作,酒气熏天。这场景颇能代表法规所指的“明显情形”(obvious instance),尽管这肯定远非生理学中上“睡眠”状态的“标准情形”。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一例子和对于法律忠诚的理想有什么关系。假设我是一个法官,有两个人因违反此项法规而被带到我的面前。第一个是一位因火车延时而于凌晨3点仍然等待的旅客,当他被逮捕时,他正在安静地坐着,但执行的官员听到了他轻微的鼾声。第二个是一位带着毯子和枕头去车站的人,很明显是想在车站过夜的,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睡觉之前就被逮捕了。这些案中的哪一案件代表了词语“睡眠”的“标准情形”?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就决定处予第二个人罚金而释放第一个人,那么我是否违反了对忠实于法律义务?如果我把这一法律中的词语“睡眠”解释为“某人躺在长椅或地板上过夜或似乎想过夜”此类的含义,我是否违反了忠实于法律的义务?
我们来验证哈特教授理论的另一个方面:不用知道法规的目的而去解释法规中的一个词语,这真的可能吗?假设我们碰到下面一个不完整的句子:“所有进展须迅速报往……”。哈特教授的理论象是断定:即使我们仅有此一片断我们也能阐明词语“进展”,以适用它的“标准情形”。尽管在我们能明智地处理“边缘暗区”之前,我们不得不去了解句子的其他部分。可是,我所引的这个截短了的句子中,词语“进展”肯定如同符号“X”一样没有意义。
如果我们以“护士长”或“村镇规划局”等词补充句子,词语“进展”就立即有了含义,尽管这些词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但不能说这两种含义代表了词语的“标准情形”的边缘暗区扩大了。有人顺便又想知道,如果报告是送往规划局的,在决定词语“进展”是否包含因为一所房屋不能抵押使得它所在的地皮降价的时候,核心与边缘暗区的理论能起多大的作用。
我想,考虑以其他方式补充这个句子是有启发意义的,假设我们给“所有进展须迅速报往……”加上“研究生分部主任”。在此,我们不再象以往一样在黑暗中摸索,相反,我们似乎将要进入了这一个空盒子(empty box)。如果,最后的短语是“校长”,我就获得了一个更好的理解方向。如果是“送往初中学生家长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则我们可以彻底松一口气了 。
应当注意,决定在各种案件中这个词语“进展”的含义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将这一词语放在如医院执业,村镇规划,或教育的一般语境中去理解。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进展”在上述最后一个例子中也与教师和学生在该例中的含义一致。相反更进一步,我们要问自己:此项规则为何存在?它追求或避免何种恶?它试图促进何种善?当报告是送往护士长时,我们会问:“是不是或许由于医院空间不足以致于那些恢复很好的病人就被送回家里或被安置到受到较少护理的病房去”。如果说“校长”一词比“研究生分部主任”更易于理解,这肯定是因为我们对初级教育与大学研究生教育之间的差别略知一二。在任何关于“校长”与“研究生分部主任”的差别影响到我们对“进展”的解释之前,我们一定是对两种教育事业运行的方式和其面临的问题有一些最低限度的认知。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将我们置于法规制定者的位置去理解他们认为的“应当”是什么。正是依据“应当”我们必须决定规则“是”什么。
现在转向哈特教授所谓的“关注边缘暗区”问题,我们必须要问自己,通常所假设的各种“边界”(borderline)情况对解释过程有什么助益呢?哈特教授似乎在说:“噢,什么都没有,除非我们在解决暗区问题”。如果这就是哈特教授的意思,那么我发现他的观点令人困惑,因为他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处理某一个边缘暗区问题时,对考虑其他边缘暗区问题会有帮助。
哈特教授在他的有关解释的整个讨论中,似乎假定有一种编目程序(cataloguing procedure)。法官面临一个新问题就象一个图书馆馆员决定一本新书放在哪一书架上,简单的情况如:《圣经》属于宗教类,《国富论》属经济类,如此等等,易于处理。那么难些的例子,则需图书馆馆员进行创造性的选择:《资本论》是属政治类还是经济类,《伽里奥游记》是划入幻想类还是哲学类。但是不管决定归类是容易还是困难,图书管理员都不得不把书放好。哈特教授认为在所有实质性的细节上,法官也是如此。当然,司法过程还有编目程序之外的含义,法官不能在给案例作出适合的归类之后就撒手不管。如果你愿意的话,法官还不得不作出更多的事情以解决案件。正是这一更大的责任,说明了解释问题决不能依靠单个词语的原因,也说明了为什么历代的法律家认为“处于边界的案件”(borderline cases)虚构边缘案件不仅对于边缘暗区的理解是有帮助的,而且有助于弄清边缘暗区是什么地方开始的。
我认为,重新讨论“所有进展须迅速报往……”这句法规的例子,就可以搞清楚这些问题。不论短语后面的省略号指的是什么,法官仅仅决定“进展”的种类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几乎句子的所有词语都需要解释,但最明显的是“迅速”和“报告”。何种“报告”被考虑过呢,是一个“便条”还是一项医院记录中的住院声明?它必须明确至何种程度?讲“好多了”或“一间有凸窗的大屋子”能够充分表达含义吗?
现在,任何法律家都清楚:解释如“进展”“迅速”“报告”之类的词,查问一些法外的“标准情形”对这些词语的解释没有真正的帮助。但更为重要的是,当这些词是单一思考结构的所有组成部分时,在解释过程中,它们之间会相互影响:“什么是一个‘进展’?那么,它一定可以成为报告的主题,于是,就法规的目的而言,‘进展’实际上就意指‘可报告的进展’。‘报告’必须制成何种式样呢?那么,这要依靠从中可以得到信息的‘进展’种类和意欲得到信息的大量理由来决定了。”
当我们超出单个词语而视法规为一个整体时,这些假设的案例对解释过程的帮助就变得大致清楚了。通过引导我们的思想到不同的方向,这些案例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面前的思想框架。这个框架正是我们尽力去识别的,所以我们能真正理解它是什么,同时它也是我们为了努力(依据我们忠实于法律义务)使法规成为连贯、可行的整体,而不可避免有助于创造的东西。
如果不是为了回应哈特教授的解释理论,我本不该在这里多说这些陈词滥调的东西。哈特教授认为他的理论如此重要以致于除非接受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忠实于法律。法律解释所关注的核心是法律的目的和结构,而非法律的词语,那么实证哲学有可能命令我们放弃这样的观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场学派之争的赌注也太高了。
我曾经从维特根斯坦关于教小孩做游戏的例子获得一些教益,但是,让我迷惑不解的是哈特教授给这些教益赋予了新的理解。我仅试图表明,通过与面临同一问题的人进行交流,并设想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反思可以推动我们做出应当做什么的决定。我假定所有这些简单而又熟悉的措施可能使我们明了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并且整个过程不仅是为达到目的而选择适当的方法的问题,而且是对目的本身的阐明,当一位著名的英国法官把普通法说成是“纯粹自身”的运作时,我认为他有类似的想法。如果对司法过程的这种观点在其起源国家不再存在,我只能说,不论曼斯菲尔德勋爵在英国的声誉如何变化,对我们来说,他将一直是他的国家的法理学中的英雄人物。
我已经强调了哈特教授理论的不足之处,因为这种理论影响着司法解释的。然而,我相信它的缺陷会变得更为严重,一般说来,其原因最终来源于有关语言含义的错误理论。哈特教授提出一个可以称作“意义的指称理论”,该理论忽视或者降低讲话者的目的和语言结构对词语含义的影响。这一思想学派的特征在于拥有“习惯用语”(common usage)的观念。当然,其原因在于:只有在这种观念的帮助下,好像才能获得它所追求的死的意义材料,这是一种不受语词的目的和结构影响的意义。
我不想在这里进一步讨论语言学理论。我必须满足于指出:隐含在哈特教授论文里的“含义理论”在我看来它已为站在逻辑分析方面现代发展最前沿的三个人所抛弃:他们是维特根斯坦、罗素和怀特海。维特根斯坦在其去世后才出版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讨论了由于词语语境的变化而引起词义变化的方式。罗素则否定了对“习惯用语”(common usage)的迷信,反而问道,如果我们没有任何明确动机而使用“词语”这个词的时候,那么我们能给“词语”这个词本身赋予什么样的“内容”呢?怀特海则说明了“反复使用的词语具有的欺骗性”(the deceptive identity of the repeated word)对于现代哲学家所具有的吸引力,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假定一些语言学上的一贯性(linguistic constant)(如“核心含义”),才能主张必然要使语词在语境之间来回运动的逻辑程序式有效的。
八、实证主义的道德基础和感情基础
如果我们忽略那些和实证主义哲学相关联的具体理论理论,我相信我们能够这样说:实证主义者的最主要论调就是担心对法律和法律制度作目的性解释,或者至少他们担心这样的解释会被推进得太远。我认为有关这种担心的明确又肯定的迹象可以在所有那些被哈特教授归类为实证主义者那里找到,当然,一个明显的例外就是边沁,他在哪一方面都是一个例外,并且同所有那些能够被称得上是“伦理的实证主义”的观点完全是两回事。
现在我们当中许多人都确信:这种对目的性解释的担心给实证主义带来了一种病态的转向。但是这种这样的确信将不会误导我们认为那种担心是没有一点儿合理根据的,或它仅仅反映了在社会组织中毫无意义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承受法律的目的解释带来的更大责任(这些责任本身就是目的性的,就像所有的责任都是并且必须是具有目的性的),那么“忠实于法律”就会变得不可能。可以假设下面一种可能情景:一条法律规定不应当出售苦艾酒。这条法规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促进健康。但现在众所周知的是,苦艾酒是一种很好的、有益健康的饮料。因此用法规本身目的来解释这条法规,我会把它理解为是命令出售和消费最健康的饮料——苦艾酒。
如果在目的性解释中,这类事情的危险是隐含的,那我们能够采取什么办法去消灭它或者把它减少到一个可以容忍的程度呢?有人试图这样说:“这有什么,不就是采用了一般的普遍感觉吗?”但这只是一种对问题的回避,就等于在说——虽然我们知道答案,但我们无法说出它是什么。为了给出一个更好的答案,恐怕我将不得不背离那些被哈特教授高度赞赏和经常示范的有关清晰条理性的高标准。我将不得不说答案就在一种结构这个概念当中。一部成文法或者一条普通法的规则,或者明显地,或者通过与其他规则的联系,都具有所谓的“结构完整性”。这就是当我们说到“法律的意图”时我们脑海中所想到的,尽管我们明白是人而不是纸上的词语具有意图。在这种结构的限制之内,“忠实于法律”就不仅允许而且要求法官扮演一个创造性的角色,但是超越了这一结构,它就不允许法官多走一步。当然,我所提到的结构具有它自身的“边缘暗区问题”。但是,在这一案例中的边缘暗区包围着一些真实的事物,一些有其自身的意义和完整性的事物。它不是那种借用诗歌语言的惯用法来获取其自身意义的漫无目的的词语的组合。
哈特教授的文章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它使实证主义关于忠实于法律的理想的观点变得清晰明了。然而我认为(尽管我不能够证明),实证主义担心目的性解释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它可能导致一种无政府状态,而是因为它可能把我们朝相反的方向推得太远。它认识到,目的性解释将会严重地威胁人类的自由和尊严。
让我通过这样的假设来阐明我所说的意思:假定我是生活在一个热烈地信奉新教的社会中的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这个社会中的一条法规规定我在星期天打高尔夫球将是违法的。我认为这条法规很讨厌并且很不情愿地接受它的规制。但是我感觉到的这种烦恼和我在下面的情景中体验到的“不高兴”不会有特别大的区别。即假设即使在星期天玩高尔夫球是合法的,但由于某种阻碍使得我不能够搭乘我通常会坐的去高尔夫球场的那次有轨街车而无法去打高尔夫球。俗话说得好: “这样也不过就是如此罢了。”
假设如果有一条法规强迫我去教堂,甚至更糟糕的是,迫使我跪下祈祷,那么这整件事会呈现多么不同的性质呀。此时我将感到一种对我人格尊严直接的侵犯。然而这两条法规的目的都可以被解释为促使人们多上教堂。其区别只是第一条法规掩饰地间接地去追求其目的,而第二条却是直接地公开地去追求。然而这确实是一种情形:在其中“间接”有其美德,,而“直接”却对人类尊严造成侵犯。
现在我认为实证主义就是担心一个太直截了当和毫不拘束的以目的为名义的解释恰恰会推动第一种法规朝第二种法规的方向转化。如果这是实证主义哲学最基本的担心,那么这种哲学正在应付一个真正的问题,无论如何,它对这一问题的反应似乎是无能的。因为这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目的问题,在我们社会中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你可以想一想通过全国劳工联合法案中确立的讨价还价中的“诚信”义务。你可以回想一下这样的主张:惩罚犯罪与其说是公开侮辱他的人格尊严,不如说是改造和完善罪犯。我们会想到法规的序言:成文法适用的不断增加,成文的立法智慧,符合成文法的意涵的司法解释。我们大家自然会想到向国旗致敬案。我自己想起了Hippel教授关于纳粹政权最根本错误的精彩分析。他认为纳粹暴行的最错误之处就是他们的强迫行为——例如要悬挂国旗,还要说“嗨,希特勒!”。而这种行为只有在自愿地去做的时候才有含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在这种被强迫的行为是完全依赖于和过去那种自愿表达的联系时,它才有含义。
当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承担一个更积极的角色时,这类问题毫无怀疑地变得更加明确。有意义的经济活动不可能通过“禁令”垄断性地组织起来,经济生产的性质要求一种相互合作的努力。因此,在经济领域中有一种特别的原因,担心“这是你可以不做的”
将被转变为“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但是自愿的”。众所周知,在行政实践中的“预先听证会议”就代表了导致影响这种转变的最大可能。在这里,行政官员会使用国家禁令的消极的威慑力去劝导一种他们真心实意地认为是正确的态度。
我期待着有一天法律哲学能够使自己热切地从事于讨论这种类型的问题,而不是当一种状况已经形成后仅仅利用它们来获得好处。在我看来,哈特教授的文章为这样的讨论开辟了道路,因为它从实证主义哲学中摒除了那种迄今一直迷惑着每一种涉及它的讨论的假定。当然,这种假定就是实证主义的道德上的中立性。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无比诚恳地说,尽管我几乎整段整段地不同意哈特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我仍旧认为哈特教授对法律哲学作出了持久的贡献。
*译文是“当代西方法哲学”课程中集体合作的成果,译者依照翻译内容的次序分别为强世功、郭永茂、蔡巧萍、李娟、赵建丽、江照信和俞嘉颖,部分内容经过课堂上的讨论和相互校对。最后由强世功统一校订。
[1] Kelsen,Die Idee des Naturrechtes,7Eeitschrift für öffentliches Recht,221,248(Austria,1927).
[2] Hart,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72Harv.L.R.,593,615-21(1958).
[3] 美国宪法第五条。
[4] Hart,前注2,页624。
[5] 一个突出的例子,见G.Scammell and Nephew,Ltd.v.Ouston,,[1941]A.C.251 (1940)。我个人倾向于把Victoria Laundry ,Ltd.v.Newman Industries,Ltd,[1949]2K.B.528(C.A.)一案归为该情形。
[6] 参见Hart,前注2,页608-12。
[7] 参见N.Y.Times,Nov.8,1949,第一版第四栏(late cite ed.)(关于1949年11月7日对“天主教意大利律师联合会中央委员会”所作演讲的报道)。
[8] Hart,前注2,第603页。
[9] 同上。
[10] 奥斯汀,《法理学讲座》,页167——341(1885年第五版)。
[11] 凯尔森,《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页401,(1949年第三版)。
[12] Lowie,The Origin of the State,113(1927).
[13] 哈特,同上注2,第619——620页。
[14] N.Y.Times,July 4,1934,p.3,col.3(late city ed.)。
[15] 参见N.Y.Times,July 4,1934,p.5,col.2(late city ed.)。
[16] Radbruch,Die Erneuerung des Rechts,2DIE WANDLUNG 8,9(Germany 1947).关于
纳粹赋予法律公开性的问题的有益讨论,见Giese,VerkÜund Gesetzeskraft,76ARCHIV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464,471-72。我在本文中的一些观点都依赖此篇文章。
[17] Judgment of July 27,1949,Oberlandesgericht,Bamberg,5SÜDDEUTSCHE JURISIEN-ZEITUNG,207(Germany 1950),64Harv.L.Rev.1005(1951).
[18] 这一部分翻译的是一个创设——的法规的第5条。Law of Aug.17,1938[1939]2REICHSGESETZBLATT pt.I,at 1456.
[19] 参见5SÜDDEUTSCHE JURISTEN207,210(Germany 1950)
[20] 参见Radbruch,Die Erneuerung des Recht,s
*这些单词是作者故意拼写错的,意思是指没有意义的句子。——译者注
[21] 见Howe,The positivism of Mr.Justice Holmes,64HARV.L.REV.529(1951)
[22] 见I PERRY,THE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 297(1935)(quoting a letter written by WILLIAM JAMES in 1869)
[23] HART,supra note 2,at 617-618
[24] 同上,at 618
[25] 同上,at 619
[26] I AUSTIN,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173(5th ed.1885)(Lecture V).
[27] GRAY,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THE LAW 96(2d ed.1921)
[28] I BERGBOHM,JURISPRUDENZ UND RECHTQPHILOSOPHIE 355-552(1892)
[29] 见HELLER,Die Krisis der Staaatslehre,55ARCHIV FU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289,309(Germany 1926).
[30] Voegelin,Kelsen’s Pure Theory of Law,42POL.SCI.Q.268,269(1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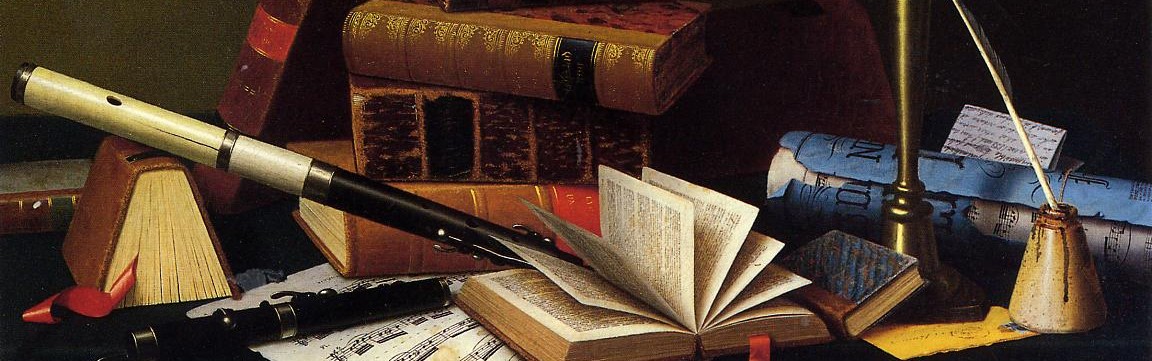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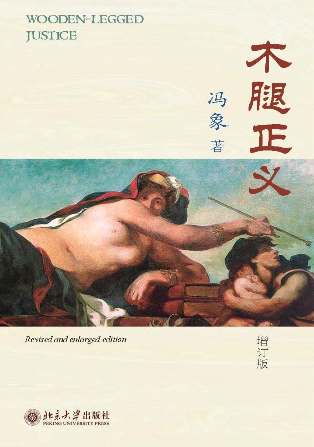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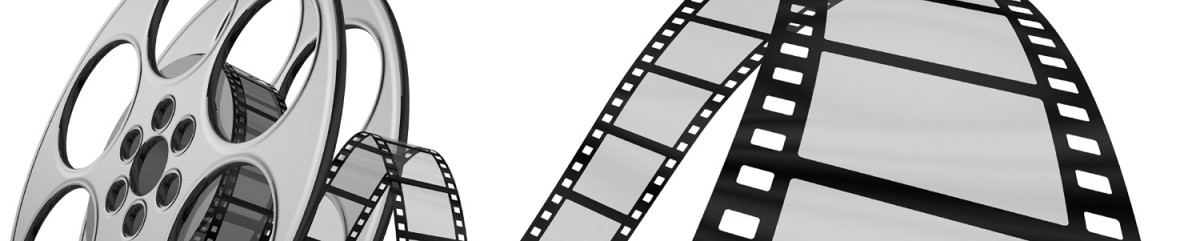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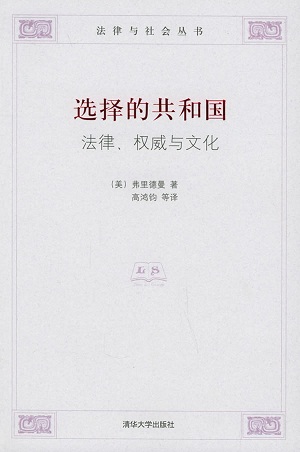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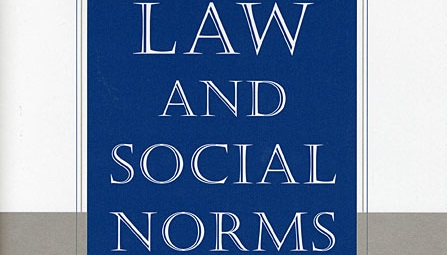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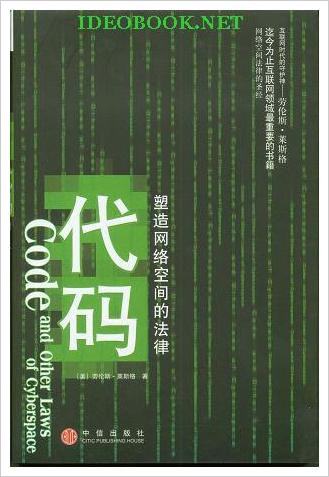 劳伦斯·莱斯格(
劳伦斯·莱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