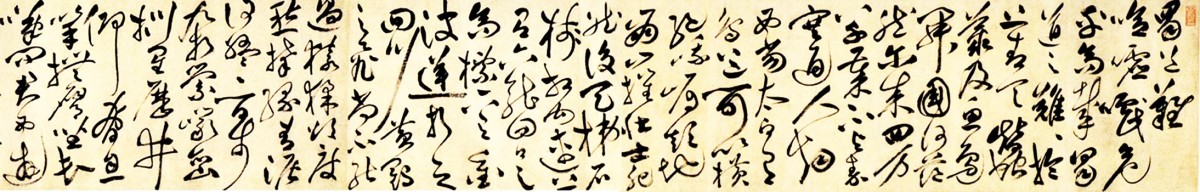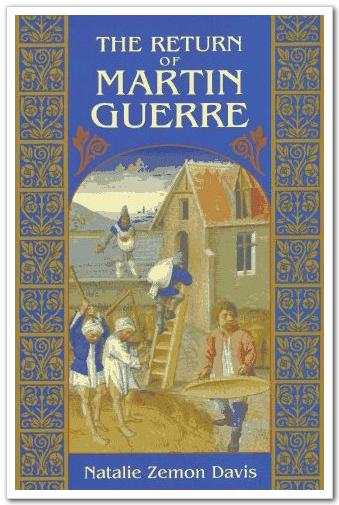苏力:这一刻,你们是主角——北大法学院2003级新生开学典礼致辞

各位同学,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北大校园!在今后的四年或三年里,我们都共属于这个大家庭。你们的履历上会永远写上“北京大学法学院”这几个字,成为你们的自豪,成为你们的骄傲。
但也未必。
许多同学可能已经知道,我们学校最近有一位校友被媒体疯狂炒作着。陆步轩,住在西安,因为工厂下岗,只好转行卖肉;据说仅仅因为这样的媒体炒作,我们的这位校友近来生意一直特别好,每天多卖很多肉,收入也因此大增;甚至有人想同他联营注册一个连锁肉店“北大仁”——仁爱的仁。
但是,同学们,我们不要只是把这当作一个社会新闻或笑话听;要想一想,如果是我,如果是你,让别人“嚼舌头”,会有什么感受?为什么?想想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对于你,对于我?
是的,社会正在变化,传媒更为发达,言论应当更加自由;是的,工作无分高下。这些道理都好讲,也都对,但一旦具体到某个人、某件事,却并非总是如此。而且,我总认为,当人们说工作无分高下的时候,恰恰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工作还是有高下的,即使言说者有意抵抗什么,但弄不好却掩饰了什么。至少在当代中国,哪怕同样是上了报纸,下岗转业却一定不如王选教授获得国家科技最高奖那么光荣;吆喝卖肉恐怕也不如我站在这里致词那么风光。说真话,我们——你们 ——真的认为这都一样吗?我们千万不要上当,用别人塞给我们的概念生活,或总是生活在一个概念的世界。事实上,陆步轩还算是幸运的,如果他不是北大的学生,媒体会把他当回事吗?为什么媒体不报道张三、李四卖肉?就是因为他有北大毕业生这样一种社会认为较高的身份,也就是因为卖肉在社会看来是一个比较低的工作,才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曝光,带来了某种尴尬,尽管这还算是一种令人庆幸的尴尬。
而这一切都不无可能,在未来,在你我当中某一个人的身上发生。考虑到前不多久另一件被媒体上炒作得很凶的有关北大教改的事(包括我自己也卷入了这一“合谋”),我们就必须清楚,在今天这个世界中,北大已不再仅仅是或总是你的资本,弄不好它也会成为你终身的负担——用公司法的名词来说,是一种“负资产”。
因此,同学们,尽管北大的名字从此将同你相濡以沫,但未必可以托付终身。北大产生过许多名人,但不要错觉自己进了北大也就成了名人;其实这些名人大致与你我本人无关,有关的那一点也只是在概率上。我们已经身在一个个体主义的社会,一个竞争的社会了,父母或家族或门第的余荫已经消散,那些家境贫寒的农村同学可能会最深的感到这些;学校或导师的大名都不过是产品的商标和商誉,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责任。
这就注定了北大并不仅仅是一个学习书本知识的地方,千万不要以为书本中、课堂上已经包含了制作你一生幸福的秘方。你们要“迎接挑战”,要“发现你的热爱”(这都是我先前的新生讲话,也许还值得你们上网看一看),但更重要的是要把大学校园视为一个现代化的组织机构,在这里,你要全面接受一种训练,一种现代化的训练。
你必须培养一种新型的责任感,不但要好汉(好女)做事好汉(好女)当,而且要对你的机构、你的单位、你的“老板”负责,一定不能混淆了自己的和“ 老板” 的利益;你要学会自己面对各种各样的陌生人,同你喜欢或不喜欢的、行为古怪甚至居心叵测的人合作——包括某些时候的不合作,而不能按地域、学历、家庭或其他因素来选择;因为你喜欢“熟悉”,你必须更多面对“陌生”——这意味着持久的学习;因为你在乎一个长久的成功,你必须接受众多眼前的失败——这意味着不断的风险;你必须学会面对种种诱惑,仍然要信守承诺、诚信做人,必须从现在——也许从助学贷款或遵守时间——开始培养自己的信誉;你可以充满理想,但不但不能太理想化,而且要宽容像我这样的好像没什么理想的人;你可以且应当从情理想事,但必须学会按原则办事;你们可以保持甚至坚持自己的偏好,却必须学会用效率的眼光来考察社会和自己的选择和付出;你们不要指望大学老师还像高中老师,不但是知识的化身,而且是真理甚或道德的楷模,其实他们只是另一种职业的知识人;你们必须遵守各种规则,不要指望好学生总会从老师和家长那里得到优待和特权,因为你们——至少本科生——每个人都至少是本县的状元;在这里,你会感到社会中的各种知识的类型和重要性都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或仍然令你们动心、动情或动容的文字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只能作为你熄灯后侃山的谈资,或恋人间 “秋日的私语”;你们要面对的是一套看上去很其实未必冷冰冰的关于社会的因果性的知识,斐然的文采必须让位给叙述的精确;甚至你们必须学会一套现代的有关知识和学术的规范:抄录它人的精美文字,在中学时可能得到作文老师的一串串红圈,而在这里,则是侵犯知识产权,甚至是剽窃,不能毕业,得不到学位;你们会发现这里学习的许多职业规范与你在中学或父母那里获得的社会规范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不一致,你必须重新界定各自的适用范围。
大学已经不再只是——其实从来也不只是——一个接受知识的地方,它也是一个训练人的机构,一个让现代生活的知识和纪律融入你们身体的机构。你们必须接受这些,要有一种真正的时代感。因为你们并不打算回到你生活的起点,而是把这里当作生活的起点;你们当中如果不是全部那也是绝大多数最终将生活在现代的都市,少说是个“白领”,最不济也混个“小资”。在这个意义上,你们是这个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的先进者。
因为,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一个空前深刻且巨大的变化。
对于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对于本科生同学来说,这一刻也许会是你们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刻之一,至少就感情兴奋的强烈程度而言。这一刻,你们是生活的真正主角。而今天来欢迎你们的教员、职员,包括在这里讲话的我这位院长,其实都是今天的配角。尽管每一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心也都充满了感动,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场合更多是一种仪式,一种程序,也是一种职责;即使感动也首先是因为你们的感动,是因为你们而感动。但我们的感动和你们的感动是并不一样的,就如同此刻你父母的兴奋同你的兴奋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泪水和你的泪水是不一样的。
这一刻属于你们。但是,生活没有永远的主角,在这个已经或正在到来的时代,尤其如此。
再过几天,就要“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了;我祝所有的新同学,尤其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的同学们,中秋愉快。我们会努力为你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并且会——套用一首歌的句式——“幸福着你的幸福,痛着你的痛”……
2003年9月4日于北大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