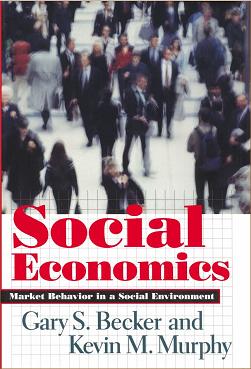埃里克·波斯纳:法律与社会规范·导论:法律与集体行动
译者:沈明
一位怀孕的已婚妇女为确定其孩子的亲子关系而请求法院指令那位被指称为孩子父亲的人(不是她的丈夫)验血。法院依据普通法关于已婚妇女孩子的合法性(legitimacy)[1]的法定推论而拒绝了该妇女的申请。法院认为这一法定推论减少了使孩子受辱成为私生子(illegitimate)的机会。这里的意蕴是:和容许孩子获知自己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相比,使他免受私生子的耻辱是一件更好的事情。[2]
警察警示本地商人说某人因扒窃商店而被拘留,尽管并没有受到起诉。一个学校告知一位求职者说本校一位老师曾经对一名学生性骚扰,不过这位老师并没有被惩罚、开除或者解雇。对于商人和可能会受雇成为教师的人来说,精确信息的传达无疑是有益的,但这也可能使他们蒙受羞辱。这种可能性能否触发启动正当程序的要求呢?[3]
一位拖船主没有为自己的拖船装备作业所用的无线电讯设备,拖船因此就没能收到天气预报,否则的话,它们或许就能躲过一场风暴,而这场风暴给客户的货物造成了损失。拖船主辩称,拖船业中并没有使用无线电讯设备的惯例,所以自己的上述行为并不构成过失。法院认为惯例并不能成为辩解理由。[4] 然而为什么不能呢?商业惯例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低于法院司法意见的吗?
一对夫妇在民事法庭获得离婚判决。只有在丈夫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所属的宗教群体才承认离婚的效力,而且,如果女方在其离婚未经宗教承认的情况下再婚的话,就会遭到其宗教群体的放逐(ostracize)。丈夫以收回其宗教上的离婚允诺为要挟,使妻子屈从了一个偏袒一方的财产分配方案。此后,女方基于被胁迫签约的理由请求民事法庭宣告该合同无效。[5] 如果法庭同意了她的请求,那么她的胜诉会对其宗教群体的凝聚力造成怎样的影响?
对于“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6]给出的常见正当化理由是:即使各州为黑人提供了适当的隔离设施,隔离黑人与白人的政策也是违反宪法的,因为这一政策使黑人蒙受了耻辱。
法院禁止某个地方政府在公共土地上建造圣诞树或者托儿所。这一规定冒犯了很多人,但是并没有伤害他们,另一方面,这却使更多的人感到高兴。从性教育到枪支管制,有无数的事情都冒犯了人们,但是这种冒犯很少成为评价这些方案的决定性因素。宗教里的符号象征(symbolism)又有什么不同呢?
法院每天都必须对行动的耻辱效应(stigmatizing effect)、行为与社会规范的一致性、符号的意义以及放逐的后果做出评估。艾滋病患者或者私生子或者接受福利救济者的耻辱是一种像戳伤眼睛一样的简单伤害吗?或者,这种耻辱促进了构成公共秩序的社会规范?当商业活动遵从而非背离惯例时,我们应当认定惯例反映的是进步的历程呢,还是逃散羊群的艰苦长征?当政府从事符号行为(symbolic behavior)(如偶像建构)或者限制符号行为(如亵渎国旗)时,真的会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危险吗?法律的介入能够消除耻辱、改变习惯与社会规范、变更符号的意义吗?——或者,这些社会事实在面对着自觉改革的努力时是坚强不屈的吗?
这些问题在法律与政治中的重要性是不能否认的。符号象征和耻辱在每一部主要立法中都发挥着作用。人们草拟出关于亵渎国旗的法案以回击毁损国旗行为的符号象征意义。在反对者看来,积极补偿行动增加了少数派群体的耻辱;而在支持者看来,积极补偿行动则削弱了少数派群体的耻辱。现代社会福利和破产立法意在消除穷困者和无力偿债者以及外来人和私生子的耻辱,然而这些法律的早期版本却是旨在强化耻辱的。删除记录的法律(expungement laws)规定了删除刑事罪犯的犯罪记录,减少了有犯罪前科的人的耻辱。对于器官出售、替身孕母、关于卖淫的立法、成本-收益分析、色情物品之类形形色色问题的争论,总是会提出上述关于实践的符号象征意义和运用法律对其加以控制的问题。
在一个不存在法律和最低限度政府的世界中,某种秩序仍然会存在。人类学研究已经明示了这一点。这种秩序大约会表现为对于社会规范的日常遵守和对违规者施加的集体性惩罚,包括使违规者蒙受耻辱以及对顽固不化者的驱逐。为了避免别人怀疑自己的忠诚,人们会对社群(community)做出象征性的(symbolic)承诺。人们也会更多合作。他们会信守并且信赖诺言,避免伤害邻人,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馈赠穷人,援救危难,参加民众集会和游行示威。但是人们有时也会违约并造成损害。那些已经成为某一群体所拒斥之行为的活符号(walking symbols)的人们会受到歧视,尽管他们自身并没有什么过错。他们之间会有争端,有时甚至是激烈的争端。仇恨会由此而生并且可能永远不会终结。社群可能分裂成小群体。秩序及其全部收益的获得都要付出成本。在和平时期,秩序是稳固的;但在危机时刻,它就会暴露出自己的孱弱。
现在添加一个强有力的、仁爱的、能够制定并实施法律的政府。这个政府能够有选择地介入非法律形式的秩序,做出去芜存精的改造吗?它能够在边界上微调激励,运用税收、补贴和制裁来消除——比如说——仇恨与歧视,同时又不会妨碍友好的亲善和信任吗?或者,社会组织的十足复杂性会压倒这样的努力吗?
从实证角度转向规范角度来说,对于诸如耻辱、放逐、社会规范、声誉、符号象征以及其他的、存在于国家法律之外的、不计其数的秩序渊源之类的事情,立法机关和法院应该怎样处理呢?我们是该假定这些事情是令人想望并且应该尊重和促进的呢,还是该认为它们是病态的并且是应该消除的?我们能够确定国家应该介入的条件吗?国家干预有可能会促进非法律合作的为人所欲的形式并破坏其令人厌恶的形式,但我们能否依据这种可能性对各种不同的干预做出评价呢?
这是一些老问题,它们占据了很多学术领域中的最优秀的头脑,但是在主流法律学者的关于法律如何影响行为的论著中,它们却被大大地忽视了,在有关法律改革的适当方向的著述中,这种忽视就更加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