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民主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潮流。联合国2002年的年度报告指出,从1980至2002年,已经有80多个国家从极权政体或威权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精英也为实现民主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民主运动和民主政体在现代世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里,人们却普遍感到民主体制的危机。在北欧一些国家,一个常见的汽车后档粘贴上写道:“对美国人要好一点 ……否则他们会把民主送到你的国家来。”虽然这一粘贴纸的主要用意在于表达欧洲民众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不满,但他们对民主的失望也跃然纸上。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民调中,人们对民选领导人普遍抱有不满情绪,但对非民选产生的政府官员却表示了很大的信任。在西方国家中,诸如《拯救民主》(Saving Democracy)和《理性选民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等学术著作不断涌现。当然,西方成熟民主社会中所出现的这些思潮和实证研究并不等于民主体制在西方社会已经发生根本性危机,但它们却明确地揭示了西方民主的弱点和西方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些弱点的不满。笔者认为,当代的民主化浪潮以及我国大量知识分子对民主的长期追求都反映了民主体制的巨大生命力,但成熟民主国家中民众对于民主的不满却也印证了民主体制的一些公认的不足之处。如何在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避免民主体制的弱点并发扬其优越性,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深刻理解民主体制的生命力及弱点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这是本文将着重探讨的问题。
在进入正题前首先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民主是中国不少知识分子所倡导和争取的目标,本文也将阐述为什么竞争性的民主选举是现代社会中产生政府的一个更为合理的方法,但在同时,本文也将以大量的篇幅讨论这种政府产生方式的不足之处。这似乎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尽管有些遗憾,我还是想就这一问题发表一些见解。民主本身的弱点给社会的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形成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也为从威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型带来了困难。特别是,当我们不能理解民主体制的这些弱点,而带着一种对乌托邦式的民主的美好理想在中国建立民主体制时,民主体制的这些弱点就会被放大,从而给人民和社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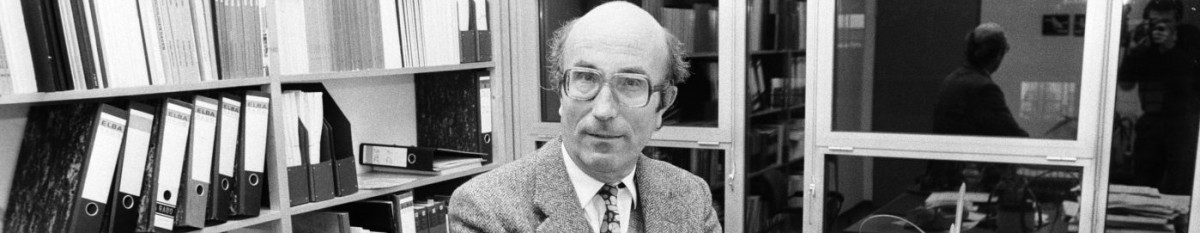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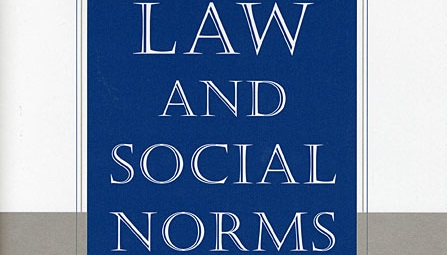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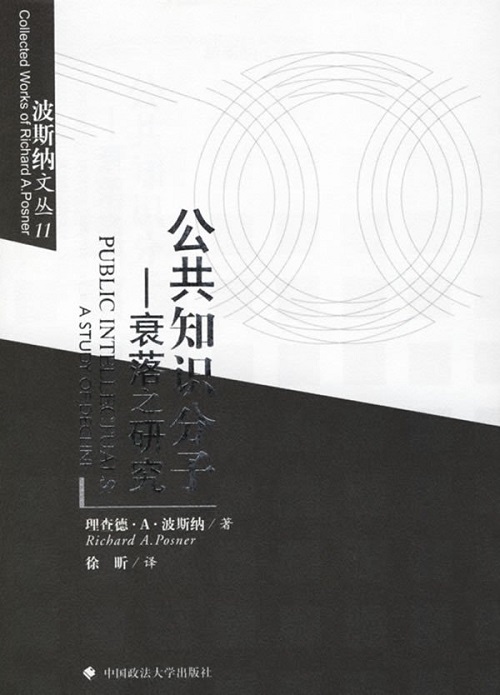 预感并不是来自书名,而是来自波斯纳1999年的两部专著:
预感并不是来自书名,而是来自波斯纳1999年的两部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