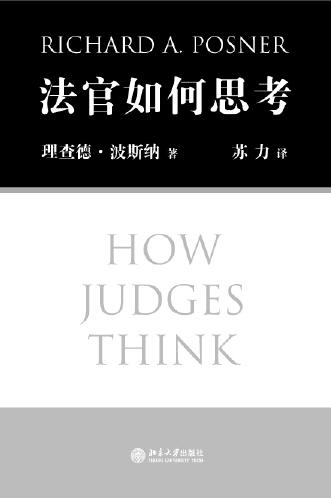强世功* 译
给了我事实,就可以给你法律。——拉丁格言
一门严格的法律科学,区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法理学就在于它把后者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一旦做出这种区分,那么这门法律的科学就立即使自己摆脱了法理学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关于法律论辩,即形式主义和工具主义之间的论辩。形式主义主张司法形式在与社会世界的关系中是绝对自主的;而工具主义将法律看作是一种反映,或者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工具。
就像法律学者,尤其是那些将法律的历史等同于其概念和方法的内在发展历史的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形式主义法理学将法律看作是一个自主的和封闭的体系,其发展只有通过其“内在的动力”才可以理解。[1] 这种坚持法律思想和法律行为的绝对自主性,确立了一种具体的理论思维模式,它完全不带有任何社会决定的色彩。凯尔森试图建立一种“法律的纯粹理论”,这只不过是形式主义思想家努力建构一套完全独立于社会约束和社会压力从而彻底地建立在自身之上的教条(doctrine)和规则的最终结果而已。[2] 这种形式主义的意识形态,即法律学者的职业意识形态,已经固化为一种“教义”(doctrine)。
与此相反,工具主义者的理论核心趋向于将法律和法理学看作是现存的社会权力关系的直接反映,其中经济决定了一切,尤其是表达了统治集团的利益,也就是说,它们是支配的工具。这种工具主义视角的典型例子就是路易斯·阿尔都塞所复活的机器论。[3] 但是,阿尔都塞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是这样一种传统的牺牲品,这种传统相信,仅仅通过指出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例如,“大众的鸦片”)就已经阐述了“意识形态”。悖谬的是,这些结构主义者竟然忽视了符号体系的结构,在我们所讲的这一具体的情形中,他们忽略了司法话语的具体形式。在以仪式般的表面程式肯定了意识形态的“相对自主性”之后,[4] 这些思想家忽略了这种自主性的社会基础,即从政治场域(即权力场域)的斗争中浮现出来的历史条件,这种自主性存在的必须条件是:要有一个使相对独立于外在约束的司法体(judicial corpus)得以出现的自主的社会世界(social universe)(例如,一个法律世界),同时这个自主的社会世界还可以通过其自己的具体运作逻辑生产和再生产出这个司法体。但是,由于对使自主性成为可能的历史条件缺乏清晰的理解,我们就不能确定法律基于其形式对发挥其假定功能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相对自主性的观念通常基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建筑上的隐语。当那些自认为正在与经济决定论决裂的人们,仅仅满足于主张法律“深深地嵌套于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中”,[5] 以便恢复法律的全部历史功效时,这一隐喻依然在指导着他们。这种关注于将法律置于深层的历史力量之中,又一次使人们不可能具体地想像法律由以产生并在其中行使其权力的特定社会世界。
要同假定法律与法律职业之独立性的形式主义意识形态决裂,同时又不陷入相反的工具主义法律观,就必须认识到这两种对立的视角(一个从法律的内部,一个从法律的外部)同样完全忽视了一种完整的社会世界(我将称之为“司法场域”)的存在,这一世界在实际中相对独立于外在的决定因素和压力。但是如果我们想理解法律的社会意味,那就不能忽略这一世界,因为正是在这一世界中,司法的权威才由以产生并得以行使。[6] 法律的社会实践事实上就是“场域”[7]运行的产物,这个场域的特定逻辑是由两个要素决定的,一方面是特定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是司法运作的内在逻辑,前者为场域提供了结构并安排场域内发生的竞争性斗争(更准确的说,是关于资格能力的冲突),后者一直约束着可能行动的范围并由此限制了特定司法解决办法的领域。
在此,我们必须考虑一下究竟是什么使得作为社会空间的司法场域这一概念与已经发展起来的系统概念(例如,在卢曼的著作中[8])区分开来。“系统理论”提出“法律结构”是“自我指涉的”。这一命题将符号结构(确切地说,法律就是符号结构)与生产符号结构的社会结构混淆了。以至于它以新的名称提出了司法制度(judicial system)依赖其自身的法则进行转化这一旧的形式主义理论,系统理论为司法制度的形式表象和抽象表象提供了理想的框架。但是,尽管规范和教条的符号秩序包含了客观的发展可能性(实际上也包含了变化的方向),它自身内部并不包含它自身发展动力的原则。[9]我准备将这种符号秩序区别于客观关系所产生的秩序,这种客观关系是由行动者在相互竞争控制法律决定权中所形成的行动者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因为没有这种区分,我们将不能理解这一点:尽管司法场域从可以想象的各种观点中获得表达其冲突的语言,但是司法场域自身包含了它自己在客观利益的斗争中予以转化的原则,这些利益与这些观点是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