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之后,我以“Google 不作恶”为关键字在 Google 上搜索了一下,返回的查询结果“约有853项”,其中前十项大部分是对“Google 不作恶”这一命题表示质疑或者怀疑的文章,这一意味深长的结果是我始料未及的。排在查询结果首位的是我先前曾经读过的 shunz 写的同名文章,讲述了他在Google AdSense项目中的遭遇。我同意 shunz 的观点,在 AdSense 项目中,Google 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我也不用拐弯抹角了,我想说的就是“作恶”二字。因此,当我得知 Google 因广告交易而遭遇了官司的时候,丝毫也不感到奇怪。
下面就具体说一说 Google 的“不作恶”。
Google 宣称的“Ten things Google has found to be true”(Google 发现的十大真理)的第六条是“You can make money without doing evil”,很多人把它简化(变化?)为“Don’t be evil”,即“不作恶”。而 Google 的官方译文是:“您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赚钱。”
Google 的“十大真理”的上一级标题是“Our Philosophy”(我们的价值观),从逻辑上看,这多少令人感到奇怪:真理是实证命题,而价值观是规范命题,在很多场合中,二者恰恰构成了对立的范畴,怎么就能汇合到一起呢?而且,在第一人称“我们的价值观”这个大标题下,有三个“真理”命题都是以第二人称“You”(您)为主语的陈述句。这到底是谁的价值观?是谁发现的真理?
而且,对比阅读现在的“Our Philosophy”和2004年6月26日的存档资料,我们可以发现,不过时隔一年,Google 对“You can make money without doing evil”的解释就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试举三例(引文粗体效果为引者所加):
1. The revenue the company generates is derived from offering its search technology to companies … and from advertising sales based on keyword targeting. 变成了 The revenue the company generates is derived from offering its search technology to companies and from the sale of advertising displayed on Google and on other sites across the web.
2. However, you may have never seen an ad on Google That’s because Google does not allow run-of-site ads that appear indiscriminately on every page of our results. Every ad shown must be relevant to the results page on which it is displayed, … 变成了 However, you may have never seen an ad on Google. That’s because Google does not allow ads to be displayed on our results pages unless they’re relevant to the results page on which they’re shown.
注:“you may have never seen an ad on Google.”——这样的文字游戏未免太矫情了。我想知道的是,现如今,到底还有多少使用 Google 而从未在 Google 上见过广告的地球人。
3. Google does not accept pop-up advertising or rich media ads. Text ads that are properly keyword-targeted draw much higher clickthrough rates than flashing banner ads appearing randomly. 变成了 Google does not accept pop-up advertising, which interferes with your ability to see the content you’ve requested. We’ve found that text ads (AdWords)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 person reading them draw much higher clickthrough rates than ads appearing randomly.
解释“You can make money without doing evil”这一真理的文字一共有四段,其中谈到AdWords的这段是最长的。还有新版有而旧版无的第四段文字,也是除了 AdWords,啥都没说。可是这两段内容看来看去怎么都像是宣传 AdWords 优点的广告,与作不作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或者换句话说,这样绕来绕去的,Google 所谓“不作恶”无非就是有节制的广告而已。既然如此,又何必如钱钟书先生所批评的那样“精巧地不老实”,非得上纲上线到善恶的高度呢?说道这儿,我不由得想起了电影《教父》中 Michael 对 Moe Green 所说的话:“we’re talking business — let’s talk business.” 到今天,您有能说 Google 的广告和其他大多数公司的互联网广告有什么本质不同吗?
显而易见,“十大真理”新版本中修改的内容几乎都涉及到 Google 先前不做而现在却做的事情。当然,这些事情并不一定都是“恶”的,但归纳其大方向,应该可以套用那句俗语,Google 逐渐在由“为人民服务”转向“为人民币服务”。至于这种修改行为本身如何评价,笔者暂时不表态了,就让它“见仁见智”去吧。
上述评论并不是批评 Google 的转向本身,因为 Google 自己说得很清楚:“Google 是一个企业。” 赚钱必然是它最主要的目的。至于“不作恶”,就像承诺不违法犯罪一样,本是无需言明的题中应有之意,特意提出来宣传一下,只能是自我标榜的商业噱头。而且这一标榜是如此巧妙:如上所述,通过这样一个以“您”为主语的陈述句,Google 似乎隐身了。然而也恰恰是这句“You can make money without doing evil”透露出了Google 的傲慢乃至无礼。怎么,您没听出来?让我给您举个例子吧:假如有人对您说“您不偷别人的东西也可以赚钱”,您听了这话会怎么想?所以,再一次地,毫不奇怪,Google 的官方译文把这句话变通为“您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赚钱。”至于像洪波等人那样,对Google把“Don’ be evil”写进公司的价值观的做法持一种欣赏的态度,我只能说,这是爱屋及乌。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Evil”在这里其实是一个相当空洞的语词,Google 完全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赋予它不同的含义和解释。就此而言,拿“Don’ be evil”和朱镕基先生给国家会计学院题写的“不做假账”的校训比一比,就高下立见了。
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吹毛求疵、咬文嚼字呢?自认为不是。说 Google “作恶”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空穴来风。本文开头提到的“Google 不作恶”的搜索结果就提供了若干旁证。还有,Google “封杀” News.com 难道不是“作恶”吗?在搜索结果上方增加广告难道不是“作恶”吗(而且居然大言不惭地说,这样做既提高了广告效果又提升了用户体验)?与“坏人”为伍难道不是“作恶”吗?如果这些还都算不上“evil”的话,到底怎样才算“evil”呢?清高到“不作恶”之程度的 Google 难道耻于把自己混同于普通人民群众吗?
参考:
“比尔·盖茨先生,您可以歇会儿了,轮到 Google 当坏蛋了”
Google:不作恶,除非是为了更大的善
Google 威胁退出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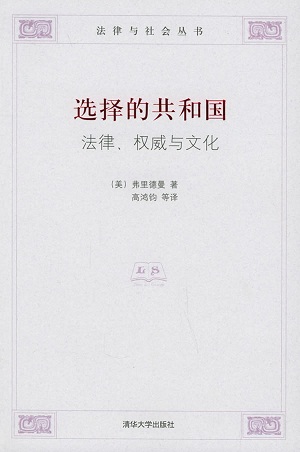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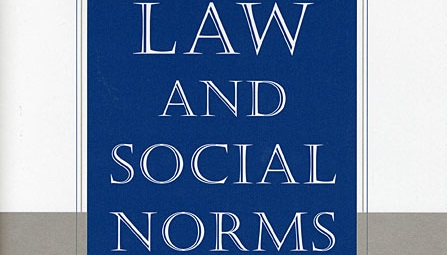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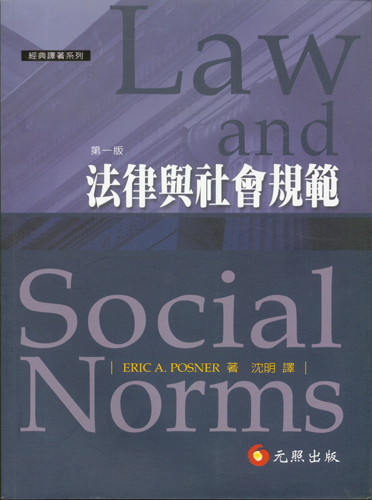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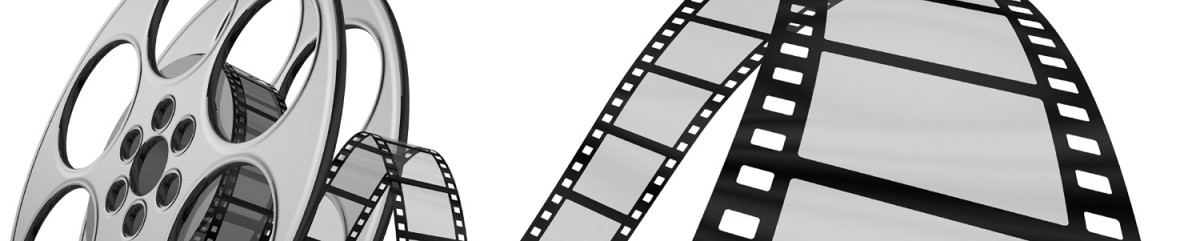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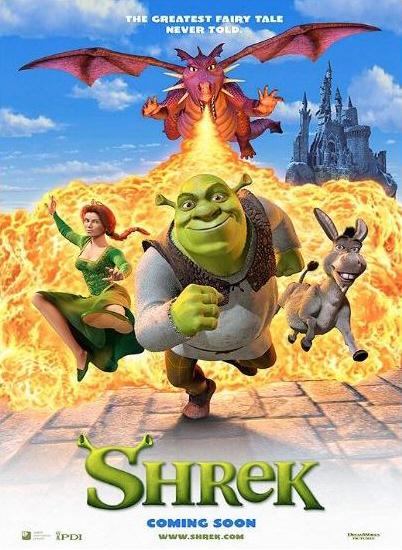 小时候我很喜欢看电视里播出的动画片,有那么一两年,中央电视台每周日晚六点半至七点演《米老鼠和唐老鸭》,这半小时几乎成了我雷打不动的收视时间。后来,动画片对我的吸引力似乎不那么强烈了,我开始喜欢流行歌曲:小虎队、张雨生、
小时候我很喜欢看电视里播出的动画片,有那么一两年,中央电视台每周日晚六点半至七点演《米老鼠和唐老鸭》,这半小时几乎成了我雷打不动的收视时间。后来,动画片对我的吸引力似乎不那么强烈了,我开始喜欢流行歌曲:小虎队、张雨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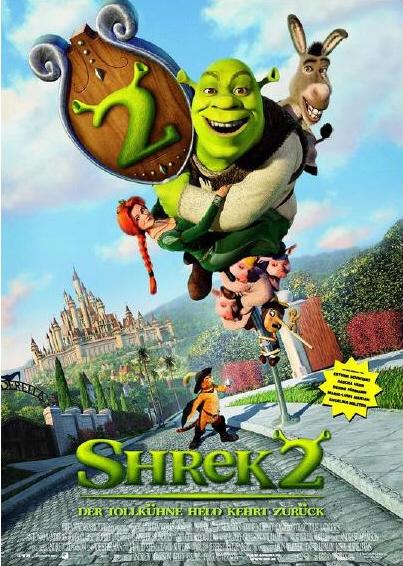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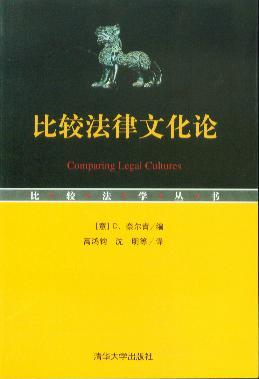 现在,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本翻译难度较大的书:多数篇章语言晦涩,论述抽象,涉及的知识领域众多,而且跨度很大。(读者如果有兴趣读一读原文的话,当知此言不虚:David Nelken, ed.,
现在,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本翻译难度较大的书:多数篇章语言晦涩,论述抽象,涉及的知识领域众多,而且跨度很大。(读者如果有兴趣读一读原文的话,当知此言不虚:David Nelken, 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