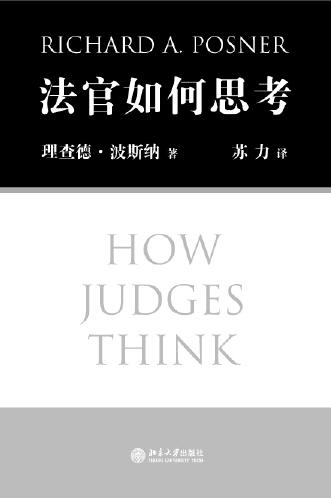尊敬的王振民院长,
各位领导和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昨天下午5点,忙完了公务,我查看电子邮件,查看了周到的王振民院长为我准备的今天大会的致辞。稿子很好,但难免公文化,不够真切。八十年才一回,哪能就这样放过了清华法学院,岂不便宜了王振民院长?!因此,我连夜自己准备了一份致辞,代表北京大学法学院,并听命于王振民院长,未经各兄弟法学院校授权而擅自代表他们,热烈祝贺清华大学的法学教育八十年。
清华1929年就设立了法学院,先后曾有一批著名学者如张奚若、钱端升、程树德、燕树棠等在清华法学院任教,为中华民族培养和输送了许多杰出的法律和法学人才,例如著名的法学家梅汝璈、陈体强、王铁崖、端木正等。毫无疑问,清华法学院在中国现代法学教育中占有光辉的一页。因为全国高校院系调整,1952年清华中断了法学教育,直到40多年后,1995年才重建清华法律系,1999年再复建法学院。
法学教育中断40多年,我分享许多当代中国法律人的观点,这是清华的不幸,也是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学教育的某种不幸。但我也认为,历史的中断,失去一段可能的辉煌,也未必是一个值得后来者太多凭吊感叹的事件。历史充满了这种诡诘莫测,不仅出现于往昔,也完全可能因种种变局而出现于未来。而且,一个法学院甚或一所大学的光荣,并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她的历史悠久。时间确实会使美酒浓郁醇厚,但时间也可能仅仅意味着年迈和败落,甚至衰亡。都说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有历史上最悠久的持续的法学教育,但它在今天世界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中算不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名字,也并非一股最朝气蓬勃、鲜活生动的力量;它在当代中国的著名,也许更多因为它是时下中国法学意识形态的一个符号。
一如既往,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当下和未来,因此最重要的事是行动和创造。事实上,对于今天参加这个大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历史上那个大名鼎鼎的清华法学院,是模糊的,更多是时空距离的创造;真正生动真切的其实是我们在过去14年间看到的这个新生的清华法学院。在14年里,特别是过去的10年间,在清华大学校方的全力支持下,在王叔文、王保树、王晨光、王振民——四“王”——主任/院长领导下,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清华法学院已迅速崛起,成为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一座重镇,其实力无论是北大还是人大法学院都不敢小觑。张明楷、崔建远、高鸿钧、张卫平、王亚新等一批中年学者在中国法学界十分耀眼,更有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正在迅速成长。
不仅于此。清华法学院还创造了一个,在当代中国问题多多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下,如何新建或重建法学院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如今正在上海交大等一些著名理工科大学得到有效复制。这就是,一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凭借其雄厚的无形资产和相对雄厚的经济资产,在短期内,从全国各地吸引一批一流学者,便可能迅速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清华法学院是第一个成功的范例,这就是清华法学院对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个重要贡献。
这个模式的意义其实还相当实在。除了其他必要条件外,我认为,它告诉我们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法学教育同样需要大量投入,需要有形资产,也需要无形资产,首先得有钱,然后才可能有一流的学者,一流的校舍,一流的管理。也因此,清华法学院对当代中国几乎是白手起家、“过快”发展的法学教育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重要提醒:尽管法学教育主要靠讲授,无需昂贵的仪器设备,但千万不能以为办法学只要找几位教师,给几间教室就可以了。
清华法学的快速发展还对整个中国法学教育提出挑战,促使法学人反思。这个挑战并不是又多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这其实应令人高兴。真正令人忐忑的是,尽管中国法学教育在过去30年里有了很大的成就,但就总体而言,水平并不高,积淀并不厚,进步还不够快,这才给清华法学院留下了可以迅速跨越的发展空间。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更应在各自岗位上不断努力,推动中国法学教育的坚实和有效发展,特别是面对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特别是面对中国在世界的迅速崛起。这是中国法学教育和研究必须面对,也只能面对的第一位的重任。
过去有一句老话:“同行是冤家”。但距离清华法学院空间距离最近的北大法律人并不这么看。这固然因为,或首先因为,清华法学院与北大法学院之间的历史渊源。在民族危亡之际,北大、清华和南开曾共同组建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我们曾患难与共!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决定将清华法律系并入北大,紧接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则把整个清华法学院并入了北大——我们曾血脉相溶!而过去10多年来,两院之间的师生交往,无论是正式的,还是日常的,更是家常便饭。
但更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追求。在法学教育、科研和管理等各方面的更多竞争、挑战和激励将有益于北大,有益于清华,也有益于整个中国法学教育。我们愿意并会一如既往,同包括清华法学院在内的全国其他法学院更紧密合作。这并非因为某种抽象的北大精神——兼容并包,而是因为我们的事业不可能属于任何个人、学院或大学。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这就是中国,是中国的法治,是中华民族的正在崛起和伟大复兴。
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事业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2009年4月25日夜于北大法学院科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