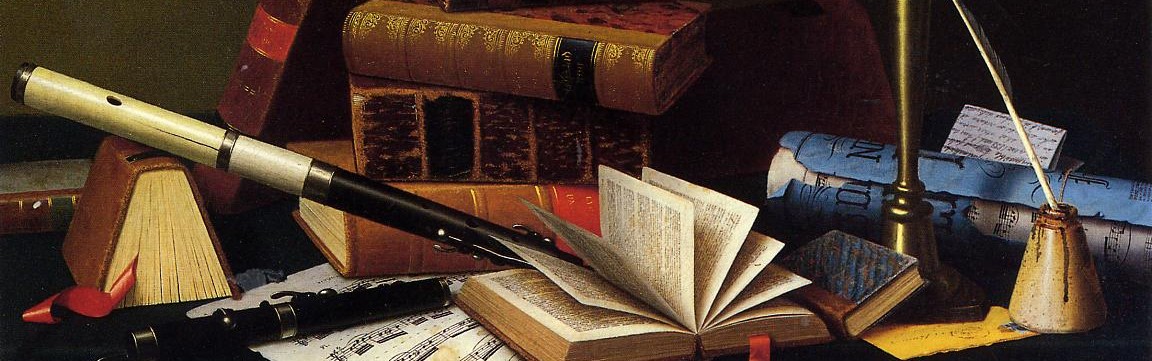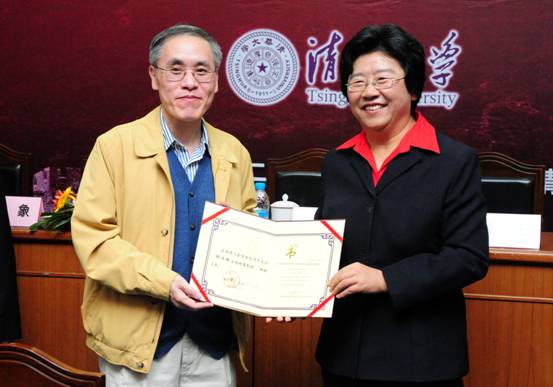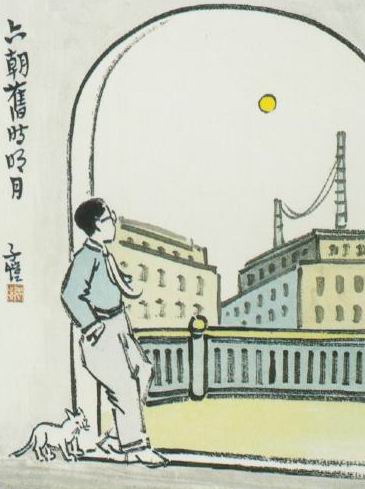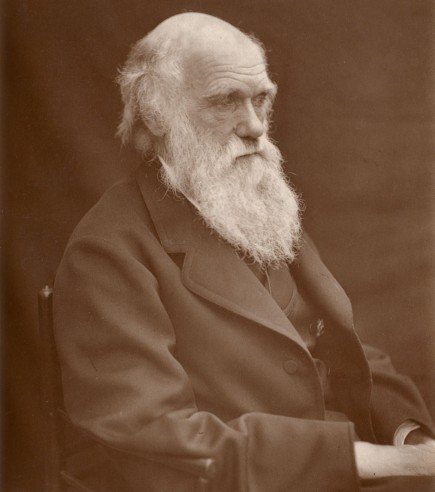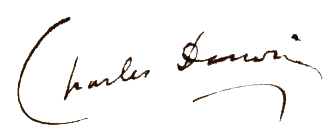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冯象谈法学教育
在熊中为熊,在鸟中为鸟
来北京才一个月,碰到的同仁、家长和有识之士,谈到教育都痛心疾首。前几天钱学森先生逝世,媒体报道也是强调他那一句话,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去办学。他说得很直白:这是当前中国很大的问题。现在大家都怪罪教育体制。这自然是不错的,一边是应试教育,一边是产业化、官僚化、量化的办学,教育和学术伦理在沦丧,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但这在在业内人士、教育部门,绝非什么新近的发现。所以抱怨归抱怨,其实是无须继续评论的。
今天就谈谈法学教育在这个恶劣大环境下,面临的一些特殊挑战,以及我们力所能及的一些对策、改革的路向。
不以美国法学教育为蓝图
本来恢复法律教育以后目标是建立一个法律的职业化队伍,形成一个职业化的共同体,30年的时间并不短,但这个共同体建立得并不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化的门槛很低
今天法学在“文革”结束后的恢复建设,是30年来法治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重要的。法学院的教育虽然只是一个专业化的训练,但也有一些问题。
标准教科书不是讨论现实生活中的法律状态,而往往讨论的是应然的、超越现实、理想化的架构方式。这个理想跟美国有关系。我们的法学教育也往往直接间接提到或关注美国的法学教育,看上去是一种比较方法充斥论文的写作、学者的论述、学生的思考,甚至影响到社会上。很多论文、教书一般开始都是美国怎么规定、法国、日本、德国怎么规定,到了最后一章才是中国怎么规定,提几点建议。具体问题还没讨论,就结束了。
美国与中国的法学教育有根本的差异,至少在目前很难拿来比较,或许说作为一个目标来套用。美国的法学教育是单一的研究生教育,全部课程围绕一个学位来进行。中国正好相反。1980年代刚恢复时基本也是以单一本科教育为主,到1990年代设法律硕士以后,学位就多样了,固然可以吸引各种各样背景的人进入法律行业,但却把原本的设置搞乱了。
就像中国政法大学方流芳教授指出的,在现在的中国,法学的第一学位可以是任何一个阶段的学位(本科、硕士或博士),一个人可以从任何阶段进入法学教育。法律资格考试(司法考试)也不需要法学专业,整个行业门槛变得很低,职业化受到阻碍。
本来恢复法律教育以后目标是建立一个法律的职业化队伍,形成一个职业化的共同体,30年的时间并不短,但这个共同体建立得并不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化的门槛很低,不同的阶段都向外开放,这样的教育制度太繁复,还促成很多不规范作法。到1990年代末扩招,一下把就业市场搞乱了。现在很多学校,法学专业的就业很不好,并且由于就业压力、法律就业市场接近饱和,大部法学院毕业生流向非法律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