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明:“路”vs.“网”: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角力
研究全球化的文献已经汗牛充栋。宽泛地说,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的近现代化过程大体是同步的。在这个意义上,几百年来,全球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历史进程。尽管每一代人都感觉自己生逢全球化时代最前沿的历史时刻,但事实上,全球化并非一个线性进化过程:在某些非常重要的领域,例如就劳动力的跨国自由流动而言,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程度还不及十九世纪。阻碍或者牵制全球化的因素显然既复杂多样又盘根错节,但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恐怕就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及其治理对全球化的敌意了。通俗地讲,在全球化这一宏大的叙事层面上,地球村从来都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故而全球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建构出来的社会工程或者乌托邦,而只能是由种种利益驱动的政治经济博弈的动态过程。道理这样讲似乎有些抽象甚至空洞,我们不妨以不久前出版的一本书为例子,由国际贸易这一典型的全球化论题入手,看看从古老遥远的丝绸之路到——比如说——案头昨天报纸上还在热议的“一带一路”、“亚投行”这些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风马牛”,如何被全球化的理论勾连在一起,以及这种整合过程为什么必然充满了羁绊、分歧乃至冲突。
我们要讨论的书是阿努帕姆·钱德(Anupam Chander)的《电子丝绸之路》。钱德教授任教于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法学院,是一位网络法与国际贸易法专家。他这本书系耶鲁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书出自知名学术出版社,封底印有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精英法学院学者(以及美国参议员、WTO官员)的推荐语,不过其文体定位却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从全书的结构、行文以及特别是文献引证来看,应该说其性质更接近 journalism。话这样讲,并非基于某种所谓的学术自信或自大贬低洋人同行,因为至少“他们是不大敢一把剪刀、一瓶浆糊闯天下的”(借用冯象老师说法)。其实,指出学术味不够浓这一点,虽然算不得赞许但也并未意在贬低。我们知道,与国际商贸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研究多属实践性很强的部门法领域,对于这类论题来说,纯学术的、着力追求理论创新的“阳春白雪”型写作很可能只是富有“波西米亚”意味的自娱自乐。立足于严肃的实证材料的分析和研究——而非花拳绣腿或者屠龙术——应该成为法学研究的主流。这一点对当下中国来说格外值得强调,因为门派/语词之争变换了模样,在法学界代代转世生生不息,甚至可以化神奇为腐朽: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的战斗本身其实构成了(或者说延续了)政法法学。钱德教授这本书即便在纯学理层面上缺乏建树,但其务实的方法、扎实的材料、多学科视角及其提出的诸多问题与分析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国际商贸与互联网既是当今世界的重大政治经济学问题,也是重大的法律问题。我相信政治法律经济贸易等诸多相关专业的学者,以及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都能从这本书中汲取有益的信息和洞见。以上简单介绍之余,应该说明,笔者的醉翁之意不在作为部门法的国际贸易法研究,而在提取该书宏旨,在一个较为抽象的层面上,即所谓“理论”层面上,略微探讨一下电子丝绸之路、互联网、世界贸易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尝试初步挖掘这种关系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特别是全球化和与之相反的力量“地方化”之间的张力与互动。可以说,这是形塑当代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力量和基础性动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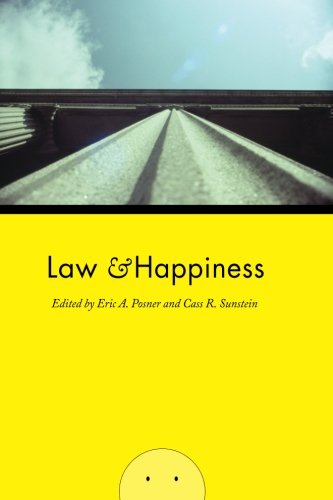


 Lawrence Lessig:《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Lawrence Lessig:《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