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地方名叫啤酒屋,老派,聊天蛮好,是不是?你仔细看这儿的客人,那神情;年纪同我相仿,多半是来哈佛看孩子的。招待员,我们这一位,文文雅雅的是在校生。那边金色的大罐子,是蒸馏器。他们自产啤酒,待会儿你尝尝,要没过滤的,有劲。美国是这样的,懂啤酒的人,或者自个儿在地窖里酿,或者上山沟里水质好的小厂子拎,称作microbrew,小酿,跟超市里卖的“马尿”是两种文化。
不,“马尿”不是英语,是云南土话。我在乡下的时候,老百姓看我隔三差五往酒厂和商店跑,拎回来的有些瓶盖撬开还滋滋冒泡,拿过去呷一口——寨子里头他们打着什么分我什么;我搞到的名堂,酒啦火药啦(兄弟民族的生产工具),也给他们——啊呸,马尿!吐地上了。我说,是你赶马帮饥渴了接马尿喝过,晓得那滋味?
你别笑。话说回来,我的意思是,做学问、办案子,这世界上干什么事都有一个饮小酿还是接马尿的价值立场问题。
二
这一回“80后”算是露峥嵘了,老喇嘛走哪儿,抗议跟到哪儿。破天荒哪,他在西方是神圣,见他一面蒙一辈子的福。你们老师也跟我说,好感动。真的,比李登辉访问康奈尔那一次留学生反台独大联合,还要壮观。
国内民众自发的抵制活动,是否“非理性”“民粹主义”?操那份心干吗?仿佛老百姓上街,喊喊口号,会坏了谁家的秩序。他又没抢商店,没烧民房。
“理性”而大写,是现代法治的门面。法治的要义,叫形式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名程序正义。程序背后,一笔笔见不得人的交易,才是真正享受保护、百般补贴照顾的那个理性博弈者的世界。而老百姓的“非理性”,那博弈者眼里的“民粹”,便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动力和一大特征。自古如此。不然,高贵的苏格拉底就不会像只牛虻似的去蜇民主,终于被民主的雅典判处死刑。
是的,民主和法治一样,也是以暴力为后盾,因暴力而强盛的。不懂这一点,就不懂雅典以降西方民主传统的生命力所在,包括今日的美国,她的充斥暴力的大众文化。民主与资产阶级法治这两样东西,因此是经常处于冲突之中而相互制约的。现代政治例如西方式代议制民主,按照那个市场经济学家的宝贝,中产阶级“经济人”(马克思讥为“英国人”)的阴郁性格来衡量利弊,不参与才是最理性的选择。因为,它的设计总是让多数人的参与成本很高而收益无从预计。换言之,民主之能够建立、成长、纠正自身的弊端,抵制受法律保护的形形色色的腐败,依靠的绝非法治的或市场经济的“理性”,而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非理性”,即他们动辄上街上访,抵制这个打倒那个,甚而置“自身利益”于不顾的不屈的精神。
有没有小写的“理性”?有啊,到处是它,躲都躲不及;就是日常生活中教我们屈服于现实的一套套托辞。
都说知堂老人(周作人)的文章高明,“童痴”冲淡,如一片苦茶。但那是铁屋子里蜷缩久了反以为悠闲,枯坐着品,这么习得的丁点文人趣味。放到“大先生”的文字一旁,在那刺向国民劣根性的思想的投枪面前,就显得过于精巧、小气又太讲理性,文如其人了。他的“寿则多辱”之叹,固然是社会与家庭悲剧;但一个新文学先锋,处于民族危亡的关头却患得患失,实在是不明智又怯懦之至。人的天性,本是健强好胜而不乏搏斗的意志的。“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这,才是不惧暴力、敢于反抗的自由人格。小民“顺生”、柔弱“守雌”之类的说辞,各个朝代都有,是驯服了的“理性”的自辩和自慰。法治化的今天,“理性”大纛高扬,则是这浮华时代颓唐风貌的一副扮相。
其实小民“顺生”当个良民,至多是一厢情愿。你想,鞭子握在别人手里,良民与否,怎么个讨生活,还得看主子脸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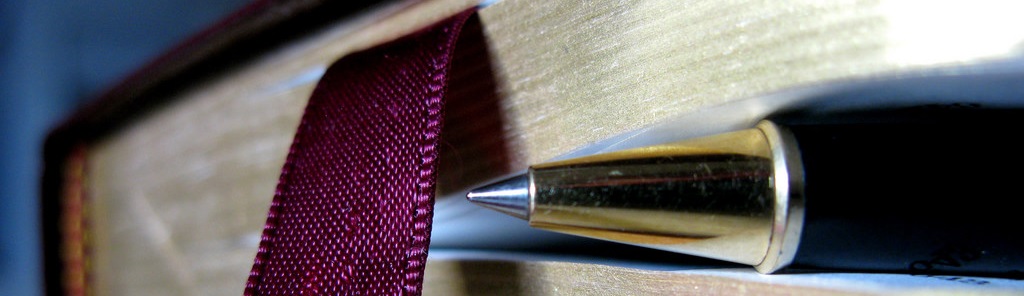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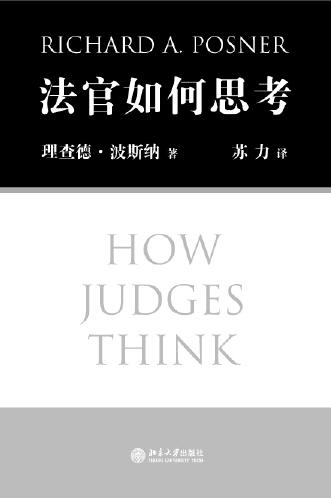

 赵利栋(以下简称赵):瞿老,您是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嫡孙,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家世和童年的情况?
赵利栋(以下简称赵):瞿老,您是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嫡孙,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家世和童年的情况?
